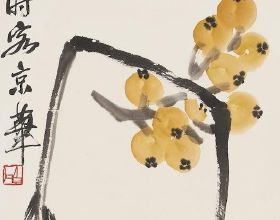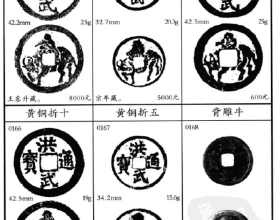韓羽先生新著《我讀齊白石》,解說齊白石先生的畫作,可謂璣珠滿目,精妙入神。經他老人家一點撥,使我這個書畫界的門外漢也能對齊翁的畫作愚思開竅,從畫裡看出畫來,不由地讚歎:是這麼回事,是這麼回事!真真是大家,真真是巨眼!
說來我不是一個能輕易被人說服的人。不怕人笑話,前些年一些文化講壇節目正熱,我對有的主講就熱不起來,無卓見、無新意還瞎扯。在名勝旅遊景點,我大都不隨團聽解說,因為我聽過信口開河亂加醬油醋的導說,受不了他們編造的“熱鬧”,不如單走單看有所得。可我對韓老的《我讀齊白石》,卻是一字不落地看,有的地方是回過頭來再看,唯恐錯過接受教導的機會,好似一個沒有點撥就不會思考的人。也許正因為如此,順著韓老的指引想得也就多了,如齊翁的《牧牛圖》竟使我想到了牧羊事。
韓老說《牧牛圖》,從“拽直了的韁繩”及牧童身上的鈴鐺“畫眼”中看到是牧牛歸來,確是解得切,令人佩服。齊翁童年放過牛,晚年寫放牛詩,作放牛畫,對放牛之事有生活體驗,有美好回味,畫中隱含著真摯的感情,這感情也被韓老讀了出來,而且一點不差。何以見得?由我放羊知之。
我記事的時候村中各家各戶已經“入社”,牛全是生產隊的牛,在牛屋院裡有飼養員餵養。田間耕作時把牛套上,讓它們拉著拖車到地裡去;不耕作的時候,把它們拴在牛屋裡,或者拴在院子裡,我從來沒見過放牛的事。那時允許社員養羊,我見過放羊,自己也放過幾年青山羊。前幾年初冬于田野裡看到一個老漢在割小野豌豆苗,說是餵羊。我問他怎麼不牽出來放放,這樣羊才能長得更好。他說牽不走它,用棍打、腳踢它都不走。我笑說這是它自小沒被放養的緣故,你忽然拉拽它往外走,它擔心沒好事,害怕了,哪裡肯走?如果在外邊放養習慣了,解開羊韁繩它會在前面拉著你往外跑,還是廣闊的田野比家裡羊圈好哇!
羊拉著人往外跑,這時韁繩也是直的。羊與牛可比嗎?可比。當年齊宣王以羊易牛,怎麼沒有以其他牲畜易之?再說宣王是對親見者“不忍其觳觫”,並沒有分牛大羊小哩,正所謂“一視同仁”。若說此比有些牽強,那“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可有得一比?牛羊有其共性,較溫順、不刁滑、少任性,表達快樂和畏懼的情感,讓人最容易觀察到的就是願意走和不願意走。牛羊都是在放牧去時走得急,回家路上走得慢。放牧歸來,雖然“日之夕矣”,還是不大樂意進入牛屋羊圈。齊翁所畫牧童在放牧歸來的路上想著家長掛念,急於回家吃飯,而牛已吃飽喝足偏偏不慌不忙,這才有了人在前、牛在後、韁繩直,甚至還有牧童回首埋怨牛因不解人意而腳步遲緩的各種情態入畫。齊翁曾是放牛者,知人知牛,方有《牧牛圖》佳作;韓老未必放過牛,當見過放牛,或許還有放牛娃朋友,知放牛事,又是知畫者,自然看得透,解得切,畫中感情也在他眼中現出。我曾是牧羊之童,與牧牛體驗亦有相通之處,因此韓老說牛我說羊,信口扯來,也算旁推互證。
牛也有慢悠悠地往外走、急匆匆地返回牛屋的事,那是我親眼所見在生產隊耕作的牛。牛被趕出牛屋院後,它們也知道是去出大力,無論是在前拉拖車的牛還是拴在拖車後跟著走的牛,都走不快;而收工回來的路上,它們則是大步快走。我想,無論是給集體耕作還是給個體耕作,牛都會是這個樣子。而集體耕種時,社員們出工路上慢悠悠,收工回家急匆匆,那是“吃大鍋飯”體制所造成的,分田到戶後這種現象隨之無影無蹤。
不論何種動物,嚮往去的地方就會加快步伐,不願去的地方就會放遲腳步。“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可見陶淵明思歸、李太白願往之情。齊翁一首題畫詩亦云:“當真苦事要兒為,日日提籮阿母催。學得人間夫婿步,出如繭足返如飛。”道出貪玩的兒童初入學堂猶如野馬上籠頭,上學、放學路上恰似兩人所為的實情。人猶如此,況牛羊乎?熟知放牧之事,洞察人物心態,才能概括生活、提升意境,畫出好畫,解得好畫。
(作者:孫南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