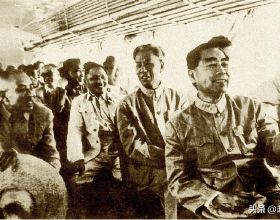劉少奇,曾經還到過峰峰的八特,並且還留下了一段驚險的故事。
一九三一年深秋的一天傍晚亥時,天空早已拉起了夜幕,大地披上了漆黑的面紗,勞作了一天的峰峰八特村民,早已進入了夢鄉。秋風襲來,村周邊的若大的玉米、高粱地秸稈,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砰砰砰”—一陣槍響聲……劃破了寧寂的夜空,從武安磁山方向傳來,驚醒了睡夢中的八特村民,村中弘濟橋兩側的十幾棵古楊樹上的黑背白肚兒長尾巴鵲同時驚飛,發出哀嚎,朝沒有槍聲的西南趙王腦方向競相逃命……
青紗帳在嘩嘩作響,只見一年輕人熟悉的連串幾塊玉米高粱地,沿著村北后街官井,匆匆的跑來,穿越幾條衚衕和幾堵矮牆,疾步來到村東觀音廟東側的東坡頭,見一人家兒還亮著微弱的燈光,原來是八特村油坊掌櫃韓恆年正在刷鍋洗碗,清洗油坊器具。年輕人一個箭步跑進來,操著濃濃的湖南口音:“老鄉哥,有人追我,借大哥棉襖兒一用。”韓恆年見來人說話和氣,睿智豁達,迅速脫下棉襖兒,粘帶,白羊肚兒毛巾。又從鍋底順手摸了一把鍋灰,抹在了年輕人臉上,並幫他繫好粘帶,年輕人手持吹帚(八特方言,一種用高粱毛做的洗刷用具)洗刷起碗筷來。藉助搖曳的籽油燈光,只見年輕人高鼻亮腮,神情穩重,一臉和善,油坊掌櫃知他不是賴人,急中生智,便教給他應付歹徒的點子。
“砰砰砰”—又一陣槍聲響過,“就跑了這一片了!”這夥眾匪兵踢開油坊的大門,不分青紅皂地闖進了進來。
“搜!”在小頭目的厲聲吆喝下,眾匪徒像木梳篦的一樣把五間正屋,四間陪房,以及碾房,存有花籽的柴房颳了一遍,結果哩什麼也沒有發現,而雞窩裡的活雞卻無一倖免。
“班長,沒有。”
“糟老頭,看見有人跑進來沒有?不說實話,老子斃了你”!
“長官,我看見了”。
“你他媽的藏哪了”!
“俺正在鍋臺上洗鍋碗兒,沒有許顧(八特方言,沒注意)人啥樣,光聽見身後有人往北跑的腳步聲,肯定往北門跑了”。
“他是誰?”小頭目晃著手槍對準了正在洗碗的年輕人。
“長官,他是俺家的啞巴兄弟。”說著順手用力扯了扯年輕人的衣襟。
“長官問你話哩”?
只見年輕人轉過身來,面對著拿槍的眾匪徒不屑一顧。用油漬的手指指了指張開的嘴巴,發出“啊啊”的啞巴聲,小頭目走上前仔細觀察年輕人,只見他身著油漬的破棉襖,頭上繫著油汙斑斑的白羊肚兒毛巾,腰間裹著破粘帶,臉上還流著拉風箱幹活的菸灰汗跡,疑心頓消。“打”小頭目一聲令下,眾匪徒拳打腳踢,還用槍托把韓恆年打翻在地,“逮不到共匪,回頭找你算帳!”說罷帶領眾匪徒,手拎著六口活蹦亂跳的家雞向北門灰溜溜的追去……
年輕人忙把韓恆年扶起,給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塵。韓恆年看看眾匪徒已走遠,便插上北門的門栓,回身對青年人說:“我用力扯你的衣襟是暗示你裝啞巴,裝的不賴。不然一說話就露餡了”。
他接著說:“你也看到了這夥刮(國)民黨兵,對老百姓淨幹些打罵欺壓,偷雞摸狗,耍女人的絕戶頭事兒,不是我攆你,說不定,這夥國民黨兵還可能回來哩”。
年輕人把棉襖還給韓恆年,低聲說:“我叫胡服,剛才好險啊!多謝大哥出手相救,還為我捱了打。”說完向韓恆年深深的鞠了個躬,接過韓恆年在煤渣窯裡藏的護身小手槍,轉身邁著堅毅的步伐往鼓山陵東的西佐、六河溝煤礦方向,摸黑急去……
解放後,韓恆年才知道“胡服是少奇同志的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