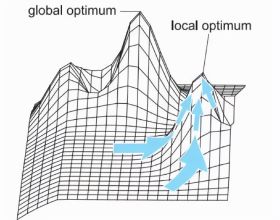有兩天,沒給母親打影片了,心中不安。昨天晚上,我拔打母親的影片。等了幾秒,接通了。“媽媽”。我看著影片,叫了一聲。過了一會兒,黑糊糊的螢幕裡面,出現了模糊媽媽的面容。“嗯,我剛才睡著了。”媽媽躺在被子裡,緩慢地說著。”由於沒有開燈,藉著手機螢幕的光,我看不清媽媽的樣子。加上媽媽的聲音,比較微弱。我心裡,更加不安起來。“媽媽,您身體還好吧?”我緊接著問道。“我沒事,你放心。這兩天,家裡下雨。有些寒冷,吃完飯,我早早睡了。剛才睡著了,聽到手機鈴響,看是你打的,趕緊接了。”媽媽接著說:“沒事就好,那您睡吧!”我怕說的多了,影響媽媽的睡眠,更怕因寒冷的氣溫,會使媽媽著涼。因此只問侯了一聲,就想掛掉影片。
我的老家,在鄂西北的大山深處。雖然十月的深圳,炎熱似火。但是我老家的十月,己入初冬。晨有寒霜白露,夜有冷風呼嘯,人們己穿上了,防凍衣帽了。
“才說幾句,你就要掛掉。我感覺好多天沒和你說話了。很想拔你的影片,又怕打擾你休息。”模糊的螢幕裡,又傳來了,媽媽的聲音。“媽媽,我只不過兩天,沒給你打影片,你怎麼說好久沒和我說話呢?”我不解地向媽媽問道。
“我現一點記性都沒有了,每天心裡總是,想著能和你子妹幾個,說說話。一天沒有聽到你們的聲音,我心裡總感覺著不踏實。所以,兩天沒和你說話了。我總感覺,隔了好久好久。”媽媽接著跟我說道。
聽著媽媽的聲音,我心中一陣顫抖。自從父親去世,媽媽獨自一人在家,己整整三年多了。如今媽媽,也己六十多歲了。自幼兒時,家裡的生活。都一直是非常艱難的。
鄂西北,與秦嶺相連。我家就在兩省交界的山坳裡。山高地貧,土地是七分石,三分土。就是這種貧瘠的土地,我家五囗,只分得不足三畝。還有一畝五分水田。水田在背陽的山腳處,天干旱的時侯,常常是由於缺水,而顆粒無收。每年,還得按人頭交公糧。我家有三個小孩,我和妹妹都是超生人口。因此,還得要交一筆超生費。再加上我們三個上學,的學雜費。
家裡常常是,無米下鍋。要靠著向親戚鄰居借債來維持。爸爸迫不得己,離家到河北鐵礦,河南煤窯謀生。但由於身弱多病,時運不濟,常常到了年底空手而歸。
因此撫養,我子妹三個的千斤重擔。全都落在了媽媽的肩上。
媽媽,為了讓我子妹三個,不餓著,不凍著。起早貪黑,拼命勞作。除了耕種田地,還養了幾頭豬。到了年底,殺了豬,一大半用來還債了。剩下一些邊角,用來改善伙食。
長年累月的勞累,得不到休息。媽媽的身體己嚴重透支。在一次重感冒後,患上了支氣管炎。每到秋冬來臨,媽媽就會從早到晚不停的咳咳、咳!不時還會吐出一兩口,鮮紅的血痰。年幼的我,常常在寒冬的深夜,被媽媽一聲聲的咳咳聲,從睡夢中驚醒。聽著媽媽撕心裂肺的咳聲,我心憂如焚,我怕這該死的疾病,會讓我失去媽媽。然而人小無力,只能把頭埋在被窩裡,偷偷的掉眼淚。
我一邊用手抹著淚水,一邊在心裡,默默祈禱,祈禱老天,保佑媽媽早日趕走病魔。祈禱老天,讓我快快長大。我要外出打工賺錢,有了錢我就可以給媽媽冶病了。就可以減輕媽媽肩上的重擔。
十四歲那一年,我離開了家門。隨著鄰居到了河北省,武安市西門鎮,一個叫馬甲腦的礦區。一千多米深的鐵礦井,狹矮陡峭的,採礦通道。井下岩層湧出的流水,冷若寒冰,刺骨透心。在密不通風的井下,狹小通道里,衝氣鑽的打孔聲,鐵鍬碰撞礦石的聲音,異常刺耳。一個班八九個人,十幾個小時,在這不見天日的地下勞作。
腳踏冰冷巖水,彎腰弓腿,前拉後推著,滿載六七百重礦石的手拉車。一鍬鍬的鏟著沉重的礦石。一曰又一日。我的手磨破了,腳起了水泡。一到下了班,升了井。躺在床上時,我的肩膀,胳膊腿總是痠痛難受。
半個月後,一天上班時,推礦石車時,我滑倒了,腿碰到了塵硬的鐵礦石上。當時一陣鑽心的痛疼,使我的腿頓時,失去了知覺,接著從褲口處,不斷湧出鮮紅的血。我本能地伸手拉起褲子,在左腿關節處,一塊雪白的皮肉向外翻起,一股股的紅紅的血,從破口處湧出。我本能地用雙手,緊緊按下破皮,以減少出血量。
值班的,班長趕過來。將我送到了井上。包工頭,用車載著我,去了礦區的小診所。醫生用酒精,清洗了破口。用針錢線將破皮縫合,縫了十四針,才將破皮合攏。後用白紗布緊緊繞了幾圈,粘上膠帶。又輸了幾瓶葡萄糖,幾瓶消炎水後。告訴我,三天後來換藥。工頭付了錢,載著我回到井口處,用石棉瓦搭的宿舍。
回去的晚上,傷口時時疼痛,是鑽心的疼。整整一個星期,我都無法安睡。每到開飯時,上廁所時,我只能用右腳,一瘸一跳的緩慢移動。二十多天後,終於拆線了。但我依舊不能行動自如。
多少次,我好想回家,好想給媽媽打個電話。可是每次都放棄了。長途電話,鎮上才有。一般要先打到鎮上,讓人帶好口信,給家裡。約好時間第二天,在那裡等著接聽。礦區,也得到商店才有長途電話。我家離鎮上,還有三四十里的盤山路。我也不想告訴媽媽,我現在的處境。因為我怕她難受,怕她擔心。
我更不能回家,隨原上了半個月的班,可除了出來借的三百元路費,我所剩無幾。家裡的僨,媽媽的病,我許下心願,將無一實現。
又過了半個月,礦上發工資了。我還了出來時借的路費,還剩下五百塊。由於腿上的傷口沒有完全恢復,我仍然無法下井。
當時礦上,民工多。井下的活有限,用不了這麼多的人。因些每隔幾天,工頭總會排除,一部分身弱病老的民工。我自然是其中的一員。結完工資,我和另一位年長的民工。被包工頭除名了。
後來,我跟著這位工友。來到了河北省,唐山市,豐潤縣,任各莊鎮,光新村的一間做膠合板的小廠。
在這裡,我整整幹了一年,一月上三十天班,一天十二小時,半月白班,半月夜班。小廠兩班共有二十多個民工。我的工作就是擺板,在一塊鐵板上,先放一張松木皮,後襬上過了膠合劑的四塊曬乾了的雜樹木皮。在再上面,密密麻麻地,排滿碎木皮。然後又在上面,蓋一層壓過膠的大料。一層大料,上面加一層曬乾的碎料。然再壓一層大料,後再蓋上一張很薄的松木皮。後將幾張擺好的板,推進熱壓機,壓實烘乾。
再經過切割四邊,一塊塊地擺放整齊。然然裝車送往建築工頭,傢俱廠使用。擺三層皮的叫三合板,九層的叫九合板,十二層的叫十二合板。以次類推。工廠會根據客戶的訂單生產。最多隻能壓十五層,最少的是三層。
小廠是包吃包住的,吃的是,早晚白菜湯麵饅頭,中午則是土豆,或是洋蔥,或是白菜西葫蘆燉肥肉,加一碗大米飯。一年時間,大都如此。只有過節,過年時稍有些變化。
住的是,長長的一大間,毛丕平項紅磚房。房裡砌著長長的一排土炕,紅磚牆上抹了層白灰,宿舍的地面,是坑坑凹凸的泥地,牆面因多年,冬季燒炕的煙火,燻的黑如鍋底。一到冬節,就要往坑裡的,爐坑中,忝加幹樹皮,碎木削,或是木板的邊角料。點燃取暖,每當睡覺前,總得忝上木料,燒上三四個小時。早上起床時,被子上頭髮上,地面上總會落上薄薄的一層煙塵。,
工作的車間,是一個大棚子。四堵八九米高的紅磚牆,上面架著三架鐵梁,樑上面用鉚釘,釘著三十多張薄鐵皮。南邊向院子,的一面開著四米多高,三米多寬的大門洞。沒有門框門板。一到冬天,寒風從四面的破口,倒灌進棚子。夜晚常常冷的全身顫抖,手腳冰涼麻木。夏季,壓模機裡的刺鼻,膠水煙味瀰漫整個棚子。一到開機時間,取出壓好的膠合板時,一陣陣嗆人刺鼻的青煙升起,辣的人睜不開眼。只得用衣袖掩住口鼻,先深吸一口氣,憋住。等壓好的板從熱壓機中,拉出來後再吐出。滾燙的
鐵板即使帶著膠手套,依然感到火辣辣的痛。四十分鐘,要出一次板,一次七張。每張都要靠近熱壓機,雙手抓緊鐵板,用力地將板從熱壓機裡抽出來。擺在地上,然後再在空鐵皮上擺料。週而復始,長年累月的重複著。
作滿三十天,除掉罰款,可剩五六百元。一年下來,我積攢了四千多元。年底我帶著錢,到了市裡的大藥房,選了冶療支氣管炎,哮喘病的,最好的藏蒙藥。一口氣買了半年的藥量,付了兩千多元。提著一大包的藥,趕到郵局,寄給媽媽。
一年後,媽媽的氣管炎,孝喘沒有再發作了。後來我帶看媽媽,爸爸一起來到這個小廠又作了一年。終於還清了多年的舊帳。還完了賬,我和爸媽一起,離開了這個我工作了三年的工廠。後來爸媽,留在了家裡務農。我則南下到了廣東。
如今雖然,常有錢物給媽媽。可是無法陪伴左右,遠隔千里的我,每每想到這裡,總會不安。只得隔三差五的,打電話影片。陪母親聊聊家長。年老的母親,獨自在家,是多麼的孤獨無助!幼小時,躺在媽媽的懷裡,才會感到安心幸福。片刻沒見到媽媽的身影,頓時會驚恐的,手足無措,繼而哇哇哇大哭。直到擁入媽媽的懷中,才會心安快樂。而今我長大了,媽媽也老了,切相隔千里。當母親孤獨時,無助時,生病時,又能指望誰?依靠誰?這個大大的問號,時常掛在我心頭,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