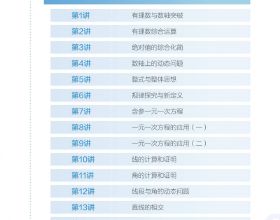“十一”將至,一年一度的國慶小長假來臨,同時也拉開了藝術黃金週的帷幕。香港地區作為頭部陣地,各大拍賣行早已競相佈局。不少拍賣公司已經提前劇透了秋拍“硬菜”。其中作為老牌拍賣公司的香港蘇富比也算是牟足了勁,尤其在中國書畫版塊,彙集多項香港及海外私人收藏,如梅潔樓藏20世紀名家書畫、饒宗頤基金藏饒氏精品、馮康侯家屬收藏書畫等。
其中,最令人矚目的當屬張大千的潑彩山水鉅製《春雲曉靄》,此幅作品也是香港蘇富比有史以來估價最高的書畫作品。
潑彩紙本 鏡框 一九六八年作 100.5x140公分
估價待詢
來源:香港蘇富比,一九九一年五月
中國書畫拍賣會,編號88
梅潔樓藏
《春雲曉靄》是張大千在巴西時期的潑彩作品,也是他潑彩達於顛峰的鉅製,畫面大膽抽象,墨彩掀起一股狂飆的氣勢,如入無人之境,是他創作最具爆發力時期的代表作。
本幅為橫幅構圖,畫面幾乎全滿,略無留白,乍看只見墨色上堆積著大塊鮮豔的石綠,有色彩造成的視覺興奮感,但因並無任何細節描繪,會引起觀者暫時的迷失,但旋即在畫面上方看到疑似峰巒的數個山頭,左方峰巒上還有曾在傳統中國山水上出現的植物表徵,再加上畫面右下角的若干山石紋路,若非這些微小的細節輔助,讓觀眾可以將之閱讀為山水,它簡直就是純粹的抽象畫了。由於畫面的瞬間性與狂掃之姿,會令人誤以為這是即興之作或神來之筆,其實這樣的畫面效果得來不易,作畫的過程也頗耗時費日。
上世紀 60 年代,張大千的潑墨潑彩藝術作品讓國內外藝術界震撼,更為中國傳統國畫藝術打開了一扇窗。自近現代以來,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傳統國畫一直在尋找現代轉型的突破口,張大千的藝術融合或許是一次最成功的探索。
說到張大千可能有人提出疑問,張大千的潑墨潑彩到底是對傳統繪畫技藝的傳承與發揚,還是將西方藝術與中國藝術的成功融合?張大千的潑墨潑彩藝術的成因是什麼?近幾年市場低谷期,這種藝術形式的市場表現又如何?您想知道的盡在雅昌Artbase,讓我們一起來探個究竟。
自 2012 年進入調整期以來,張大千書畫作品交易量進入下行通道,尤其是 2018 年,成為張大千書畫拍品近 6 年來成交件數最少的年份,這跟前一年其拍品成交量的拉昇不無關係,考慮到整體經濟不景氣,資源徵集愈加困難,加上重複上拍週期等問題,預計後續張大千書畫拍品全球成交量會持續走低趨勢。
張大千書畫拍品無疑位於中國書畫拍賣梯隊中的第一梯隊,也是絕對的市場“硬通貨”,其學術價值、美學價值等等方面已然獲得歷史定位,因此其作品的價格體系較為成熟穩定,但隨著中國藝術品行情的下調,不僅單價難創新高,整體成交狀況也出現萎縮,2018 年,張大千書畫拍品全球成交量僅為 38.63%,這應該是 2000 年來張大千書畫拍賣市場的低谷,業內人士認為,這與上一波牛市行情有關,精品挖掘、釋放後,進入新一輪的收藏期,不到下一波牛市,藏家不會輕易出貨,貨源的緊張也是導致低成交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幾年來,張大千作品雖然上拍量、成交量、成交率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跌,但張大千書畫拍品的成交總額卻在近三年表現突出,2018 年其創收總額達到 22.65 億元,這意味著張大千書畫拍品均價在提升,原因並不神秘:一是各大拍賣控制上拍量;二是拍行紛紛聚焦拍品質量,尤其是千萬元級別的張大千書畫作品市場得到更多重視,而非往日只盯著億元級的拍品,畢竟精品、極品是鳳毛麟角,支撐一位藝術家大盤的主力軍還得靠中高階價位區間的市場成交。
在中國區域,拍賣的重鎮無非是京津地區和港澳臺地區,這裡的拍賣資源最優,也是高價記錄的主要誕生地。從 2012 年至 2018 年兩地的拍賣資料可知,張大千潑墨潑彩作品中,創作於上世紀 80 年代跟 60 年代的拍品均價最高,也最受藏家追捧。
張大千潑墨潑彩作品的創作分為幾個時期,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50 年代中期,張大千的細筆畫風開始向減筆、潑墨潑彩等粗筆畫風轉變。他在 1956 年創作的《山園驟雨圖》成為這一時期潑墨風格的代表作。到了 50 年代後期,張大千對於潑墨尤其是潑彩的探索投入極大的精力跟熱情,畫面的抽象感更加強烈,但又不是西方印象派的簡單衍生,因為其作品中除了墨與色,還有中國繪畫中極為重視的線條,這些線條強而有力,“劃破”墨色的覆蓋,讓這種大收大放的畫風中有多了工整細緻之感,更有中國文化的意境。總體而言,張大千的潑墨潑彩作品給人透明通靈、清逸雅緻之感,他也真正完成了了中國畫在現代語境下的傳承和演進。
張大千的潑墨山水給人直觀感受是色彩鮮亮,好比一件攝影作品,飽和度、對比度、構圖比例等都恰到好處。其色彩上的優勢主要緣於張大千用墨十分考究,拒絕使用宿墨,每次創作前都會將硯臺清晰乾淨。其山水潑墨作品中,儘管有大面積的潑彩或者墨團,但依舊給人剔透晶瑩之感,虛實相間,水墨比例控制恰當,如仙境一般,自然生動。
自 2012 年進入調整期以來,張大千書畫作品交易量進入下行通道,尤其是 2018 年,成為張大千書畫拍品近 6 年來成交件數最少的年份,這跟前一年其拍品成交量的拉昇不無關係,考慮到整體經濟不景氣,資源徵集愈加困難,加上重複上拍週期等問題,預計後續張大千書畫拍品全球成交量會持續走低趨勢。
張大千的潑墨山水給人直觀感受是色彩鮮亮,好比一件攝影作品,飽和度、對比度、構圖比例等都恰到好處。其色彩上的優勢主要緣於張大千用墨十分考究,拒絕使用宿墨,每次創作前都會將硯臺清晰乾淨。其山水潑墨作品中,儘管有大面積的潑彩或者墨團,但依舊給人剔透晶瑩之感,虛實相間,水墨比例控制恰當,如仙境一般,自然生動。
張大千潑墨潑彩作品的創作分為幾個時期,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50 年代中期,張大千的細筆畫風開始向減筆、潑墨潑彩等粗筆畫風轉變。他在 1956 年創作的《山園驟雨圖》成為這一時期潑墨風格的代表作。到了 50 年代後期,張大千對於潑墨尤其是潑彩的探索投入極大的精力跟熱情,畫面的抽象感更加強烈,但又不是西方印象派的簡單衍生,因為其作品中除了墨與色,還有中國繪畫中極為重視的線條,這些線條強而有力,“劃破”墨色的覆蓋,讓這種大收大放的畫風中有多了工整細緻之感,更有中國文化的意境。總體而言,張大千的潑墨潑彩作品給人透明通靈、清逸雅緻之感,他也真正完成了了中國畫在現代語境下的傳承和演進。
任何藝術家最終選擇的藝術風格必然與其所處時代、所經歷的一切息息相關。張大千最 終完成潑墨潑彩的藝術創作,是其一生所遇的必然選擇。近現代的特殊歷史環境下,所有的藝術家都會面臨中西文化碰撞帶來的不安全感,傳統 繪畫所奉行的遊戲規則被打破,原本清晰的脈絡突然間中斷,而新思想、新文化中又始終找不到自己的文化之“根”,可以說,這種心理上的焦慮不只影響著張大千,更伴隨了那個時代所有藝術家的一生。因此,“衝突”成為張大千的創作之源,解決“衝突”成為他藝術探 索的動機,並提供了無窮的動力。
自 1949 年 12 月離開成都, 張大千與家人開始了漫長的流亡生涯。因此流亡成為張 大千所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即身份的焦慮。他們先後在臺灣、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國等國家與地區居住, 其間還遊歷過義大利、法國、英國、瑞士、西班牙、日本、韓國。 而這個流亡的過程持續了幾十年,文化衝突加上身份焦慮,這雖痛苦,但卻成為張大千潑墨潑彩藝術突破的一種靈泉。
在漂泊海外的生活中,起初張大千期望透過外在的標籤來確認自己的文化身份,比如穿 長衫、戴東坡帽、說四川話、寫詩填詞等等。然而,身處異域文化傳統中,加上現實生活環境,讓處處有意透過中國文化元素,在宣示自己文化歸屬的張大千顯得格格不入,而且越激 烈的對西方文化的對抗行為,並沒有讓張大千獲得平靜,反倒讓心中苦悶加重,這對其潑墨潑彩藝術探索的影響是深遠的。1957 年,張大千在一首題畫詩《懷鄉》寫道:“不見巴人 作巴語,爭教蜀客憐蜀山?垂老可無歸國日, 夢中滿意說鄉關。”這首詩也印證了張大千的內心情緒,對家國的思念,其背後更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愛。
1953 年,張大千生活在阿根廷,期間創作了一幅頗具中國傳統文人畫審美情趣的《漁人歸去圖》,展現了一位典型中國文人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意境幽遠,山水朦朧,並題詩“流 水含雲密, 漁人罷釣歸。山中境何似,落葉鳥同飛。”該畫作同時也透漏了張大千更加傾 向於中國傳統的藝術語言。張大千在新的文化環境中,沒有立刻選擇融入西方價值系統,他始終在堅守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這也是他潑墨潑彩作品始終被中國藏家鍾愛,因為從中能 找到文化認同,找到共鳴。
如果說有誰最終幫助張大千打破這種中西文化衝突困擾,那這人一定是畢加索。 1956 年,在法國坎城附近的尼斯港畢加索的地中海式別墅,張大千與這位西方現當代藝術大師有 了一次深入的交流,而這也對張大千後來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三年後,張大千創作了《山園驟雨》這幅畫在構圖上突破了中國傳統國畫的構圖——近景、中景和遠景的組合模 式被取而代之,只留有樹枝、半邊山石、幾根細竹、疏落的水草等近景。不得不說,這幅構圖開啟了張大千探索新藝術形式的道途,醞釀出潑墨潑彩的創作風格。最終張大千完成了“以 運墨之法運石青、石綠”的轉變,正式宣告了潑墨潑彩的誕生,張大千的藝術世界更得到了 巨大的提升,這從市場成交中有所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