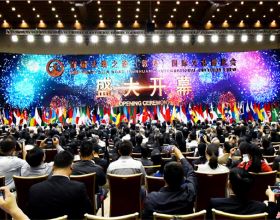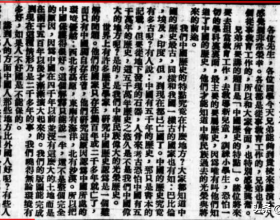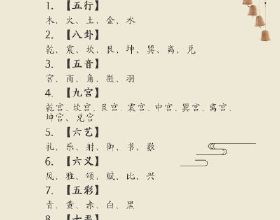俗話說:“待人三自反,處世兩如何。”這是設身處地的待人處世之金科玉律。所謂“三自反”,就是“日勤三省,夜惕四知”,亦即曾子所說的“吾日三省吾身”。“吾日三省吾身”,第一個省察、反省的問題是:“為人謀而不忠乎?”講的是工作問題。第二個省察、反省的問題是:“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講的是交誼與誠信的問題。第三個省察、反省的問題是:“傳不習乎?”講的是學習問題。從每天的工作、生活和學習這三個方面,作例行性的回顧和檢點,無非是盤點、審視這些方面可能存在的錯誤和問題,以及反思這些錯誤和問題為何發生?怎樣解決?如何修正?——這,又有何難哉?
《禮記·中庸》有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的確,君子之所以勝於常人者,乃多於日常、日用之私底下用功夫。知道“吾日三省吾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並不難,難能可貴的是把自己擺進去不斷地“三省吾身”。所以說,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文化價值和典型意義,就在於其直面錯誤和問題的勇氣與格局,在於其堅持不懈地進行檢視、反省的誠意與良知。
沒有良知就沒有反省
反省,與自省和反思語義頗為相近。據《現代漢語詞典》解釋:“自省:自我反思、反省。”“反省:回想自己的思想行動,檢查其中的錯誤。”“反思:思考過去的事情,從中總結經驗教訓。”簡而言之,反省就是反躬自省,就是捫心自問,就是良心拷問。問誰?問自己。問什麼?拷問自己身上存在哪些錯誤和問題。
為何自我拷問?出於本心本性,出於良知良能,出於道義責任。《孟子·盡心上》:“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在孟子看來,良知良能是人之與生俱來的天性本能,與愛親敬長的“仁義”之行,皆為正常人的本心本性所具有的通行天下的“達道”——亦即具有本源性與普遍性、公理性與普世性。
對於良知,《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良知:良心。”“良心:本指人天生的善良的心地,後多指內心對是非、善惡的正確認識,特別是跟自己的行為有關的。”天性善良是“仁”,辨別善惡是非是“義”。所以說,良知或曰良心的核心是“仁義”,其重心則在於“仁”。
孔子曰:“仁者,人也。”“仁”字由“人”和“二”構成,“仁”不僅呈現一個人的本心,同時也體現著對待他人的態度——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仲弓問“仁”,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用俗話來說就是“若要公道,打個顛倒”,就是將心比心,換位思考。所以孟子又把“仁義”解釋為:“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說,人要有人心,人要走人路。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良知良能是人之天性本能,為什麼還要去“發現良心”,還要去“致良知”呢?答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是說人心始終處於變化、變動之中,很容易為私慾所矇蔽,從而危殆難安。故舜帝告誡大禹,必須精誠專一,信執其中,要守護好“道心”——也就是良心、初心與正道。
正如成語“利令智昏”與“喪心病狂”形容的那樣,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有些人的良知或曰良心,在面對聲色、勢利、威福、怒愛的遮蔽、誘惑或圍獵之際,是很有可能喪失和泯滅的。守護好良知或曰良心,需要不斷地進行真誠的自我反省,需要批評與自我批評——自我批評同樣也是自我反省。自我反省就是面對自己良心的自白,是自我“良心發現”的心路歷程。
沒有反省就沒有自覺
魯迅先生寫過一篇很有名的雜文《恨恨而死》:“古來很有幾位恨恨而死的人物。”“我們應該趁他們活著的時候問他:諸公!……您在半夜裡可忽然覺得有些羞,清早上可居然有點悔麼?四斤的擔,您能挑麼?三里的道,您能跑麼?”“他們如果細細的想,慢慢的悔了,這便很有些希望。”為什麼“悔了”便很有希望?因為慚愧與懊悔,是反省反思的結果,也是自覺自律的開始。
《易經》講到人的過錯時,經常用“悔吝厲咎”四個字來概括表述,而這四個字所表述的錯誤程度卻是不一樣的。譬如,“悔”,表示懊悔、懺悔、悔恨,是認識到錯誤、對待過錯的態度——這樣,人與事的發展態勢便趨於“吉”;而“吝”則表示恨惜、遺憾、艱難,其面對錯誤的心態是“能有多大點事啊”,搖頭晃腦,滿不在乎——這樣,人與事的發展態勢則趨於“兇”。所以《尚書·大禹謨》強調:“惠迪吉,從逆兇,惟影響。”由此可見,從“悔”“吝”到“吉”“兇”,不過是人的“一念之差”。
《尚書·大禹謨》還講:“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其中損和益也是《易經》中的兩個卦:給人造成損失的主要根由多是火氣與慾望,故損卦講究“懲忿窒欲”,得力在一個“忍”字,即不要過分地放縱自己的慾望和脾氣;為人帶來補益的重要緣由多是向善而改錯,故益卦講究“遷善改過”,得力在一個“悔”字,誠如古諺所謂“迷而知返,得道未遠”。
不過,反省,悔悟,揭開自己的傷疤,往往是沉痛而且沉重的。相反,把錯誤一股腦兒地推到他人身上,問題和責任都是別人的了,那麼自己便滿臉無辜,無比輕鬆。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最應該反省和懺悔的人,要麼是大言炎炎欺世盜名,要麼是振振有詞埋怨別人,要麼是巧言令色諉過於人,毫無愧悔之心,更無悔改之意。孔子曰:“小人行險以僥倖。”然而一直心存僥倖、鋌而走險,最終還是“行”不通的。子夏亦云:“小人之過也必文。”但是始終文過飾非、自欺欺人,終究也是“過”不去的。
據《韓詩外傳》記載:“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不懂反省的人身上大多具有這種典型的“三不亦現象”:第一種是在內部搞內卷,卻到外邊去貼熱臉,這不是正好搞反了嗎?第二種是自己做得不好,卻總是去埋怨別人,這不是扯得太遠了嗎?第三種是等到禍患臨頭,才去求告“老天爺啊”,豈不是太晚了嗎?其實,這三種現象是一種密切關聯的遞進關係,而導致“三不亦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這種人從來不懂得反省,不懂得悔悟。
俗話說得好:“人勸不如自悔。”悔悟是人的一種心靈自潔功能和自我救贖功能。悔悟悔悟,一“悔”就離“悟”不遠了——“悟”就是覺悟與自覺。由“悔”到“悟”是反省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反省的全部價值和意義所在。
沒有自覺就沒有自新
我國古代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中有一種“射禮”。《禮記·射義》指出,射箭射不中靶子,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只能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去埋怨比自己射得更準的人。所以古代把“射”作為一種禮,也是為了培養人們“發而不中,反求諸己”的反省錯誤、認識錯誤和改正錯誤的自覺性和道德律。
據《新唐書·馮元常傳》記載,馮元常作眉州刺史時,劍南有“光火盜”武裝團伙,晝伏夜出,為害鄉里,“元常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就算是作惡多端的賊寇,一旦有了自覺的反省和悔悟,也會“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爭取到“悔過自新”的機會。與之相反,據《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載,漢文帝劉恆屢次寬恕吳王劉濞的罪行,希望他能夠“改過自新”,然而劉濞卻是面從心違、不思改悔,“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最終自取滅亡。可見,沒有反省和悔悟的主動性與自覺性,即使給他再多的機會、再優厚的條件,也不會真正地“改過自新”。
沒有自覺,談何自律?沒有自律,談何自新?對於自新,《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自覺地改正錯誤,重新做人。”《左傳·宣公二年》有言:“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對於“過而能改”,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待:一方面,犯錯者能夠認識到錯誤,並自覺地改正錯誤,那自然是“善莫大焉”;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形下,“能叫醒真睡的人,叫不醒裝睡的人”,犯錯者不肯自覺、自律地自新,那就需要規則和規矩來管教約束,需要運用“批判的武器”(批評教育)乃至於“武器的批判”(法律制裁)。
俗話說:“年好過,月好過,日子難過。”相對而言,年和月是抽象的概括的,而一天一天的日子卻是具體的實在的。也許人生倏忽而過,然而每一個日子卻是具體而實在的。人生,由每一個日子組成。作為社會人,有誰不生活在“比較”之中?問題是跟誰比?怎麼比?比什麼?孔子的教誨是,賢與不肖正反兩方面的“範例”都要比照——“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皋陶的忠告則是——“屢省乃成”(《尚書·益稷》),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經常自我反省,保準做啥啥成。倘若真能把兩位聖賢的“金句”內化於心,外化於行,那就有可能將人生中的諸多隱患、錯誤和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不讓“虎兕出於柙”。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反省,則日新。之所以反覆強調反省的價值和意義,並不是為反省而反省,不單單是為了追悔昨天的失誤,也不僅僅是為了憑弔過往的傷痛,而是為了更好地審視並總結今天的自己,揮手告別昨天的所有錯誤和彎路,更新自我,開拓明天的道路。(李建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