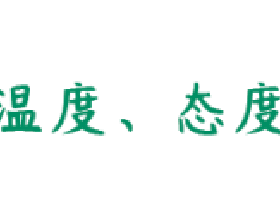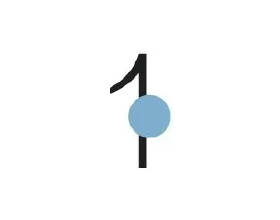梁文春
長篇小說《誰在敲門》寬闊、舒緩、靜水深流,是一部向傳統和時代致敬的小說,時代大潮丟棄的碎片,被撿拾,被細心擦拭,使之發出光彩,照亮和收容失措的靈魂。三代農民子女的命運變遷,讓人切實觸控到當下現實的溫度,有一種厚重的歷史感。
這部長篇小說出場人物有上百個,每個人物都有血有肉,有稜有角。呼風喚雨的大姐夫,被兒子丟盡臉的大哥,一毛不拔的二哥,坑蒙拐騙的四喜,早熟的聰兒,卑微的父親,等等。這些人物就像藤上的葡萄,而父親則是把他們串聯起來的葡萄藤。“父親是離世界遠了,他生日的全部意義,就是提供一個機會,讓兒孫團聚,能聚的人越來越少,表面的理由萬萬千千,最深層的,是父親正在遠離。”
小說以許家為核心,以為父親慶生至父親病重、離世為主線,描述人、事、物,如《清明上河圖》般截取了時代的一個橫切面,勾勒了大時代下的微小細節。
作者有非常鮮明的空間意識。小說以父親為核心出現三個重要的地點,一是大姐家,眾子孫為父親慶生;二是醫院,父親病重,眾子孫聚集守護或探病;三是燕兒坡二哥家,眾子孫為父親舉辦葬禮。這三個地點由封閉走向開放,由點輻射到面,就像舞臺劇中的三個重要場景,所有的矛盾衝突都集中於此,不同的人事物在同一個空間中上演,在不同的空間演繹著不同的角色。
“誰在敲門”的“門”即是一個空間概念,也是空間發生聯絡的通道。當有人在敲門時,內部的空間即與外部的世界產生了聯絡,這是一種怎樣的聯絡?在大姐家,“門”的概念是相對清晰的,空間也是相對封閉的、私密的,焦點更多集中在“家人”身上。在醫院,“門”的概念趨向於模糊,在這裡不斷上演著生與死,也預示著任何人都逃不過生與死的離別。在二哥家,“門”的概念是開放的,讓人與大千世界發生更深遠更密切的聯絡。
人的社會屬性,在有限的空間中由複雜微妙的人際關係體現出來。在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中,每個人物所擔任的角色與責任與他們的所作所為密切相關,當兩者之間出現較大偏差時,人物本身就會出現較大的張力。所以,在《誰在敲門》中,每一個人物的刻畫都讓人印象深刻,就如作者本人所說,小說裡的人物不是塑造出來的,是小說自己長出來的。
十多年前,羅偉章創作了《飢餓百年》,如今創作了《誰在敲門》,我心中疑惑,《誰在敲門》的“父親”形象是否是《飢餓百年》裡“父親”形象的延續?
對此,作者並不否認:“《飢餓百年》中的‘父親’是終點,到《誰在敲門》,就成為起點了,而這個起點恰恰成為‘父親’人生的終點。
作者在《後記》中也曾提到,“《飢餓百年》是山的文明,《誰在敲門》是河的文明”。山與河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描寫的是傳統文明,後者是現代文明,兩者之間是骨肉聯絡。在《飢餓百年》中,“父親”及爺爺的一輩,乃至祖上一代代人終其一生都在為土地而奮鬥。到了《誰在敲門》,土地對人的束縛已走向瓦解,大時代的洗禮悄然改變著每一個農民子弟。
羅偉章對於平凡人的一生力透紙背的書寫,讓讀者看見每個人物身上的卑微與崇高,也看見了自己身上的卑微與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