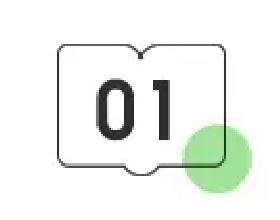作者:林培源
1.和上一部小說《在南方》(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書寫美國南部故事不同,張惠雯的小說集《飛鳥和池魚》(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將“異域”目光拉回中國,講述地地道道的“縣城故事”。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部新作視為尋常的“縣城故事集”,它的別緻和新意,體現為灌注其中的“在地者”的自我審視,以及“身在異鄉為異客”的“還鄉者”對故鄉的回望與哀悼。在這部小說集裡,“異域體驗”和“在地經驗”如同顯微鏡的目鏡和物鏡,成為觀照和勘測縣城社會的有力工具。
我們知道,“還鄉書寫”早在“五四”時期魯迅的小說(譬如《故鄉》)裡就已成型,並延展為貫穿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種敘述模式(關於這點,宋明煒為《飛鳥和池魚》所作的序中有所提及)。如果說一百年前的還鄉小說是出於“僑寓者”對邊地和故土的凝望,它們尚披著國民性批判與“啟蒙”意識的外衣,那麼在張惠雯筆下,這一層外衣早已剝落殆盡,此時的還鄉書寫充滿的是陌生化色彩。“今昔對比”與思辨性的“對耦”,堪稱這部集子最大的文學特色。
所謂“今昔對比”和思辨性的“對耦”,首先歸結為一種“回憶”的書寫結構:過去與現在的重疊、關聯,青春往事與中年心境的遙遙“對望”,這些如同映象或穹頂,在映照小說時間紋路的同時,撐起了小說的敘述結構(《昨天》和《良夜》兩則故事可視為這方面的“姐妹篇”,而《關於南京的回憶》則是一場徹徹底底的對青春往事的“復原”);其次,這些故事裡,作為還鄉者的主人公,大多旅居國外多年並歷經滄桑:他們要麼被迫離開那個“更好、更廣闊的地方”,回到“小地方”(縣城)照顧年邁、患有精神疾病的母親,在現實的泥淖裡掙扎,終於理解了“飛鳥”和“池魚”的苦樂(《飛鳥和池魚》);要麼是返鄉為父親料理後事,卻囿於親人的唯利是圖而落入“虛空”,只能依靠與青春時期的愛慕物件“偷情”而獲得寬慰(《天使》);要麼則像《昨天》和《良夜》的主人公一樣,返鄉後與昔日友人重逢,不管這些人物身份多麼迥異,作為離鄉者,他們在情感上對故鄉小城的隔閡和疏離總是高度一致的。
這也是為何在這部集子裡,張惠雯會如此頻繁、密集地書寫“深淵”的意象:
《飛鳥和池魚》裡的“我”無意間看到了母親的日記。這些日記出自一位記憶衰退、混淆了現實和幻想邊界的老人之手:“那裡面充滿了我聽不到的聲音、我所不知道的陌生來客以及我父親這個鬼魂對她的秘密拜會、擠在窗戶上面的朝她窺視的小臉兒、站在雨地裡的淋得精溼的透明人……”“我看著這些句子,它們來自失序的意識的深淵,卻具有某種毒藥般的詭麗。我不能看太久,否則我覺得自己也會被這股黑暗的旋渦或是潛流捲到另一個世界裡去”。此處的“深淵”既指向母親心底的秘密,也指向她寄託在文字裡的深深的孤獨。
在《漣漪》中,步入中年的評論家多年後重返年輕時待過的城市,憶起當時與出軌物件共處的時光,“我覺得身體有種輕飄飄的感覺,像是站在懸崖邊,在我面前是整個回憶的深淵。回憶和窗戶外面的世界那樣發著光、令人暈眩”。這裡的“深淵”又是故地重遊時內心蕩起的漣漪,它關聯著激情和冒險,透著懷舊的、頹唐的氣息。
在《臨淵》中,作為小城“失敗者”的青年主人公偶遇獨自垂釣的老教師,老教師熱忱地介紹起他的女兒,而“我”則向老教師虛構了自己的情感故事,待到離開時,“我”才被前同事告知,多年前,老教師的女兒在美國求學時被男友槍殺了。這些年來,老教師隨身帶著貼有女兒獎狀和簡報的剪貼本,逢人便反覆訴說,似乎藉此可以讓死去的女兒復活。在瞭解了老教師的悲慘遭遇後,“我”領悟到:“當一個人彷彿懸浮著,當你飄在無論是語言、幻想還是現實喧囂、慣性的浮沫上,即使你的下面是生活的整個深淵,那種載浮載沉、置身事外的感覺也能讓你多多少少感到解脫。”對老教師而言,垂釣(即“臨淵”)是排遣孤獨的方式,向陌生人講述女兒,則是另類的寄託哀思。但他是否從中得到解脫?我們不得而知。
對上述幾篇故事而言,“深淵”經由作者的反覆渲染和勾繪,已增殖為一個繁複的意象。我們很難說,它就是尼采那句“與魔鬼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魔鬼;當你遠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在文學層面的轉寫或迻譯;或者,“臨淵”在此處已成為一種寫作的姿態,成為小說賴以存在的哲學基底。
2.如果要在《飛鳥和池魚》中找出一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恐怕非《街頭小景》莫屬。在這篇小說裡,“我”從熱帶國家飛抵中原小城陪母親過年,患了一場嚴重的感冒,養病期間,“我”待在家中讀一本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契訶夫短篇小說集》。契訶夫在此處現身並非毫無來由——“我”覺得自己“就像契訶夫小說裡描述的一百多年前的人,從彼得堡或是莫斯科回到自己外省小城的家鄉,對一切陋習不滿,變得憤世嫉俗”,面對小城的陋習和世相,“我”憤懣,又無力改變,判定自己不過是個“多餘而無用的人”(和《臨淵》裡被父親貶為“廢物”的青年人異曲同工)。
這裡的“街頭小景”亦是契訶夫式的,“街頭”意味著流動和偶然,“小景”意味著稀鬆平常。換言之,這篇小說裡沒有曲折鋪張的戲劇衝突,“小故事”與“大背景”以一種自然、貼切的方式關聯著、凝結著,所有的情感、批判和思考皆是從日常生活裡飛昇起來的。
小說由兩處“街頭小景”構成,如同一幅勾繪出縣城眾生相的速寫畫,人心的淡漠、人性的自私與殘忍,被收束於契訶夫式的希冀與憂愁之中。此處出現了兩重視角,一是“契訶夫式”的對“眾生”的凝視目光,寥寥幾筆,沒有起伏跌宕的情節,卻賦予小說穿越時空的雋永和淡然;一是“我”作為返鄉者對故鄉的審視,由此生出一種“不可理喻的希冀”。
3.我們或許可以將“契訶夫”當成理解《飛鳥和池魚》的線索。除了《街頭小景》,在這部收錄了十個短篇的集子裡,契訶夫的影子和蹤跡也偶有閃現,《昨天》援引了契訶夫《我的一生》的句子作為題記,而《漣漪》則在結尾處迴盪起契訶夫的追問——“米修司,你在哪裡?”它們如同微光照亮了人物晦暗的內心和意識。
《我的一生》是契訶夫1896年的小說,主人公米賽爾是個貴族出身的青年,但他卻對被父親視為“代代相傳的聖火”的社會地位極度不滿,認為這一切不過是金錢和教育換來的特權。米賽爾說:“大衛王有一個戒指,上面刻著幾個字:‘一切都會過去’……要是我有心給自己定做一個戒指,我就會選這樣一句話來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會過去’。”《昨天》題記援引這句話,是為了凸顯這樣的道理:對小說人物而言,記憶、初戀的美好、曾經的遺憾,如同鋼針一樣扎進人的內心深處,永遠不會過去。
去國離鄉二十年後,已在國外大學任教的“我”歸鄉,見到曾經愛慕的女生,此時她早已和高中的同學、玩伴結婚,在同一所高中任教。三人相聚,“我”在這對昔日友人的要求下,彈奏了一曲甲殼蟲樂隊的《昨天》。曲畢之後,“我”陷入惘然。當“我”意識到已經顯出“初老的跡象”的女同學成了普通的縣城女人——“我們的生活、精神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交集”時,“我”對寄寓了美好和青春的“昨天”生出厭煩,覺得它頑固,停駐在那裡不可撼動;當“我”試著尋找“昨日”,“昨天”已不可抵擋地被時間和記憶修改了,再也無法抵達,最後“我”和昔日的愛戀物件只能在默然和尷尬中匆匆告別。
這樣的“昨日”也出現在《漣漪》裡,後者結尾那句“米修司,你在哪裡?”,出自契訶夫另一篇名作《帶閣樓的房子》。在這篇故事中,畫家和天真爛漫、春心甫露的女子(被家人親切地稱為“米修司”)的戀情淪為一場空,畫家對“米修司”的呼喚,代表的是對過往的眷戀。而在《漣漪》中,評論家憶起多年前那場婚外情,在家庭倫理和道德準則之間擺盪,就在評論家準備回家向妻子坦白一切時,妻子卻告知自己懷孕了,命運的玩笑將評論家擊倒,他不得不背叛了對戀人許下的承諾。這裡,“米修司”已晉升為一枚符號,契訶夫如同站在這些小說背後沉默注視一切的人。
可以說,在故事層面,“臨淵”是小說人物精神和意識的標籤,它經過時間和記憶的萃取後,成為不可剔除的“剩餘物”留存在底部;而“契訶夫”則不妨視為某種寫作的“方法論”,它的存在貫穿於這批小說的前後,使得他們擁有相似的氣息和統一的敘事風格。這種風格,體現為張惠雯小說所具有的罕見的“剋制”——即便其中偶有抒情和寫景的片段,也是張弛有度的,張惠雯不放任情感肆意流淌,她的敘事自始至終以流暢、剪裁得當的方式穩步推進。這是當代中國作家中頗為難得的品格,也是屬於小說家的美德。
更值得注意的是,張惠雯旅居海外多年——她的寫作早已被文學研究者和評論家歸入“海外華文文學”的譜系中,但她並不侷限於特定的空間和地域範疇,而是試圖糅合不同經驗,將其衍化為複合的小說風格。在新作《飛鳥和池魚》中,“在美國”與“在縣城”以某種和諧的形式共處著,成為彼此的映象,閃爍出別樣的光芒。
來源: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