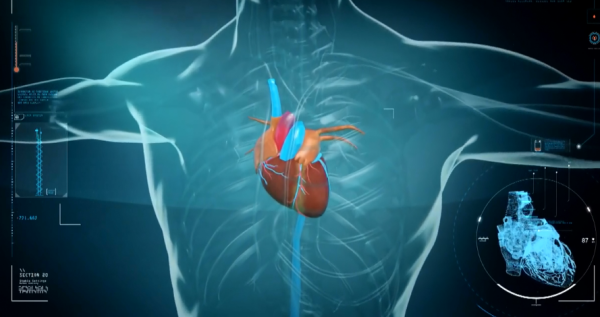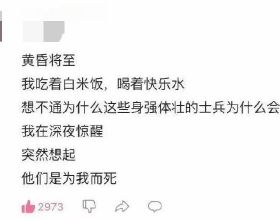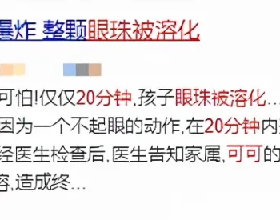因為吃了一頓海鮮,鄒磊直接躺進了醫院。那天是他的二十四歲生日,他出去和朋友慶祝,點了不少海鮮。
當時,他就感覺海鮮有點不新鮮了,但鄒磊捨不得浪費這個錢,還是吃了很多。他哪裡知道,會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第二天他就發起高燒,繼而就是下消化道大量出血。在當地醫院,治療三天沒有效果,他被緊急轉入了瑞金醫院。
鄒磊的媽媽怎麼也想不到,她養了24年的兒子,只是出去吃頓飯就陷入了生命垂危的險境。她只能在病房外不斷祈禱,希望上天垂憐,能讓她的兒子脫離生命危險。
因為下消化道大量出血,鄒磊的血壓極不穩定。毛主任決定冒著巨大的風險,給他做血液淨化,排掉身體裡的毒素。這個方法極為冒險,對鄒磊而言,可能是救命稻草,也可能是致命毒藥。
在全身大出血,凝血功能又差的情況下,機器一開,有可能反而會加重病情,導致死亡。一息尚存,醫生就不會放棄。這場與死神的博弈,在機器的啟動聲中拉開了帷幕。
由於病人體內大出血,再加上血液淨化需要消耗大量鮮血,搶救室緊急從血庫調來了大批血製品。剛到的血很涼,血液加溫器還來不及調配,醫生們就用體溫去溫暖這些救命的血液。帶著醫生體溫的血液,源源不斷輸入了鄒磊體內。
經過八小時的搶救,鄒磊的家人迎來了第一個好訊息:
“就是我們看到了一線希望,氧飽和度上來了。只能說是沒有想象的惡化,反而開始有一點點跡象的好轉。”
毛主任小心翼翼地措辭,他不敢給家屬太多希望,因為病房內的變數太多太多,誰也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
醫生搶救了他八小時,剛出現一絲轉機,下一秒他瞬間出血一千毫升,這是醫生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大量的出血意味著,鄒磊的上消化道出現了應激性潰瘍。
毛主任趕緊讓血庫送血,但血庫的血源緊張,只能給他們兩個單位。毛主任只好親自打電話去要。
“你再給我四個單位,可以吧,對對對,沒辦法了,兄弟,24歲啊,24歲啊”
終於,在毛主任的努力下,血站撥了800毫升鮮血。血液淨化的流量開到了最大,不間斷地衝洗消化道,輸血速度也開到了最大。所有的醫療措施、搶救手段都毫無保留地給他上了。醫生們都想把這條24歲的年輕生命從死神手中搶來,但他們還是失敗了。
“其實我們從七點鐘就開始了,一直在搶救他。我們也無能為力,也沒辦法,到這個地步了。”
車在前醫生已經48小時沒閤眼了,他參與了三場搶救。除了鄒磊,還有一位80歲的男性患者和一位70多歲的女性患者,三個人中只有最年輕的鄒磊沒有搶救回來。車醫生不知道如何去安慰鄒磊一家,只能默默守在病床旁。
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這恐怕是對醫生最好的解釋。有時候,他們拼盡全力搶到了一次機會,還是闖不過最後的難關。
對於他們來說,最困難的不是面對失敗,而是面對失敗帶來的挫折,依然能重拾最初的那份熱情去面對更大的難關。
27歲的王建輝,就是他們的新難題。他的右心房長有惡性腫瘤,已經去了好幾個醫院了。但他的腫瘤情況複雜,甚至有醫院開啟胸腔後,發現無法切除,又把他關上了。
這等於是給他判了死刑,但是來到瑞金醫院後,趙主任聯合多個科室聯合會診拿出了一個治療方案:心臟移植。
“一般來說,有100個等待心臟移植的病人,大概只有一個人有這樣的機會。”
27歲的王建輝很幸運地成為了百分之一,常州人民醫院的一位50歲的腦外傷患者已經腦死亡,家人願意捐出心臟,王建輝獲得了這次移植的機會,這也是他唯一活下去的機會。
時間緊迫,心臟外科的兩名醫生第一時間開車,從上海奔赴到常州市人民醫院。晚上7點49分,寶貴的心臟被摘下,生死時速開始了。
“我們認為比較安全的心臟移植,大概四到六個小時以內。”
所以他們必須儘可能快地趕回上海,給王建輝帶回生的希望。心臟離王建輝越來越近,225公里、125公里、40公里,到最後不到100米。
為了節約時間,醫生拎著存放心臟的儲存箱狂奔。終於,心臟離王建輝不到兩米了。趙醫生開始切除心臟,準備進行移植。
這就是那顆寶貴的心臟,在醫生眼裡,它溫潤、光潔、神聖,是一個生命饋贈另一個生命的禮物,更是王建輝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這場移植手術與以往不同,為了儘可能切除腫瘤,趙主任在在切除心臟時,沒有預留連線供體心臟的主動脈和下腔靜脈等介面,這大大增加了手術的困難。
凌晨一點半,手術已經進行了五個小時,50多歲的趙主任不吃不喝,依然鎮定指揮著手術。移植的心臟開始紅潤,在王建輝的胸膛裡跳動起來。他們勝利了,從死神手裡搶回了王建輝。
“手術非常成功,比預計的要複雜,要難。心臟外科生涯裡面,我做了大概80例的心臟移植病人裡面,這個是我第一次這樣做。我們付出的努力,會有回報的。”
沒人知道趙主任是帶病上的手術檯,他得的是直腸末端靜脈曲張,也就是我們說的痔瘡。久坐久立,是痔瘡的主要誘因。對於天天站立在手術檯旁的外科醫生來說,這幾乎等於他們的職業病。
手術的成功、病人的康復,這些都離不開醫生的付出。他們跟生命賽跑、與死神博弈,一次又一次帶來生命的奇蹟,是當之無愧的白衣天使。
我是樸叔 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