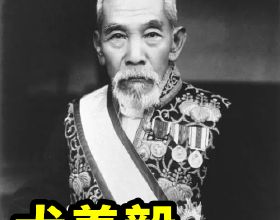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羅工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經典回放
油畫《地道戰》的場景設定在晦暗狹小的牛棚裡,畫家充分利用虛實對比、光線的明暗處理等手法,破除了空間限制,給人以“一目瞭然”的觀感。在畫面的視覺中心,畫家以中間亮、四周暗的舞臺追光手法,將手持駁殼槍站立的女民兵形象突出出來。另一個正從地道口躍出的女民兵,也被追光照亮,連同隱沒在黑暗中的老者,也因為光線的處理,變得生動起來。同時,畫家巧妙地運用人物向上、向外的視覺方向以及體態動作,拓展了畫面的空間。畫面中,除了往上遞手榴彈的民兵,其他民兵的視線都朝向右方,而畫面右方計程車兵正在觀察外界的情況,讓觀者的焦點有了向外的聯想與延伸。狹窄黑暗的空間與人物飽滿的身姿形成反差,卻也構建了視覺上的和諧。為了表達正義的信念,畫家將畫面處理為柔和的暖色調,天窗投射的光線以及身著紅衣的女子,洋溢著溫暖的感覺,渲染出光明必勝的堅定意志。
羅工柳創作的《地道戰》,在中國當代油畫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不僅是一幅構建國家敘事視覺美學的典型作品,也塑造了幾代中國人的革命藝術共同記憶。
2014年,我在策劃由中國油畫學會和中國美術館聯合主辦的“在場·第二屆中國油畫雙年展”的過程中,試圖探索如何透過展覽去構建國家敘事的視覺美學,即讓觀眾在走進“藝術殿堂”,瞭解中國藝術歷史“真相”的同時,去觸控有溫度的歷史“在場”感。畫框中的藝術、散落於畫室角落的張張草稿以及檔案和研究文獻,都是我復原“面向藝術本身”的起點。羅工柳的《地道戰》草稿便成為重要展品之一。尋找其寫生稿和創作草稿,也成為我的必然選擇。
羅工柳早年的藝術經歷與國運、時運休慼相關。1951年,第一次拿起油畫筆的他就創作出了《地道戰》。地道戰是抗日戰爭時期,在華北、冀中平原上,抗日軍民利用地道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作戰方式。
剛開始創作時,羅工柳憑著想象和前線生活經歷打了幾份草稿:先是把場景侷限於室內,地道的出入口設於灶臺中;後又嘗試加入連線外部院牆的梯子,將地道口置於牲口棚頂,試圖將場景向外部空間轉移;最後,他帶著草稿來到河北的一個村莊,請教當年參加了地道戰的民兵。民兵看了草稿表示畫得不對,洞口應該向低處開,這樣既隱蔽,又能有效快速地殲滅敵軍,這種設計是他們經過血的教訓改進出來的。羅工柳為此深受啟發,感慨道,美術創作如果不真正深入生活,怎能畫出站得住腳的作品?他靜下心來,進一步瞭解當年地道戰的真實情況,在村莊裡畫了大量速寫,最終把地道口改在一間普通的牲口棚內,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地道戰》定稿。
羅工柳在修改草稿過程中,不斷加深自己對地道戰、革命鬥爭實踐的認識。這也是我想要展出這些珍貴草稿的原因所在。
“在場”是在重建一種現場感,一種多聲部與主旋律的關係,是“觀念”的和聲或變調,是歷史與現實的對照。羅工柳《地道戰》的寫生稿和創作草稿,回溯了他當年為了使作品畫得真實、聽取參戰民兵意見,並不斷修改草稿的過程和情境,進而讓今天的觀眾感受到羅工柳在創作中不斷演進的節奏和細節處理中呈現的生動。如此重建藝術同戰場之間的關聯,促成對話,讓觀眾感受這位充滿革命理想的藝術家的精神溫度——“我不懂,是老百姓教了我才畫出了《地道戰》”。
羅工柳本土油畫“在場”的起點或許可追溯到20世紀早期。當時,一些畫家的油畫被稱之為“土油畫”,但西洋油畫的構圖、造型、色彩等藝術原理已然被運用在畫面處理中,其中不乏西洋畫的基本審美。畫家們也試圖在寫生和創作中融入中國畫的筆法,將油畫與中國本土審美融合。
羅工柳當年完成《地道戰》後,就有人說這是典型的“土油畫”。在他赴蘇聯列賓美術學院求學時,其他同學都被分為本科生或研究生,只有他沒被分配。羅工柳不明所以,帶著這幅“土油畫”的照片去找教授。教授才道明:他的“土油畫”具有中國民族特色,一定要好好堅持和發展;若在此學習,看似可以掌握蘇聯油畫的風格,卻可能丟掉中國“土油畫”的特質。儘管如此,羅工柳仍然堅持留在蘇聯學習。教授認為,他的水平已經高出本科生和研究生,就讓羅工柳以進修生的身份留了下來。
今天,我們回望這個“土油畫”的故事時,或許會有人產生疑問:當年的“土油畫”為什麼能夠得到來自世界頂級藝術殿堂的讚譽?我認為,所謂的“土”是相對“洋”來說的。羅工柳在敘述“地道戰”這一歷史事件時,懂得在西洋油畫語言中加入中國本土繪畫語言,巧妙地把二者結合,重建藝術作品與現實社會語境之間的關聯。最重要的是,羅柳工的畫傳遞出一種崇高而生動的歷史感,充滿凝聚人心的力量感。這種打動人心的視覺美學是無遠弗屆不論土洋的。
事實上,國家敘事的視覺美學就是要把國家的形成與建設,用具有敘事性、場景性、時代性、抒情性的畫面呈現出來,以視覺的形式表達、凝聚、塑造人民的歷史記憶和家國情感。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之際,重溫中國美術史中的經典——羅工柳的油畫《地道戰》,再次從中汲取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的養分,對當下美術創作有著不可忽視的啟發意義。作為親歷者,羅工柳重塑了革命歷史的“在場”,以《地道戰》為代表的重要作品,成為表現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的重要載體。今天的主題性創作,美術家不僅要表現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還要以生動有力、具有歷史感的表達,為人民留下時代見證,鼓舞和凝聚人心,召喚美好的未來。唯有這樣的藝術才能成為國家敘事,才是具有人民立場的美學。
(作者為中國美術館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