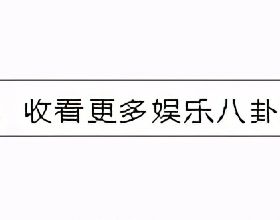他瘦高個,穿著球鞋和牛仔褲,和劇組的年輕人聊天。正在排練的是椎·劇場話劇《爸爸的床》,他演一個失去了妻子的男人,一個平凡的父親。
整場戲只有父親和女兒兩個角色,90分鐘未曾謀面,從頭到尾都在電話裡交談、討論、爭吵、沉默,極其考驗演員的功力。
出演《爸爸的床》,讓王學圻想起年輕時在空政話劇團和濮存昕、李雪健一起跑龍套的日子。
那時候,節目單裡永遠找不到他們的名字。他們演過“紅軍甲”,演過“匪兵乙”,後面寫的都是“本團演員”四個字。有時候一句臺詞也沒有,最出彩的只是一個背影。直到話劇《九·一三》,王學圻才摘掉了龍套的帽子。
1984年出演陳凱歌電影《黃土地》後,王學圻逐漸從舞臺走向大銀幕,在《大閱兵》《梅蘭芳》《十月圍城》《日照重慶》等電影中塑造了深入人心的角色,修煉成“老戲骨”。
當年,沒有“天價片酬”,也沒有“頂流”。王學圻說,那時候只有熱愛表演的演員,踏踏實實演戲,誠誠懇懇做人,塑造每個角色之前都會花時間去體驗生活,“懂了”再演。無論角色大小,反覆探索,字斟句酌,這樣的習慣他保持至今。
從藝多年,對演員王學圻來說,角色永遠很複雜,但生活始終很簡單。
這樣的故事,全世界都在發生
上觀新聞:很多年沒演話劇了,這次為什麼會演《爸爸的床》?
王學圻:首先本子我一看,很喜歡。它在形式上恐怕是獨一無二的,光靠父親和女兒打電話,撐起了整個一齣戲。因為故事裡的妻子去世了,父親和女兒又沒住在一起。父親總在把過去裝進盒子裡,想要扔掉。可女兒永遠要把過去留下來,要活在其中。
我看本子有個標準:一定得自己先感動,不然沒法兒演。《爸爸的床》打動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兩個字——真實,它寫的是我們千家萬戶的故事,甚至於我覺得每個家庭都說過這樣的臺詞。它提醒我們,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要忘記親情是多麼重要、多麼溫暖。因為不管你多大了,想起父母,永遠是非常溫暖的一段回憶。
上觀新聞:這個戲讓人想到義大利作曲家梅諾蒂的歌劇《電話》。一個女演員從頭到尾一直在打電話,但是透過打電話就把她的故事很巧妙地表現出來了。
王學圻:對,有一些形式你覺得很簡單,很極致,做好了確實是個好東西。其實,我一開始看了《爸爸的床》也很猶豫,因為光靠對話、沒有接觸的戲劇,會不會太簡單?但其實,這給我們兩個演員,給德國導演馬丁,還有法國的舞臺設計師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你不會覺得單調,一定會被它打動。
上觀新聞: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創作班底?
王學圻:是的,劇本是荷蘭作家寫的,它的邏輯、語言節奏,會讓你感覺是發生在國外的故事,但用的又是中國人能聽懂的語言。兩個人的對話很簡單,臺詞翻譯得也地道,很有煙火氣,很熟悉。其實這樣的故事,全世界都在發生。
上觀新聞:您自己和兒子多久打一次電話?
王學圻:我兒子和戲中角色很像,每次打電話都一樣:“爸,怎麼樣,拍什麼戲呢?累不累,多注意身體啊,吃好飯睡好覺,有什麼事打電話。好,再見再見。”沒別的。因為我不知道他在幹嘛,他也不瞭解我具體在幹嘛。
我當時看完《爸爸的床》劇本,在車上跟大家說起來。司機馬上就說:“王老師,我跟我爸也這樣。我說‘你幹嘛呢’,他說‘我養花呢’。‘種了些啥?’‘種點蔬菜,茄子什麼的。’‘哦,你注意身體啊。天下不下雨?’‘不下。’‘不下雨還行,您注意安全。’”完了。
上觀新聞:跟我和我爸的對話一樣,因為分開太久了,每次見面,他們講的都是我高考之前發生的事。
王學圻:因為你大學以後每天干啥,他不知道了。我也是一樣,說起來全是過去,所以老說老年人愛回憶。他不愛回憶,他是隻知道過去,不太瞭解現在。
上觀新聞:所以兩代人之間好像真的很難達成真正的理解。
王學圻:是。因為一個在積極創業,不停地解決各種困難;另一個在延續自己的生命,需要陪伴。可是孩子太忙了,不可能給他們陪伴。這個戲好就好在,沒有對任何一方有過分的譴責,只是把這件事說出來,理解他們,同情他們。其實沒有很好的辦法。親情或許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能成為解決問題的勇氣。
真正過癮的還是舞臺劇,一氣呵成很難
上觀新聞:演舞臺劇和演影視劇有什麼不一樣?
王學圻:我是演舞臺劇出身的,舞臺是其他藝術形式代替不了的,它對一個演員的鍛鍊太大了。演舞臺劇和演電影不一樣,你必須從頭至尾完全地暴露在觀眾面前。
真正過癮的還是舞臺劇,一氣呵成很難。好也罷,壞也罷,有觀眾最直接的反饋。我覺得演員要在舞臺上多練練,是提高演技的一個好方法。舞臺帶給我很多榮譽,也帶給我很多教訓,這都是好事。
電影是遺憾的藝術,因為只能演一遍。可是在舞臺上,今天可以演成這樣,明天可以演成那樣,總有上升的空間,總有完善的可能。我一直夢想著回到舞臺,重新去檢驗自己,提升自己,現在實現了。
上觀新聞:演《爸爸的床》的時候,有沒有想起您以前在空政話劇團的日子?
王學圻:一站在舞臺上,我就想起當年在舞臺上是怎麼過來的。舞臺上那些委屈、那些失落、那些痛苦,甚至於那些迷茫,都想起來了。
那時候,我跟小濮、雪健,我們仨是“龍套鐵三角”。一齣戲我們一個人能演四五個角色,臺詞一句都沒有。但我們也覺得很熱鬧,比男主角還熱鬧,因為演完一個角色就到後臺換裝,再上臺。有時候我們會自我安慰:誰是主角啊?咱們就是主角啊,你看咱們多少套衣服,一二十套,主角才兩套。
有一回終於分到一句臺詞,就一句,我們仨琢磨半天。正琢磨著,人家問:“你們幹嘛呢?”我們說:“我們琢磨怎麼演呢。”人家說:“別琢磨了,走過去就完了。”但我們仨都很興奮,天天想著要琢磨“透”,怎麼演更“搶鏡”一點,更有辨識度。
上觀新聞:那些日子對您來說意味著什麼?
王學圻:那時候就是一種積累和鍛鍊的過程。你演完下臺,會有很多老前輩給你說戲。那時候沒有那麼多名利來引誘人,影視行業也沒那麼發達,演戲只是喜歡。就覺得咱現在不如人家,要好好學,天天演,鍛鍊自己。那時也不覺得苦,雖然都是跑龍套,但是跑得認真,跑得勤懇,跑得滿懷希望。
現在回過頭看,咱們演員必須要經過這一步。什麼叫塑造角色?怎麼才能演好角色?一步一步學習、鍛鍊,才會進步。
大家一起過著苦日子,但個個心懷理想
上觀新聞:1984年演《黃土地》是您第一次觸電?
王學圻:對,《黃土地》。當時也不懂,真不懂,你要說懂那是裝的。就覺得這片子不一樣,跟別的片子不一樣。
上觀新聞:有什麼不一樣?
王學圻:敘事、對白極其簡潔。
《黃土地》裡我第一次見翠巧,她給我打一盆洗腳水。我洗腳的時候就問她:“咱吃井水?”她說:“吃流水。”“河裡擔?”“嗯。”“道遠?”“不遠,十里。”十里地擔個洗腳的水。你看它詞兒寫得多好,簡單至極。她爹進來一看我猶豫沒洗,就問:“水不熱啊?”再往裡加。這是農民的那種寬厚、樸實。當時沒理解這麼深,後來覺得這個電影能成精品,靠的就是這些東西。
上觀新聞:當時有沒有想到它會成為“第五代”導演開創性的作品?
王學圻:沒覺得。那時候我剛剛接觸電影,就覺得每天管吃管住,挺好。
拍《黃土地》時我的第一個鏡頭,一大早,要一口氣跑到半山腰上。那時候沒有對講機,拿一小紅旗指揮。跑了好多遍,冷,頭暈,缺氧。當時我心裡就想:“不拍了,太難受了。”可是拍完我跑下來的時候,看見凱歌和藝謀含著眼淚和每個人握手:“謝謝,謝謝你們!”看到我過來,就擁抱我:“學圻,謝謝你!”我當時就覺得這事兒太崇高了,還得繼續拍。
上觀新聞:是什麼成就了《黃土地》?
王學圻:那是我第一次和“第五代”導演拍戲,當時就覺得他們認真、執著。這種東西讓我一輩子都要記住,也潛移默化到骨子裡面了。
我記得,有一次在廣州住一個酒店,50元一晚,大家都嫌貴。4個人擠在一個標準間裡,加了一張床,還有一個人要睡地上。那時候很簡單,大家一起過著苦日子,但個個心懷理想。我覺得不可能再有那種狀態了,不可能有了。
演完《黃土地》,其實大夥也不認識我。連我們團裡的人,也是後來才知道,哦,《黃土地》是王學圻演的。
不能化妝、造型哪都像了,就你人不像
上觀新聞:後來您又演了很多部陳凱歌導演的作品,哪個角色印象最深刻?
王學圻:如果沒有陳凱歌的話,就沒有現在的我。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對人物的理解、對劇本的審視。他在我身上也做了很多嘗試。《梅蘭芳》裡的十三燕是京劇名角,《搜尋》裡我是一個公司大佬,變化很多。
陳凱歌的臺詞,沒有廢話,而且很深刻,有琢磨頭,你會反覆去想,久久不能忘。你看,《黃土地》的臺詞,我現在還記得,包括1986年的《大閱兵》臺詞,還能背出來,因為我當過兵,所以非常有感觸。
“是大寒大暑大飢大渴雨雨風風,家事國事天下事都在我心中。軍人的苦,軍人的光榮,為中華壯大,為天下太平。我要說一聲,好男要當兵。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準備犧牲,萬千男兒上陣,能有幾人生。軍人的苦,軍人的光榮,為中華壯大,為天下太平。我要說一聲,好男才當兵!”是不是寫得好?
上觀新聞:這麼多年了還沒丟掉,不容易。這些角色裡最難的是哪個?
王學圻:每個角色有每個角色的不同,還有每個角色的困難。演《梅蘭芳》裡的十三燕,很難,首先技術上就難。我不是唱京戲的,但是我又演一個名角。其實在臺上唱沒那麼難,哪個難啊?生活裡難,生活裡要一看就是梨園行的掛相,這個很難。
2007年大年初四,我到了京劇名家李舒老先生家裡,拜他為師。我從跑圓場、整雲手、甩髯口開始,練了4個多月。《梅蘭芳》中的所有京劇戲份,都是我自己演的。第一個鏡頭,我就拍了37遍。
我曾向陳凱歌提出,最好能備一個京劇替身,導演也答應了。等拍完之後,陳凱歌才告訴我,其實他根本就沒準備給我找替身。
演京劇名角,就得慢慢去了解梨園老前輩的言談舉止,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行裡邊這些人情世故。多少都得了解,才能明白,為什麼要當角兒,怎麼才算角兒。
演《梅蘭芳》時,我把它當作演藝人生中的最後一次機會。它對我自己來說是一次突破。演完《梅蘭芳》,我覺得那是我最好的時候,我應該珍惜機會,好好拍點戲。
上觀新聞:所以,您進入每個角色還是靠觀察、靠生活閱歷?
王學圻:是的,塑造角色,本身需要演員花費大量的精力去體驗和感受,你的表現手法、你的狀態都在裡面。以前就靠體驗生活來塑造角色,不體驗我根本不瞭解,裝不出來。《黃土地》也好,《大閱兵》也好,《搜尋》也好,靠的還是對生活的觀察和理解。現在很多作品,為什麼觀眾不太愛看?演一個角色不能化妝、造型哪都像了,就你人不像。
好演員要在銀幕上發光,在日常生活中“隱身”
上觀新聞:您覺得怎麼樣才算好演員?
王學圻:演員的職責就是把戲演好,一定要進入角色,讓你演的角色真實可信。當然,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還是得“悟”。還有一個,演員要有經歷,經歷是演員最大的財富。你經歷過,演起來就有感覺,狀態就對。
你把角色吃透了、演好了,觀眾相信了,我覺得就是好演員。當然,這次是好演員,下一次未必就是好演員。誰能保證10部戲都是最好的?一個演員一輩子能有幾部好作品,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很多演員,他們看上去不像演員。有人說,演員走在大街上,在人群裡不顯眼,看不出來跟別人有什麼區別,這才是好演員。一個好演員要在銀幕上發光,但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隱身”。
上觀新聞:去年您在《故事裡的中國》裡出演鍾南山院士,很多網友說,無論外形還是氣場,都是“神還原”。
王學圻:首先,我不能跟人家比。鍾南山院士對社會的貢獻太大了,我只是有幸參與還原一下那段歷史,讓大夥不要忘記,在最艱苦的時候,有這麼一個人叫鍾南山,他像一顆定心丸,給很多人以信心去戰勝疫情。
上觀新聞:演這樣一個離我們很近的人物,會不會更難?
王學圻:會。尤其大夥都很熟悉,這難上加難。所以我壓力也很大,但時間又很緊,容不得你多想。我也非常感謝鍾南山院士送了我一本簽名畫報,他說他們家人都認真地看了。他還開玩笑說:“你走道不像我啊,我走路帶風。”
他天天健身,我也是。其實我那不叫健身,叫活動,但一直在堅持。我演過一個電影叫《天地英雄》,演安大人,土匪首領。裡邊有我赤裸上身的戲,演完之後,我們團裡的人都沒想到我會有那樣的身材。他們說:你看,演員健身有好處吧。
上觀新聞:安大人其實是一個突破性的角色。
王學圻:對,那是我第一次演反派,我喜歡挑戰新的角色。我演反派不想演那種生下來就壞、一壞到底、毫無原因的壞。我想演那種亦正亦邪的。安大人是個劫匪,卻把名譽看得比命重。他喜歡音樂,崇拜英雄,重感情。我覺得,這個人物很豐富,很有色彩,很吸引我。
我們這代人,把名譽看得比命還要重
上觀新聞:這兩年有沒有遇到自己覺得特別過癮的角色?
王學圻:前兩年演電視劇《大明風華》,我就感嘆:演了一輩子了,終於實現自己的夢想,演了一回皇帝。
我演的是明成祖朱棣,他是一個很複雜很矛盾的角色。作為帝王,他有他的鐵血和狡猾,不怒自威。但他也是一個凡人、一個父親,和睦的家庭、日常的溫情會讓他感到幸福。我記得有一次俞灝明的爸爸來探班,他帶著他爸到我跟前說:“爸爸,這是我爹。爹,這是我爸。”
上觀新聞:有沒有什麼角色您覺得原來演不了,但現在能演的?
王學圻:其實演員也是一份需要積澱的職業。《金色池塘》你知道嗎?亨利·方達和凱瑟琳·赫本演的老電影,講一對老夫妻的故事,對年老的種種危機有所觀照,對人性的刻畫充滿深度,這是需要功夫的。
老年人處於一個總結人生的階段,總結一輩子的感悟。看完之後,你會覺得,哦,人生是這樣。這是需要有閱歷的人才能演好的。
所以《爸爸的床》讓我很激動。本子確實好,看著簡單,但又讓你回味無窮,充滿遺憾和無奈。演員本身也很有激情,和我演對手戲的周鳴晗,每場排練都掉淚,很投入。我特別希望我們這一版《爸爸的床》能給更多觀眾帶去思考。
上觀新聞:平常您生活裡都喜歡做什麼?
王學圻:我一個人喜歡打掃打掃房間、洗洗衣服、刷刷碗,把家裡收拾得乾乾淨淨,心裡也亮亮堂堂。
因為從小當兵,天天早上一起來就要搞衛生,被子疊得一模一樣,毛巾搭得整整齊齊,牙刷都衝一個方向,養成習慣了。現在也還是,休息的時候一定先把衛生打掃了,不打掃就幹不了別的事。非得都弄乾淨了,都弄整齊了,就像有強迫症一樣。
上觀新聞:演戲也有強迫症嗎?
王學圻:演戲也有。我的道具別人都不能動,這一動我就覺得哪不對了。比如腰帶這沒弄好,上臺就老惦記著,詞兒就忘了。
我14歲當兵,對我的一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們這代人,把名譽看得比命還要重,無論從藝或做人,都講究“得體”,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當下。
少誘惑就少苦惱。一輩子像我這麼過,也挺好。
(實習生郭晟對本文亦有貢獻)
題圖:王學圻在上海排練椎劇場話劇《爸爸的床》
圖片來源:董天曄 椎·劇場 王學圻
來源: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