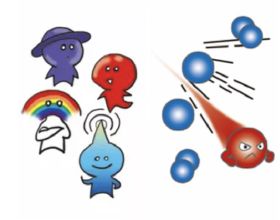老屋村的人喜歡扳手腕,也善於扳手腕,這是遠近聞名的。全村80多戶人家,近三百口子,不論男女老少都能來幾下。他們還經常在村口那棵古老的大樟樹下進行板手腕公開賽。方法很簡便:擺上桌子板凳,比賽雙方相對坐定,伸出右手左手,像小學生回答問那樣,將手舉起,以胳肘為支點立在桌面上,然後雙方兩手相提,同時使動,以將對方的手壓倒在桌面上為勝。勝者可繼續比賽,敗者當即淘法。這樣反覆較量,最後決出冠軍。
村裡有個年輕入,名叫伍松,隊伍的伍,松樹的松他人高馬大,手也好。經過一次次的比賽,坐上了手的第一把交椅,一坐兩年出頭,就沒人能拉他下來。
有一天,村裡來了師徒兩個鐵匠,在大樟樹下安營紮寨,擺開場子,製作農具。中午,師傅招攬生意去了,村裡一小夥子見小鐵匠閒來無事,就纏著要和他扳手腕比手勁。小鐵匠開頭不幹,後來一想,覺得這不過鬧著玩的,勝敗都無關緊要,而且還可以試試自已的手勁如何,於是就然同意了行,小夥子們很高興,急忙搬來了桌子板凳,擺開了戰場。
誰又想到,這些小夥子們都不是小鐵匠的對手,一連上了10來個,一個個都敗下陣來,正在他們抓耳撓腮無計可施的時候,早已有人,把事情告訴了伍松。伍松一聽來了火,手裡的活兒一丟,三步並作兩步來到了大樟樹下。
這時候,大樟樹下已經圍了不少人,一個個關注著這場比賽的最後結果。人們見伍松昂首挺胸地來到現場,立即讓開一條通道。伍松到小鐵匠面前,笑說:“小師傅,讓我也領教領教你的手勁,小鐵匠見伍松腰圓膀粗,知道來者不善,連忙說:“大哥,算了吧,我剛才不過是玩玩,山頭上動士啊”!一聽這活,伍松來了氣心想好大的口氣不過是玩玩就把我們一幫小夥子玩下去了,我非殺殺你的成風不可。他想到這,又說:“既然玩開了,那就再玩一次吧,要是我輸了,就盡義務為你三天大錘,“如果我輸了呢?“那就對不起,請你買一條煙,全村分一分。”“不比不行嗎?“也可以,不過你們得馬上捲鋪蓋離開老屋村。”
小鐵匠也是個血氣方剛的小夥子,經伍松這一,也上了火,牙一咬說:“好,比就比,我大不了拿出一條煙。”這可是一場旗鼓相當的比賽,兩隻大手抓在一起,動不動地足足堅持了5分鐘雙方的臉漲得血紅,手上的青筋暴得老高,圍觀的人們拚命叫喊加油,就是分不出勝負。突然,小鐵匠一用勁猛地一壓,將伍松的手按倒在桌面上,他勝了這是人們萬萬想不到也是不願看到的場面,幾乎所有的人都傻了眼。伍松不用說,更是滿臉通紅,難堪極了他覺得下不了這個臺,他決心出這口氣,不為自己也為老屋村挽回名譽。他猛然想到了一個人,於是擠出人群,往村裡跑去。
不一會兒,伍松回來了,他同來的還有個度老頭,伍松說:“小師傅,對你的手勁,我佩服,但是……”他指指身邊的瘦老頭“我們這位老同志不服氣。他王阿大,今年57歲。因為他兩隻都曾經受過傷,可不他想用耳朵你比手勁。就是說,你用手捏住他的耳朵,10秒鐘之內(不讓他的耳朵脫,你就勝了,不敢比一下?你要是輸了,拿出20元請客,如果你贏,我請你。”他說出了兩張“工農兵”。
這種比法實在新別致,小鐵匠很想一試。但仔細一想,又覺得不,暗想:你別誆我,我也是庭湖的麻雀一一見過風浪的。憑我的手勁,鐵打的耳朵也能抓住,可王阿大的耳朵畢寬是肉長的呀,捏輕了我要輸,捏重了會把耳朵址斷,那時人證物證俱在,我賠得起嗎?不,我絕不做傻瓜他想到這裡,連抱拳施禮說:“大哥,這個小弟不敢打,請多多包涵。”
恰在這時,鐵匠老師回來了。他問清了情由,當即掏出兩張“大團結”桌上一扔說:“徒兒,跟他賭,一切後果我承擔。”有師何這麼句話,小鐵匠還怕啥。他手一揮說“好,比就比,但我有言在先,扯斷耳朵不管。”王大笑笑說;“那自然,那自然。”
比賽開始了,小鐵匠運足了氣,伸手提住了王阿大的左耳朵。他那兩個指頭就像一把鐵似的得緊緊的,期說是耳朵,哪怕是根繡花也休想溜。伍松在一旁晉手錶,嘴裡在:“一,二,三…”他“四”字沒出口,只見王阿大的腦袋向右一偏,他那左耳朵意從小鐵匠手裡滑了出去,安然無恙。
這下眾人都樂了,有笑的,有叫的,有的,有跳的。老師驚得杲了好一陣才上前握住王阿大的手說:“了不起,真了不起哇,老哥,你這一手功夫是怎麼成的呀?”王阿大聽他這一問,尷尬地一笑,說道:“不瞞你說,這是“火紅'的年代裡在君爐裡煉出來的。那時我和你們一樣走村串戶副業掙了點錢被作為資本主義而被批鬥。因為我沒有頭髮,他們就抓我耳朵,一次又一次地使我練出了這手“耳朵功,你看怎麼樣?”
老師傅聽罷,拉起王阿大和伍松的手說:“走,咱們喝酒去!”
據說,他們那一頓花去了整整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