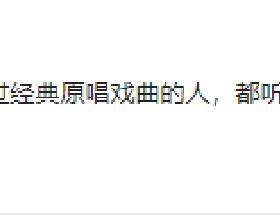在醫院的後院裡有一座不大的偏屋,四周長著密密麻麻的牛蒡、蕁麻和野生的大麻。這房子的鐵皮屋頂已經生鏽,煙囪塌了半截,門前的臺階早已腐朽,長出草來,牆上的灰漿只留下斑駁的殘跡。偏屋的正面對著醫院,後面朝向田野;一道帶釘子的灰色圍牆把偏屋和田野隔開。這些尖端朝上的釘子、圍牆和偏屋本身,無不顯得陰森可怕,只有我們的醫院和監獄才會有這種特殊的外觀。
如果您不怕被蕁麻螫痛,那您就沿著一條通向偏屋的羊腸小道走去,讓我們看一看裡面的情景。開啟第一道門,我們來到了外室。這裡的牆下和爐子旁邊扔著一堆堆醫院裡的破爛。床墊啦,破舊的病人服啦,長褲啦,藍白條紋的襯衫啦,毫無用處的破鞋啦--所有這些皺皺巴巴的破爛混雜在一起,胡亂堆放著,正在黴爛,發出一股令人窒息的臭味。
看守人尼基塔,嘴裡咬著菸斗,老是躺在這堆汙七八糟的廢物上。他是個退伍的老兵,那身舊軍服上的紅領章早已褪成棕黃色。他的臉嚴厲、憔悴,兩道下垂的眉毛給他的臉增添一副草原牧羊犬的神氣,鼻子通紅。他身材不高,看上去瘦骨伶仃,青筋暴突,可是神態威嚴,拳頭粗大。他屬於那種頭腦簡單、唯命是從、忠於職守、愚鈍固執的人,這種人最喜歡秩序,把它看得高於一切,因而深信:他們就得捱打。他打他們的臉、胸、背,打到哪兒算哪兒,相信不這樣就不能維持這裡的秩序。
再往裡走,您便進入一間寬敞的大房間,如果不算外室,整座房子就由它佔去了。這裡的牆壁塗成暗藍色,天花板燻黑了,跟沒有煙囪的農舍一樣--顯然,到了冬天,這裡的爐子日夜冒煙,煤氣很重。窗子的裡邊裝著鐵柵欄,樣子難看。地板灰暗,粗劣。滿屋子的酸白菜味,燈芯的焦糊味,臭蟲味和氨水味,這股渾濁的氣味讓您產生的最初的印象是,彷彿您進入了一個圈養動物的畜欄。
房間裡擺著幾張床,床腳釘死在地板上。在床上坐著、躺著的人都穿著藍色病人服,戴著舊式尖頂帽。這些人是瘋子。
這裡一共五個人。只有一人貴族出身,其餘的全是小市民。靠近房門睡的是個又高又瘦的小市民,褐色的小鬍子亮閃閃的,淚眼模糊,託著頭坐在床上,定定地望著一處地方發呆。他日日夜夜發愁,搖頭,嘆氣,苦笑。他很少參與別人的談話,即使問他什麼,他也照例不答。給他端來食物,他就機械地吃下去,喝下去。從他那劇烈而痛苦的咳嗽,骨瘦如柴的模樣和臉頰上的潮紅可以推斷,他正害著痔病。
在他之後是個矮小、活潑、十分好動的老頭子,留一把尖尖的小鬍子,一頭烏黑的鬈髮,像黑人似的。白天他在病室的兩扇窗子間不停地踱來踱去,或者像土耳其人那樣盤腿坐在自己床上,同時無休止地吹著口哨,學灰雀啼叫,還小聲唱歌,嘿嘿竊笑。他的這種孩子氣的樂趣和活潑的性格,即使在夜裡也有所表現:他常常爬起來向上帝禱告,也就是用雙拳捶胸,用手指頭摳摳門縫。他就是猶太人莫謝伊卡,大約二十年前他因為帽子作坊起火燒燬而神經錯亂,成了瘋子。
第六病室的全體病人中,只有莫謝伊卡一人被允許外出,甚至可以離開醫院上街去。他很久以來就享受著這一特權,大概因為他是醫院的老住戶,又是個不傷人的文瘋子,再者他成了城裡供人逗樂的丑角。只要他一出現,立即被一群孩子和狗圍住,對此人們也早已看慣了。他穿著難看的病人服,戴著滑稽的尖頂帽,穿著拖鞋,有時光著腳,甚至不穿長褲,在街上走來走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門口站住,討個小錢。有的給他克瓦斯,有的給點麵包,還有人給個小錢,所以他回來時通常已吃飽喝足,還發了點小財。他帶回來的東西統統讓尼基塔沒收了去歸自己享用。這個老兵做這種事很不客氣,他粗魯地、氣急敗壞地把他的每一個口袋都翻過來,還呼喚上帝來作證,說他今後絕不再放猶太人上街,說他在這個世界上最恨的是不守秩序。
莫謝伊卡喜歡幫助人。他給同伴端水,在他們睡著的時候給他們蓋好被子,答應下次從街上回來送每人一個小錢,並且給每人縫一頂新帽子。他還給左邊的鄰居,一個癱瘓病人,用勺子餵飯吃。他這樣做既不是出於憐憫,也不是出於什麼人道方面的考慮,他只是無形中受了右邊的鄰居格羅莫夫的影響,模仿他這麼幹的。
伊凡·德米特里·格羅莫夫是個三十三歲的男子,貴族出身,擔任過法院民事執行員,屬十二品文官,患有被害妄想症①。他要麼縮成一團躺在床上,要麼在室內不停地走來走去,像在活動筋骨,很少有坐著的時候。一種令人驚慌不安的、說不清道不明的等待,弄得他總是十分興奮、急躁、緊張。外屋裡只要有一絲動靜,或者院子裡有人叫一聲,他便立即抬起頭,側耳細聽:莫非是有人來找他?要把他抓走,這時他的臉上就露出極其驚慌和厭惡的神色。
我喜歡他那張顴骨突出的方臉盤,它總是蒼白,悲傷,像一面鏡子反映出他那顆飽受驚嚇又苦苦掙扎的心靈。他的臉相是奇特的,病態的,然而那清秀的面容雖則刻下深沉而真誠的痛苦,卻顯出理智和知識分子所侍有的文化素養,他的眼睛閃出溫暖的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歡他本人,彬彬有禮,樂於助人,對所有的人都異常客氣,除了尼基塔。誰要是掉了釦子或者茶匙,他總是趕緊從床上跳下來,拾起那件東西。每天早晨他都要跟同伴們道早安,躺下睡覺時祝他們晚安。
除了一貫緊張的心情和病態的臉相外,他的瘋病還有如下表現:有時在傍晚,他裹緊那件破舊的病人服,渾身發抖,牙齒打顫,開始在牆角之間、病床之間急速地走來走去。好像是,他正害著厲害的寒熱病。有時他突然站住,看看他的同伴們,想必他有十分重要的話要說,可是他又顯然考慮到他們不會聽他講話,或者即使聽也聽不懂,於是他便不耐煩地搖著頭,繼續走來走去。可是不久想說話的慾望壓倒一切顧慮,佔了上風,他就放任自己,熱烈地、激昂他講起來。他的話沒有條理,時快時慢,像是夢吃,有時急促得讓人聽不明白,然而在他的言談中,在他的聲調中,有一種異常美好的東西。聽他說話,您會覺得他既是瘋子又是正常人。他的瘋話是難以寫到紙上的。他談到人的卑鄙,談到踐踏真理的暴力,談到人間未來的美好生活,談到這些鐵窗總是使他想到強權者的愚蠢和殘酷。結果他的話就成了一支雜亂無章的整合曲,儘管是老調重彈,然而卻遠沒有唱完。
大約十二年或十五年前,文官格羅莫夫住在城裡一條最主要的大街上。他擁有私宅,頗有名望,家道殷實。他有兩個兒子:謝爾蓋和伊凡。謝爾蓋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得了急性肺結核,死了。他的死像是開了個頭,此後一連串的不幸突然落到這家人頭上。剛埋葬了謝爾蓋,一週後,年老的父親因為偽造單據盜用公款受到起訴,不久因傷寒病死在監獄的醫院裡。房子和全部動產均被拍賣,弄得伊凡·德米特里和他的母親一貧如洗無以為生了。
從前,在父親活著的時候,伊凡·德米特里住在莫斯科,在那裡上大學,每月收到六七十個盧布,不知道什麼叫窮,後來他不得不急劇地改變自己的生活。他只好從早到晚去教報酬很低的家館,做抄寫工作,卻仍舊捱餓,因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給母親維持生計了。伊凡·德米特里忍受不了這種生活。他垂頭喪氣,變得虛弱不堪,不久就放棄學業,回到家鄉。在這裡,在這座小城裡,他多方託人,謀到了縣立學校的一份教職。但他跟同事相處不好,學生也不喜歡他,不久他就辭職不幹了。母親又去世了。他有半年之久失業在家,只靠麵包和水生活,後來就當上了法院的民事執行員。他一直擔任這個職務,直到因病被解職為止。
他向來沒有給人留下健康的印象,即使在青春年少的大學期間也是這樣。他總是臉色蒼白,身體消瘦,經常感冒,吃得少,睡不好。只要一杯紅葡萄酒就能弄得他頭昏腦漲,歇斯底里發作。他總想跟人們交往,但由於他生性急躁、多疑,他沒有朋友,沒有一個至交。他對城裡人的評論向來帶著輕蔑,老說,他們的粗魯無知和渾渾噩噩的禽獸般的生活是他深惡痛絕的。他用男高音說話,響亮而熱烈。說話時要麼怒氣衝衝、憤憤不平,要麼興高采烈,露出驚奇的神色,不過任何時候他的表情都是真誠的。不論跟他談什麼,他總是歸結到一點:這個城市的生活沉悶、無聊,這個社會沒有高尚的需求,過著毫無生氣、毫無意義的生活,充斥著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偽善。卑鄙的人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飢挨餓;社會需要學校,主持正義的報紙,劇院,大眾讀物,知識界的團結;必須讓這個社會認清自己的面目,感到震驚才好。他對人的議論總加上濃重的色調,而且只有黑白二色,不承認有其他的色彩。他把人類分成卑鄙小人和正直人兩種,中間的人是沒有的。關於女人和愛情他總是津津樂道,充滿熱情,但他一次也沒有戀愛過。
儘管他言論尖刻、神經過敏,城裡人卻喜歡他,背地裡都親切地叫他萬尼亞①。他那種待人和藹、樂於助人的天性,為人的正派,道德的純潔,就連他那件破舊的常禮服,病態的外貌,家庭的不幸,總能喚起他們心中美好的、溫暖的、憂傷的感情。此外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博覽群書,用城裡人的話說,他無所不知,在這個城市裡是個類似活字典的人物。
他讀過很多書。他常常坐在俱樂部裡,神經質地捻著小鬍子,翻閱雜誌和書籍。看他的臉色可以知道,他不是在閱讀,而是在吞嚥,根本來不及咀嚼。應當認為,閱讀是他的一種病態的習慣,因為不管他抓到什麼,哪怕是去年的報紙和日曆,他都急不可耐地讀下去。他在家裡總是躺著看書
一個秋天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翻起大衣領子,在泥濘中啪嗒啪嗒地走著,穿過小巷和一些偏僻的地方,費力地去找一個小市民的家,憑執行票向他收款。他心情憂鬱,每到早晨他總是這樣的。在一條巷子裡他遇到囚個荷槍實彈計程車兵押送著兩名戴著手銬的犯人。以前伊凡·德米特里經常遇見犯人,每一次他們都引起他憐憫和不安的感覺,可是這一次相遇卻給他留下一個異樣的、奇怪的印象。不知為什麼他突然覺得,他也可能戴上手銬,就這樣由人押著,走在泥地裡,送進監獄去。他在小市民家待了一會兒,然後回家。在郵局附近他遇見一個認識的警官,對方跟他打了招呼,還和他一道走了幾步,不知為什麼他又覺得這很可疑。回到家裡,他一整天都想著兩個犯人和荷槍的兵,一種莫名其妙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妨礙他閱讀和集中精力思索什麼事。晚上他在屋裡沒有點燈,夜裡也不睡覺,老想著他可能被捕,戴上手銬,關進監獄。他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過失,而且可以擔保他今後也絕不會去殺人、放火、偷盜。可是,無意中偶然犯下罪行難道不容易嗎?難道不會有人誣陷嗎?最後,難道法院不可能出錯嗎?難怪千百年來人民的經驗告誡我們:誰也不能發誓不討飯,不坐牢。①而在現行的訴訟程式下,法院的錯判是完全可能的,不足為怪的。那些對別人的痛苦有著職務或事務關係的人,如法官、警察和醫生,久而久之,出於習慣勢力,會變得麻木不仁,以致對他們的當事人即使不願意也不能不採取敷衍了事的態度。從這方面講,他們同在後院裡殺羊宰牛而看不見血的農民沒有絲毫區別。在對人採取這種敷衍塞責、冷酷無情的態度的情況下,為了剝奪一個無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權利並判他服苦役,法官只需一件東西:時間。只要有時間去完成某些法定程式,然後就萬事大吉--法官就是憑這個領取薪水的,事後你在這個離鐵道二百俄裡的骯髒的小城去尋找公正和保護吧!再說,既然社會把任何暴力視作明智、合理之必需,而一切仁慈的舉動,如宣告無罪的判決,卻引起不滿和報復情緒的大爆炸,在這種情況下,侈談公正,豈不可笑嗎?
早晨,伊凡·德米特里起床後心存恐懼,額頭上冒出冷汗,已經完全相信,他每時每刻都可能被捕。“既然昨天那些沉重的思想久久地沒有離開我,”他想道,“可見這些想法不無道理。這些想法的確不可能無緣無故地鑽進腦子裡的。”
有個警察不慌不忙地從窗下經過:這是不無用意的。瞧,有兩個人站在房子附近,也不說話。為什麼他們不說話呢?
從此,伊凡·德米特里日日夜夜受盡折磨。所有路過窗下的人和走進院子的人都像是奸細和暗探。中午,縣警察局長通常坐著雙套馬車從街上經過,他這是從城郊的莊園去警察局上班。可是伊凡·德米特里每一次都覺得:馬車跑得大快,他的神色異樣,顯然他急著跑去報告:城裡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犯人。每逢有人拉鈴或者敲門,伊凡·德米特里就渾身打顫,如果在女房東家裡遇到生人,他就惶惶不安。可是遇見警察和憲兵時他卻露出笑臉,還吹著口哨,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他一連幾夜睡不著覺,等著被捕,可是又故意大聲打鼾,像睡著的人那樣連連吁氣,好讓女房東覺得他睡著了。要知道如果夜裡他睡不著覺,那就意味著他受到良心的譴責,痛苦不堪--這可是一大罪證!事實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這些恐懼都荒誕不經,無非是變態心理,另外,如果把事情看得開一些,即使被捕坐牢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只要問心無愧就行了。但他的思考越是理智,越是合乎常理,他內心的惶恐不安卻越是強烈,越是折磨人。這就像一個隱士本想在處女林裡開出一小塊安生之地,他用斧子砍得越是起勁,林子卻長得越來越茂盛一樣。伊凡·德米特里最後意識到,這也無濟幹事,於是索性不再思考,完全沉溺於絕望與恐懼之中。
他開始離群索居,避開人們。他原先就討厭自己的職務,現在更是忍受不了這種工作。他生怕有人使壞整他,偷偷往他的口袋裡塞進賄賂,然後去告發他。或者他自己無意中在公文上出錯--這無異於偽造文書,或者他丟失了別人的錢。奇怪的是他以前的思想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活躍機敏,現在他每天都能想出成千上萬條各種各樣的理由,說明應當認真為自己的自由和名譽擔憂。正因為如此,他對外界,特別是對書籍的興趣便明顯地減弱,他的記憶力也大為衰退了。
到了春天,雪化了,在公墓附近的一條沖溝裡發現兩具部分腐爛的屍體。這是一個老婦人和小男孩,帶有強暴致死的跡象。於是城裡人議論紛紛,只談這兩具屍體和尚未查明的兇手。伊凡·德米特里害怕別人以為這是他殺死的,便在大街小巷走來走去,還面帶微笑。可是遇見熟人時,他的臉色紅一陣,白一陣,一再宣告,沒有比殺害弱小的、無力自衛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這種作假很快就使他厭倦,他略加思索後認定,處在他的地位,最好的辦法就是躲進女房東的地窖裡去。他在地窖裡坐了一整天,之後又坐了一夜一天。他凍得厲害,等到天黑,便偷偷地像賊一樣溜進自己的房間裡。天亮之前,他一直站在房間中央,身子一動不動,留心聽著外面的動靜。清晨,太陽還沒有升起,就有幾個修爐匠來找女房東。伊凡·德米特里清楚地知道,他們是來翻修廚房裡的爐灶的,然而恐懼偷偷地告訴他,這些人是打扮成修爐匠的警察。於是他悄悄地溜出住宅,沒戴帽子,沒穿上衣,驚駭萬分地順著大街跑去。幾條狗汪汪叫著追他,有個男人在後面不住地喊叫,風在他耳邊呼嘯,伊凡·德米特里便覺得全世界的暴力都聚集在他的背後,現在要來抓住他。
有人把他攔住,送回住處,打發女房東去請醫生。醫生安德烈·葉菲梅奇(這人以後還要提起)開了在頭上冷敷的藥液和桂櫻葉滴劑①的藥方,愁眉苦臉地直搖頭。臨走前他對女房東說,以後他不會再來了,因為他不該妨礙人們發瘋。由於伊凡·德米特里在家裡無法生活和治療,只好把他送進醫院,被安置在性病病室裡。他每天夜裡不睡覺,發脾氣,攪得病人不得安寧,不久安德烈·葉菲梅奇便下令把他轉到第六病室。
一年後,城裡人已經完全忘了伊凡·德米特里,他的書讓女房東胡亂堆在屋簷下的雪橇裡,被頑皮的孩子們一本本拿光了。
伊凡·德米特里左邊的鄰居,我已經說過,是猶太人莫謝伊卡,右邊的鄰居是個一身肥肉、長得滾圓的農民,一張痴呆呆的臉上毫無表情。這是一個不愛動的、貪吃的、不乾不淨的畜生,早已喪失了思想和感覺的能力。從他身上不斷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惡臭。
尼基塔給他收拾床鋪的時候,總是狠狠打他,使勁掄起胳膊,一點也不顧惜拳頭。這時候,可怕的不是他捱了打--這種事是可以習慣的--可怕的是這個遲鈍的畜生捱了打卻毫無反應:不出聲音,沒有動作,連眼睛都毫無表情,只是身子稍稍晃一晃,像個沉重的大木桶。
第六病室的第五個,也就是最後一個病人是個小市民,原先是郵局的揀信員。他是個瘦小的金髮男子,一張和善的面孔上帶點狡猾的神色。看他那雙聰明、安詳的眼睛以及明亮而快活的目光可以推斷,他城府根深,心裡藏著極重要、極愉快的秘密。他在枕頭底下,床墊底下藏著什麼東西,總不肯拿出來給別人看,倒不是怕人搶了去,偷了去,而是有點不好意思。有時他走到窗前,背對著病友,在胸前佩戴什麼東西,還低下頭看了又看。如果這時有人走到他跟前,他就滿臉窘色,立即把胸前的東西扯下來。不過他那點秘密是不難猜出的。
“您得向我祝賀,”他常常對伊凡·德米特里說,“上司為我呈請授予二級斯丹尼斯拉夫星章。二級星章向來只頒發給外國人,可是不知什麼緣故他們願意為我破例哩,”他笑嘻嘻地說,還大惑不解地聳聳肩膀,“嘿,老實說,簡直沒有料到。”
“你這話我一點也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陰沉地宣告。
“不過您可知道我遲早會弄到什麼嗎?”以前的郵局分揀員狡黠地眯細眼睛接著說,“我一定能得到一枚瑞典的‘北極星’。這種勳章是值得費心張羅的。白十字架和黑帶子。漂亮極了。”
大概任何別的地方的生活都不會像這座偏屋裡那樣單調。每天早晨,除了癱瘓病人和胖農民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外室裡的一隻雙耳木桶裡洗臉,用病人服的下襬擦乾。這之後他們用錫杯子喝茶,茶是由尼基塔從主樓裡取來的。每人只能喝一杯。中午他們喝酸白菜湯和粥,晚上吃中午剩下的粥。三餐之間,他們躺下,睡覺,望著窗子,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天天如此。連以前的郵局揀信員說的也還是那幾種勳章。
第六病室很少見到新人。醫生早就不接收新的瘋癲病人,而想訪問瘋人院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是不多的。理髮師謝苗·拉扎裡奇隔兩個月來這裡一次。他怎麼給瘋子們理髮,尼基塔怎麼幫他的忙,每當這個醉醺醺、笑呵呵的理髮師出現時,病人們怎樣亂作一團--這些我們就不談了。
除了理髮師,誰也不到這裡來看一看。病人們註定一天到晚只能見到尼基塔一個人。
可是不久前在醫院的主樓裡流傳著一個相當奇怪的訊息。
傳說好像醫生經常去第六病室了。
奇怪的流言!
醫生安德烈·葉菲梅奇·拉金,從某一點上說是個與眾不同的人。據說他年輕時篤信上帝,準備日後擔任神職。一八六三年他中學畢業,本想進神學院學習,可是他的父親,一名醫學博士和外科醫師,刻薄地挖苦了他一頓,斷然宣佈,如果他真去當神父,他就不認他這個兒子。這話可信到什麼程度,我不知道,不過安德烈·葉菲梅奇本人不止一次地承認,他對醫學以及一般的專門學科向來是不感興趣的。
不管怎麼樣,他讀完了醫學系的課程,並沒有去當教士。看不出他如何篤信上帝,開始從醫時跟現在一樣,他都不像是虔誠信教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像個莊稼漢。他的臉,鬍子,平順的頭髮和結實笨拙的體態,使人想起大道旁小飯鋪裡那種酒足飯飽、隨隨便便、態度粗魯的店老闆。他的臉粗糙,佈滿細小的青筋,眼睛小,鼻子發紅。由於身材高,肩膀寬,所以手腳很大,似乎一拳打出去,就能叫人斷了氣。不過他的步態徐緩,走起路來小心翼翼,躡手躡腳。在狹窄的過道里遇見人時,他總是先停下來讓路,說一聲:“對不起!”--他的聲音完全不是預料中的男低音,而是嗓子尖細、音色柔和的男中音。他的脖子上有個不大的瘤子,妨礙他穿漿過的硬領衣服,所以他總是穿柔軟的亞麻布或棉布襯衫。一般說來,他的穿著不像一名醫生。一身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衣服他照例到猶太人的鋪子裡去買,那皺皺巴巴的新衣穿在他身上跟舊衣服一樣。同一件常禮服,他看病時穿它,吃飯時穿它,出門做客也穿它。不過他這樣做不是出於吝嗇,而是他完全不修邊幅。
當安德烈·葉菲梅奇來到這個城市就職的時候,這個“慈善機關”的情況簡直糟透了,病室裡,過道里,醫院的院子裡,到處臭哄哄的,叫人透不過氣來。醫院的勤雜工、助理護士和他們的孩子們都跟病人一起住在病室裡。人們抱怨,蟑螂、臭蟲和老鼠攪得大家不得安生。在外科,丹毒從來沒有絕跡過,整個醫院只有兩把手術刀,體溫計一個也沒有,浴室裡存放著土豆,總務長,女管理員和醫士勒索病人錢財。據說安德烈·葉菲梅奇的前任老醫生把醫院裡的酒精偷偷拿出去賣,他還網羅護士和女病人組成他的後宮。所有這些汙七八糟的事城裡人全都清楚,甚至誇大其詞,然而對此卻漠不關心。有些人強詞奪理,說什麼住醫院的都是小市民和農民,這種人不可能不滿意,因為他們家裡的生活比醫院裡還要糟得多,總不能供他們吃松雞吧!另一些人則辯解說,沒有地方自治局的幫助,光靠本城的財力是辦不成一所像樣的醫院的;謝天謝地,醫院雖糟,總算有一個。而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不論在城裡還是城郊都不開設診療所,藉口是城裡已經有醫院了。
到醫院裡視察一番,安德烈·葉菲梅奇得出結論,這個機構不成體統,對病人的健康極為有害。照他看來,最明智的可行辦法就是把所有的病人放回家,關閉這所醫院。但他考慮到,光憑他個人的許可權很難做到這一點,況且這也無濟於事。如果把肉體上的和精神上的汙穢從一個地方趕出去,那它就會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應當等待它自行消失。再說,人們既然開辦醫院,而且容忍它的存在,可見它是人們需要的。種種偏見和所有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卑鄙齷齪的醜事也是需要的,因為久而久之它們會轉化為有用之物,正如畜糞變成黑上一樣。這個世界上沒有一種好東西在它開始的時候不帶有醜惡的成分。
上任之後,安德烈·葉菲梅奇對待醫院裡的混亂看來是相當冷漠的。他只要求醫院的勤雜工和護士不再在病室裡過夜,添置了兩櫃子的醫療器械,至於總務長,女管理員,醫士和外科的丹毒,一切都維持原狀。
安德烈·葉菲梅奇極其喜愛智慧和正直,然而要在自己身邊建立明智和正直的生活對他來說卻缺乏堅強的性格,缺乏這方面的信心。下命令,禁止,堅持己見,這些他是完全做不到的。看來他似乎發過誓,永遠不提高嗓門,永遠不用命令式。“給我這個”或者“把那東西拿來”這樣一些話他很難說出口。每當他餓了,他總是猶豫不決地咳幾聲,對廚娘說:“最好給我一杯茶”或者“最好給我弄點吃的”。至於對總務長說不準他偷盜,或者把他趕走,或者乾脆廢除這個多餘的寄生職位--這些他完全是無能為力的。每當有人欺騙安德烈·葉菲梅奇,或者奉迎他,或者拿來一份明明是造假的帳單要他簽字,他總是窘得滿臉通紅,儘管他感到心中有愧,但還是在帳單上籤了字。遇到病人向他訴苦說吃不飽,或者抱怨護士態度粗暴,他就發窘,抱歉地嘟噥說:
“好,好,我以後調查一下……多半這是誤會……”
起先安德烈·葉菲梅奇十分勤奮。每天從早晨起他就給病人看病,做手術,有時甚至接生,一直幹到吃午飯。女病人都說他細心,診斷準確,特別是兒科疾病和婦女病。可是時間一長,他因為工作的單調、徒勞無益,顯然感到厭煩了。今天接診三十個病人,到明天一看,加到三十五人,後天就是四十,就這樣天天看病,年年看病,可是城市的死亡率並沒有因此下降,病人照樣不斷地來。一個上午,要對四十名就診病人真正有所幫助,這在體力上是辦不到的,所以儘管不願意,結果只能是騙局。一個會計年度接診一萬兩千名病人,不客氣地說,那就是欺騙了一萬兩千名病人。至於讓重病人住進病房,按科學的規章給以治療,這同樣做不到,因為規章是有的,科學卻沒有。如果拋開空洞的議論,像別的醫生一樣死板地照章辦事,那麼為此首先需要潔淨和通風,而不是垃圾和汙濁的空氣;需要有益健康的食品,而不是酸臭的白菜湯;需要助手,而不是竊賊。
再說,既然死亡是每個人正常合理的結局,那又何必阻止人們去死呢?如果某個商人或文官多活了五年十年,那又怎麼樣呢?如果認為醫學的任務在於用藥物減輕痛苦,那麼這裡不能不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減輕痛苦呢?據說,首先,痛苦使人完美;其次,如果人類當真學會了用藥丸和藥水減輕自己的痛苦,那麼人類就會完全拋棄宗教和哲學,可是到目前為止人類在宗教和哲學中不僅找到了避免一切不幸的護符,而且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臨死前經受了可怕的折磨,可憐的海涅因癱瘓而臥床好幾年。那麼為什麼某個安德烈·葉菲梅奇或者瑪特廖娜就不該生病呢?要知道這些人的生活毫無內容,如果沒有痛苦,那他們的生活就完全空虛,變得跟變形蟲的生活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