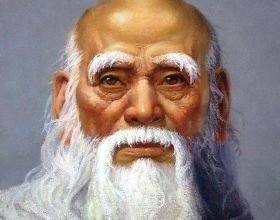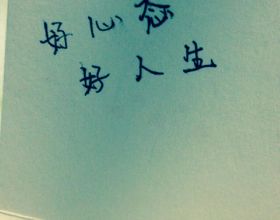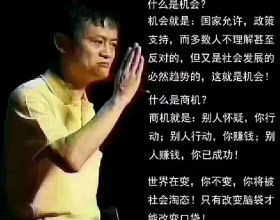夜裡兩點,牛二被胯下的傷口癢醒了,新生的肉芽正如波浪從傷口兩岸往中間洶湧,直至將那道鮮紅的溝壑填平。牛二試著用手輕撓了一把:“哦~爽!”
三週前牛二胯下捱了一刀,從陰囊往下一路劃開,肛門也被切了個口子,瘻管被拔出,留下的創口有小孩嘴巴那麼大;眼下創口新愈,肉質太嫩,稍一觸碰,或者摩擦就有血珠滲出,醫生要求臥床,再過半個月當能行動自如。
牛二輕輕搔著癢,暗忖:“那條瘻管真該給醫生要回來,串上竹籤,撒上孜然,文火一烤,就瓶啤酒擼了它,就像擼鴨腸——折磨老子兩年多,不吃了它難消心頭恨!”
牛二咽口唾沫、吧嗒下嘴,忽聞屋外老爹低吼了一聲:“日他娘,羊被偷了!”
老爹七十七了,長一副羊臉,下巴頦上留著白鬚一小把。牛二長得像爹,只少了那把鬍鬚。老爹這隻領頭羊已經老了,牛二這頭接班羊恰逢壯年——壯年的牛二小心翼翼坐起身,開燈,披上一件外套,這個時令夜裡還有點涼,他身體又虛,穿衣脫衣仍不敢大意;趿拉著鞋出了屋門,老爹陪他一起檢視,羊圈的門緊閉,鎖也完好,後山牆卻被掏了個洞,山牆又是院牆,羊便從那個洞裡叫人牽走了。羊是頭母羊,剛懷孕,老爹還巴望它生一窩羊崽子,羊崽子再生小羊羔,小羊羔再生羊崽子,羊崽子繼續生羊羔……羊子羊孫無窮匱,他也就發家致富奔小康了,兒子兒媳也不必進城務工了——那得低眉順眼瞧多少臉色呀。
羊丟了,老爹跺腳罵:“日他娘,老子再養一頭,拴床腿上,看哪個王八羔子敢來偷?”
牛二則問:“爹,我那支矛呢?”。
“在我床頭擱著呢,我拿它看家。”
老爹回屋取出長矛交到牛二手上。
矛生鏽了,那道攝人心魄的藍光也不見了,矛身由鐵鏽包裹,變成了棕紅色。牛二一手握矛柄一手撫矛頭,矛尖禿了,矛刃鈍了,木柄倒是更滑溜了。
牛二揪住衣領將披著的上衣摜在地上,人矛合一,斜著身子從那個斜長的盜洞鑽了出去,回頭又要了一支手電,說:“地上有羊屎蛋,我跟著追,不能便宜了狗日的賊!”
他爹猛一點頭,嗨了一聲:“算了,你還沒好利索呢。”
“不能算!”
他爹想了想,似有所悟,說:“這樣。你追。我報警。”
羊屎蛋猶如一串黑葡萄,走一段拉一溜兒,好像在故意給他指引;牛二踩著那些黑蛋蛋走,一會兒黑蛋蛋沒了,路上又現出羊蹄印來,他便踩著那些蹄甲印子追。兩種路標交替出現,從未間斷。牛二頭頂滿天星,走得很小心,生怕步子太大扯開胯下的刀口;行進中,他轉頭四顧,手電照不到的地方漆黑一片,上弦月早在上半夜即早早西沉;他傾耳細聽,四周蟲鳴起伏,和著他的腳步聲。
牛二倏然走了神,只一秒鐘便想完了三件事,他的大腦好似CPU,交替處理三個檔案,因用時極短,感覺三個故事同時湧入他的中央處理器,又同時處理完畢,分不出個先後——
(1)“躺上去,側身,雙腿併攏,把褲子脫到膝蓋,按你面前的圖示姿勢躺好。”
“你們有男醫生嗎?”牛二腆著臉問。
女醫生瞪了牛二一眼,沒答下語。
“怪難為情的,”牛二雙手握著腰帶的金屬扣,表情討好到無以復加。
女醫生瞥了他一眼,又哼了一聲,輕蔑地一笑,說:“不是打擊你啊,什麼樣式的男人我沒見過——比老二,我老公是你們這幫人的兩倍……怎麼樣,還難為情不?”
牛二羞紅了五十歲的老臉,乍暖的面色突然就還寒了;他往門診的小床上一倒,砸出咚的一聲響,兩手麻利地寬衣解帶,一把將褲子退到腳踝,心裡極不服氣:“還兩倍,除非你男人是嫪毐,或者乾脆就是頭驢!”
醫生戴上橡膠手套,食指從肛門探進去左摸右摸,一分鐘就定了症:“肛瘻。”
“打針還是吃藥?”一聽病名,牛二氣歪的嘴立馬扳正了。
“打針吃藥都沒用,手術。”
牛二沒敢打聽要多少錢,從醫院出來他就撥通老婆的手機,說了他的打算:“回老家治病,家裡有農合——城裡太雞巴貴了!”
隨後他又給老家的老爹去了個電話,說明天回家。
”當差不自由啊,”老爹納悶,“不逢年不過節的,咋說回來就回來?”
“治病。”
“啥病?”老爹有點緊張。
“小病,肛瘻。”
“缸漏?”
“回去再說,沒事。”
“沒事就好。”
(2)牛二邁著手術後不太靈便的步子在村子裡從東走到西,從南踱到北。村子是安寧的,也是安靜的,不見狗,不見貓,連一絲人氣都沒有;家家閉門鎖戶,堅壁清野,彷彿在防備鬼子進村。
“這才七點呀,正是《新聞聯播》的黃金時段,怎麼這般靜悄悄?”牛二趴大門上仔細瞧,有的門從外面上鎖,那是舉家進城了。有的門從裡面上鎖,表明家裡有人,他扒著門縫往裡瞅,從上往下一點一點找縫隙大的地方,活像當年一對新人入了港,他匆匆忙忙去聽房——某年某月的某一晚,入了洞房的胡二和老婆正行好事,突然嗷一聲叫喚,兩人各穿一身秋衣褲,共披一床被子從新房裡蹦了出來,嘴裡叫罵不止:“哪個王八犢子這麼損,在人家屋裡點硫磺!別叫我知道你是誰,抽不死你個癟犢子!”
外面的積雪足有一尺厚,月光之下,好一派朗朗乾坤。牛二趴在雪窩裡,就像此時趴在門縫上,欣賞一對新人剛拜完天地,這會兒又咒天罵地。牛二忍俊不禁,捂著嘴吃吃笑……十分鐘前,大傢伙聚在新人的臥室裡鬧洞房,逼著新婚小夫妻拉個手啦,抱一堆啦,親個嘴啦……淨是這類無聊的勾當。新人們不許急,這是習俗,你們成雙成對成了飽漢子,還不興一群單身的餓漢子鬧一鬧過過乾癮嗎?牛二就是趁這當口把硫磺點著的,擱在另一間房子的牆角里,與新房通連。淡藍色的火焰在淡黃色的硫磺上跳舞,活似鬼火,飄飄忽忽,辛辣刺鼻的氣味一圈一圈向外盪漾開來。牛二走回去充老好人,勸鬧洞房的人:“不早了,別耽誤人家的好事,走吧。”他這麼一說,誰也不好意思再待下去,大家笑鬧一場,分頭走人。新人們早就急不可耐,關門,熄燈,上床。他們哪裡曉得,作妖的人走了,作祟的煙霧已經在路上,眼瞅著就要飄過來。
——牛二嘴對著門縫喊:“胡二,胡二在家嗎?”
門縫裡飄出一個女聲:“沒在家,打工去了。”
“幾時回來?”
“不回來啦,死外面了啦!”
“這騷娘們,欠操!”
牛二霍然記起了那娘們的樣貌,當年鬧洞房對他刺激最深的是她那雙丹鳳眼,眼皮極薄,好像只有一層上皮細胞,眼球卻有些凸起,從側面看讓人非常擔心,一根很小的刺斜插過來就能將她的瞳孔刺穿。
牛二的審美有點怪,越是長相的特別之處越招他愛戀,胡二老婆的眼睛在他心裡滴溜溜轉了好幾年,這麼說吧,在渴望女人的年月裡,他曾多次意淫過她。
離開胡二家,牛二又去找劉二、彭二和楊二,沒一人在家,整個小二村幾乎是空的。牛二想了想,也對,要不是手術,他也不會在家的。
(3)牛二一回來就聽說了去年夏天村裡招賊的事。
王二的小麥脫了粒,晾在村口的大路上。大路平整,方便攤開。曬了一天,夜裡沒收,想著明天再見見太陽就乾透了。為防賊,王二搬了鋪蓋睡在旁邊守夜。凌晨兩點,月高風輕,王二睡得正香,兩隻手腕突然被什麼東西壓住了,他一驚,醒了,藉著月光瞧見兩條人影,一左一右,像哼哈二將,一人一隻腳將他的手腕踩得牢牢的。左邊那位手裡提著一支棒槌,壓低嗓門道:“別動,小心搗爛你的腦殼!”說著還揚了揚手裡的棒槌,做了一個砸將下來的姿勢。
王二嚇懵了,一動不敢動。一輛三輪開過來,車盤底下裝著一臺吸塵器,照直駛過去,地上的麥粒吸得乾乾淨淨。吸完一趟掉頭回來再吸。麥粒攤得很薄,面太寬,三輪吸了一趟又一趟……王二急了,那可是自家的口糧啊,就這樣便宜了這幫孫子?就這樣不做一點反抗?就這樣躺平裝死?就這樣眼睜睜瞧著……他掃一眼踩著他的那倆貨,他們的注意力也讓三輪吸去了,好像忘了腳底下還踩著個大活人。王二慢慢鬆開咬緊的牙關,張開大嘴,脖子一扭,照那個棒槌腳踝上咔嚓一口……那傢伙一聲慘叫,單腿跳躍著,一邊嚎喪去了。左邊的哼將被擊退,右邊的哈將反應遲了半拍,讓王二抓住腳脖子猛地一抬掀翻在地。被解放的王二猶如被解放的姜戈,一挺身爬起來,操起攤麥子的木鍁,瞄準三輪司機兜頭蓋臉一鍁拍了下去。
“哎呦,我日你媽!”司機從座位上滾下來與王二扭成一堆兒。司機看不出年紀,但年輕力壯,王二六十開外,是個老幹蔥,一招之間便見了分曉。王二且戰且退,自己打不贏就搬救兵,扯開嗓子喊:“抓賊啦!抓賊啦……”
村裡的老弱婦孺和老弱病殘艱難地起了床,抄上傢伙,顫巍巍地前來救援。賊人一看有援兵,撇下王二,剩餘的麥子也不要了,搖響機器駕車走人。老援兵們舉著糞叉揚著鐵鍬緊追不放。賊人一點都不慌張,撿起車上預備的磚頭瓦塊一陣狂投,矢石如蝗,砸得追兵們護頭的護頭,顧腚的顧腚——糞叉與鐵鍬哪有頭和腚重要,早不知扔哪兒去了。
鄰村得了戰報也來助陣,用鐵籬笆將路一攔,看你小賊往哪兒跑?賊人並不逞強,方向盤一打,三輪從容拐彎,由一條小路逃出生天,隨即逃之夭夭。
牛二的爹頭腦機靈,安慰王二:“不怕,我電話報警了,警察會收拾他們!”說完又衝賊人逃跑的方向啐了一口濃痰:“跑啊,讓你們狗日的跑,警察早晚把你們抓起來!”
路況太壞,三十分鐘後警車才風急火燎地趕來。民警問了情況,錄了口供,又風急火燎地返回去辦案了。
頹唐在地的王二在老婆的攙扶下站了起來,環視一遍狼藉的現場,抽泣抹淚說:“這一年可咋過吧,沒了糧食叫我們吃風屙屁嗎?”
他老婆沒有話,只跟著抽泣抹淚。
牛二追出兩裡地,羊屎蛋再次現了蹤跡,旁邊還有一堆新鮮的牛屎;繼續追,三百米外的地上又多出一堆驢糞蛋,而且正一絲一縷地冒著熱氣。牛二蹲下,一手持手電,一手用長矛撥弄那幾顆熱騰騰的排洩物,檢查一番後得出一條顯而易見的結論:離賊人不遠了。牛二心念一閃,沒來由地擔心起他老婆來,杭州那麼遠,不知這會兒她到了沒有?她中午搭的汽車,這一路要顛簸十三個小時呢。十六年前,他們夫妻承包了杭州市內一座小公園的打理工作,日常栽花種草,澆水施肥,除蟲噴藥……和種糧食沒啥區別,幹起來得心應手,薪水也可觀,另有五險一金,而且包住——公園角落裡有一間四四方方的小屋,窗戶只有巴掌大,屋內又黑又小,長年亮燈,那便是他們的廚房與餐廳。老婆平時兼管著公園裡一座廁所,打掃,沖洗,除臭……活不累,還有一筆補貼,最重要是廁所旁邊有間房子,專給管理人員配備,他們拿它當臥室——吃喝拉撒睡,全在公園內,上班下班,有活有錢,兩人相扶相持,日子過得四平八穩。兩年前,牛二襠裡起了個小疙瘩,就在睪丸之下,先是癢,後有點疼,一撓,破了,流血流膿。膿血流出來,不疼也不癢了,也就沒當個事。後來,膿血量日漸增大,三角褲上長天就沒幹淨過,老婆洗一次衣服催他一次,去醫院看看吧。牛二覺得沒啥,那點血他還流得起,人家那些小娘們哪個月不得流上二兩?病情一拖兩年,下面開始腫大,肉裡生出一條管子來,硬硬的,一擠,一股絳紫色的血水噴湧而出;牛二這才吃了心,揣上三百塊錢,到醫院去了一趟。拿回女醫生的診斷書,牛二向老闆告了十天假,在老婆陪伴下返鄉手術……手術完出院,每天都要清潔創口,老婆又在家伺候了幾日,眼下傷情穩定,後面躺著將養即可,凡事有老爹照應。昨天,牛二一早便指使老婆回城,公園裡的活計不敢耽擱太久,就怕野草瘋長,枯葉亂飛,到那時老闆不說話,市民也要說話了;別看那幫城裡人吃喝拉撒全在一座房子裡,餐廳緊挨茅廁,表面上卻乾淨得跟屎殼郎一樣。
牛二穩住心神,站起身接著追,這次還沒追出兩百米,一抬頭,正望見不遠處的一堆篝火。牛二熄了手電,握了握手裡的長矛,悄悄摸了上去。離目標一百米時,牛二發現火堆正生在一圈墳地中央,火燒得很旺,能聽見柴火噼噼啪啪地爆響。墳地之外全是麥田,接天連地,白天風吹麥浪,浪遏飛蝶。這個季節,麥穗已經上面,但麥芒還是軟的,麥葉還是青的。牛二伏低身體,慢慢趴入濃密的麥棵,然後匍匐前進,一肘一肘地往前挪,不弄出一絲聲響。這會兒天仍是黑的,但也不全黑,滿天星斗之下,遠處的白楊樹看上去像變異的蘑菇,黑乎乎的,高高大大。牛二往前挪了六十米,碰到一個小墳包,因為沒人添墳,墓土連年滑落,再過兩三年這隻土饅頭就將被雨水夷為平地。牛二側身斜靠在墳坡上,把腦袋伸過墳尖,讓視線浮在麥芒之上:好傢伙,前方四十米儼然一座小型屠宰場,就在那圈墳地當中,那堆篝火之旁。
“這夥人真是膽大妄為,嫌活物難帶,公然就地宰殺,只拉一堆紅肉回去——好計謀,好手段!”藉著火光,牛二看清了,他們一共三人,一人正用尖刀剝一頭牛的牛皮,另兩人各自把住兩條朝天的牛腿;一顆牛頭擺在旁邊一座墳前,牛角相犄,彷彿在獻祭。墳圈外圍則停著一輛機動三輪。
牛二看看手中的長矛,腦袋裡的CPU又開始活動了,同樣是三個故事一起湧入,一秒鐘後又同時輸出,誰也不知道它們在那個腦殼裡經歷了怎樣的操弄,牛二自己也說不清——
(1)那年村裡來了兩名鐵匠,一位五十歲的瘦師父帶一個二十歲的胖徒弟,倆人在村口支了個小攤,點火生爐,開始做營生。村民們收拾家裡的破銅爛鐵交到他們手裡回爐重鑄,打一口鍋,打一支鍬,或者打一把钁頭。牛二有一小段火車鋼軌,祖傳的,百十年了,一直在家擱著,平時拿它當墩子,在上面敲敲打打,不用的時候棄置一旁。村裡來了鐵匠,牛二也想打個新物件,就將鋼軌交到瘦師父手上,老先生看了看式樣,又掂了掂分量,說:“好鋼,想打個啥?”
“來支矛吧,”牛二答。
“您擎好。”
鋼軌放在通紅的爐火上,十來分鐘便燒得透體通紅,用鉗子夾出來擺在另一段鋼軌上(鐵匠也有一段鋼軌,用來當墊鐵),瘦師父的小錘叫,胖徒弟的大錘到,小錘叫到哪兒,大錘砸到哪兒。一陣敲打,鋼軌變形了,也涼了,再燒,燒紅再打,打涼了又燒……五次三番,矛的雛形慢慢就出來了。後來,瘦師傅和胖徒弟敲打得越來越快,矛的形狀也越來越清晰,這叫趁熱打鐵。小半晌工夫,鋼軌脫胎換骨成了一支鋒利無比威武霸氣的雄矛!瘦師傅夾住這件耀眼的兵器反覆比量,三驗五檢後,點了點頭,將其往清水中一投,嗤一聲,一團白氣升起;再撈出來,矛尖和矛刃上便多了一道藍瑩瑩的光芒,藍得攝人心魄。
牛二即刻就給新矛安了一根木柄,一米五長,雙手握住,正是近身格鬥之利器。然而牛二偏不這麼做,他由奧運會上的標槍得到靈感,拿長矛當投槍使,在家門口那棵大楊樹上畫了一個圈,天天練習飛矛射圈。開始技術很臭,經常射不中,射中了也射得極淺,一寸來深,怎麼看都不像射樹,更像給樹撓癢癢,但手藝都是練出來的,射樹十年功,中樹一秒鐘!牛二天天練,月月練,每次不練出一身汗決不歇息;說來也巧,練功那段日子他晚上竟然不盜汗了,牛二以為白天出汗太多,晚上也就無汗可出了。
苦練加上勤琢磨,兩個月出頭,那支長矛便如一條深具靈性的長蛇,指哪兒,射哪兒;射哪兒,中哪兒。從不失手。牛二仗著這招絕活在小二村的一眾年輕人裡坐上了頭把交椅。
(2)那天晚上,上半夜沒有月亮,沒有風,也沒有雨雪,就是個普通又幹冷的夜晚,天上悄悄下著霜,如果把白霜摩擦空氣的動靜放大一百倍,你就能聽到如蠶寶寶啃食桑葉一般的沙沙聲——實際你什麼也聽不到,在那樣一個安安靜靜人都睡死了的冬夜。夜半時分,下弦月從東天邊爬了上來,爬得很慢,好比一隻巨大的明晃晃的水餃懸在空中,勾人的饞蟲。有個新入行的毛賊仰頭望了它一眼,馬上吞了一升口水下去。他太想吃頓餃子了,最好是鮮肉餡的,帶點肥膘,油水足,解饞。他盤算了一遍行竊以來的收穫:五天前他用網兜從樹上像摘桃子一樣摘下一隻大紅公雞,可惜沒賣成,他娘說這麼好的公雞賣了怪可惜,不如留著上供用,於是拿去給他死去的姥爺當了五週年的供品;祭祀完畢,卻被舅舅一家人宰殺吃掉了,他連根雞毛都沒撈著。
四天前他挖牆根鑽進一戶人家偷了一麻袋糧食,連夜背到鎮上,壓得脊柱都彎了,買主是一間饃房的老闆,上來先宣告,以物易物。老闆伸出兩根指頭:“二十個饃饃。”他將沉得壓死人的糧口袋往地上一撴:“成交!”
連趕兩個夜班,毛賊乏透了,必須睡個好覺休整休整,順便保養一下身心——偷是個喪良心的活,他需要時間給受損的良知打個補丁。補丁打好,昨天他又出動了,他太想吃碗餃子了,可是沒錢,只好偷一點弄筆進項。老規矩,下半夜上工,凌晨兩點是組織細胞自我修復的時候,也是人睡得最沉的時候。時辰一到,他便撬開一戶寡婦門,想牽走她的羊,可前腳剛進院,後腳堂屋就傳出一聲咳嗽,男的,一陣悉索後起了床,估計要走人,或者要上茅廁。他暗罵一句:“日你娘,哪天來睡寡婦不好,非等今日老子來牽羊!”他退出去,關上大門,不露破綻,人就縮在院外一處牆角里等機會。那男的撒了泡尿,又抽了根菸,然後在院子裡轉悠開了,轉了又轉,一會兒再來支菸,不久再撒泡尿,他還沒完了!昨天的活就這樣給耽誤了。毛賊發誓,這碗餃子要吃不到嘴裡,誓不為人!誰料,今夜還沒出手就給逮住了。
他低頭大口吃著碗裡的肉餡餃子,眼裡卻有青淚垂了下來。這已是他第二次當眾招供了,第一次是在押解他的路上。此刻,他趴在飯桌的一角邊吃邊嘟囔:“再也不偷了,偷得沒有虧得多!”
(3)那天晚上,上半夜沒有月亮,沒有風,也沒有雨雪,就是個普通又幹冷的夜晚,天上悄悄下著霜,如果把白霜摩擦空氣的動靜放大一百倍,你就能聽到如蠶寶寶啃食桑葉一般的沙沙聲——實際你什麼也聽不到,在那樣一個安安靜靜人都睡死了的冬夜。夜半時分,下弦月從東天邊爬了上來,爬得很慢,好比一隻巨大的明晃晃的水餃懸在空中,勾人的饞蟲。二十二歲的單身漢牛二抬頭望了它一眼,馬上吞了一升口水下去。他太想吃頓餃子了,最好是鮮肉餡的,帶點肥膘,油水足,大補。牛二是因為腎虛盜汗被汗液泡醒的,這是他的老毛病,村裡的年輕人不問病因,只管嘲笑他手淫過度。牛二懶得分辯,只想趁早治好這個虛病。當時沒有營養快線,六味地黃丸也不好買,牛二隻好一直虛著,每晚汗出一身,半夜必須換件乾爽的襯衫,不然粘在身上溼嗒嗒的,過一陣汗涼了,又冷嗖嗖的。
這天夜裡,月移西南,牛二又醒了,迷迷糊糊扯掉身上溼透的汗衫,拿起枕邊備好的衣裳替換。不經意間,他隔著窗玻璃向外瞟了一眼,一條人影一晃而過,一瞬間從窗戶的這邊滑到了那邊。牛二一激靈,翻身下床,摸索著穿上鞋,提起長矛,貼牆游到房門口,猛地拉開門,挺矛向前,一聲炸吼:“抓賊啦!”
那條人影嚇得一趔趄,丟下手裡的豬娃,助跑兩三步,嗖一下竄上院牆,又一騙腿,噗通,跳入牆外的小巷中。
“抓賊啦!”牛二伸長脖子,青筋暴綻,活像一隻公雞吃力地打了個鳴。
小二村驚醒了,一分鐘前它還靜若一片史前遺址,在暗黃的月光下自顧沉睡。此時,每家的大門都已開啟,每扇敞開的門裡都躍出一條矯健的人影:劉二握著鐵鍬,彭二提著木棍,楊二拿著菜刀,胡二最簡單,舉著一塊板磚……領頭的牛二手持長矛,一米七八的身高朝月影下一站,黑塔一般威風凜凜,猶如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楚霸王。
“往哪兒跑了?”人群發出疑問。
牛二不答,一馬當先率領這支十數人的隊伍追擊前進,在村中的屋角與巷口間緊追不捨,開始瞧不見小偷,僅能聽見倉促逃亡的腳步聲遙遙在前。追到村子邊緣,終於望見了小偷的項背,但距離仍遠,藉著月光只能瞅見前方有個小黑點,像一顆蹦蹦跳跳的小黑豆。胡二耐不住性子,追著追著,突然一停,揚起板磚像扔手雷似的照準那個快速移動的黑點投了過去,尾隨磚頭而去的還有一句罵人話:“日你娘!”磚頭飛出一道弧線,砸空了。好在小黑點越追越大,追到村外的莊稼地,總算顯出了人形。前面一馬平川,全是青青的麥田。牛二狂追不停,右手攜矛,左手指揮隊伍兩路包抄。又追出四百米,小偷的身形越發清晰,他已經筋疲力盡,跑起來腳下拌蒜,東倒西歪,但追趕的人群也到了強弩之末,心跳如鼓,喘息如牛。牛二止住腳,長矛橫於右手,拉開架勢,衝二十步前仍在奮力奔逃的小偷喊道:“站住!老子的飛矛一出手,不見血不回頭!”
對方好似驚弓之鳥,身子一歪,倒地上不動了。
斗轉星移,二十八年後只剩牛二孤身一人捉賊了,手裡的長矛早已鏽跡斑駁,胯下還帶著傷;賊方卻有三人,個個身強體健,手持鋼刀,自己以一敵三,打起來幾無勝算。可若不打,來都來了,難不成就這樣眼睜睜瞧著?那可是自家的肥羊,就這樣便宜了那幫孫子?就這樣不做一點反抗?就這樣趴著裝死?牛二又瞅一眼手中鋥亮不再的長矛,它似乎也不如當年那麼長了,就像上了年紀的人身體縮去了一截子;他從心底發出一句感嘆:“當年這支矛是何等威風啊!”
牛二一半心神關注著賊人的動向,另一半心神忍不住回想起了那次捉賊的後續,此事雖只在頭腦中盤桓了半秒鐘,但仍讓他倍感受用——
他們押著捕獲的小偷連夜趕往香大樓村,一路上不打他也不罵他,只讓他招供都偷過什麼東西。小偷還不滿二十,滿臉青春痘,在眾人的裹挾下一邊趕路一邊老實交代入行五天來的偷盜經歷——其實他就想吃一碗大肉餡的餃子……講完,小偷開始討饒,乞求老少爺們放了他,以後再也不偷了。牛二不接他的茬,將長矛交與左手,右手拍著他的臉膛問:“你們村不是叫香太樓嗎,怎麼又叫香大樓?”
小偷像得了赦免,臉上擠出笑,哈腰點頭地解釋:“原是叫香太樓,太字那一點別人老看漏,一念就唸成香大樓……咱總不能老盯著糾正人家吧,叫著叫著就叫成香大樓了。”
“香太樓,香大樓,”牛二頓一下說,“區別還是挺大的。”
旁邊的人附和:“是不小,少了一點。”
小偷諂笑著:“就一點,沒啥。”
“不,那一點不比其他;那可是太字襠裡的一點!”牛二說。
小偷皮笑肉不笑,十分尷尬,其餘人則笑歪了嘴巴。
過一會兒,牛二對小偷說:“這次我們要給你個教訓。”
“教訓?”
“到你家去,以把兄弟的名義請我們吃頓好的,這事就算翻篇了;沒人會說出去,也沒人會把你扭送派出所,保證不影響你今後說媳婦。”
“你們要吃啥?”小偷陪著小心問。
“開三桌,每桌八個菜,燒雞、糟魚,肘子肉和煎蛋,每樣雙份,”牛二一根指頭一根指頭地往外伸,“對了,再單獨給你上一盤肉餡餃子。”
小偷算了算所需的錢數,肉疼得直嘬牙花子。
走不兩步,牛二又加一樣:“大米飯,要多放白糖和青紅絲。”快進村時,經與其他人商定,又添一樣:“張弓大麴,來五瓶。”
——牛二回過神時發現賊人們拾掇好了牛,下一步就要殺驢了;驢一看情形不妙,撒開蹄子彈跳著躲一邊去了,捉驢的人撲了個空,罵一句:“日你娘,待會兒再收拾你!”轉身又去捉羊,羊老實,沒事一樣臥在原地悠閒地倒沫。那人一把牽住繩頭,順勢扭住羊腦袋,另一人幫忙將羊按牢,第三人磨刀霍霍向牛羊——牛完了,輪到羊了。羊後知後覺,這會兒才回過味來,咩咩叫著亂踢騰。牛二看得分明,不能見死不救,他爹還指望這頭羊將來助他日進斗金呢。牛二想,不能趴在墳坡上一個屁都不放,他得行動起來,給那三個賊子一點顏色。
“抓賊啦!”牛二伏在原地,突然高喊,聲波如水波在曠野的平面上一圈又一圈地振盪。再看那夥賊人,膽小的撒腿就跑,贓物不要了,三輪也不顧了。膽更小的,一個屁蹾萎靡在地,腿腳已軟,跑也跑不了了。唯有那個膽大的,撇下羊,手裡的屠刀一挺,呵斥道:“日你娘,跑個卵?都過來,抄傢伙!”
膽小的跑兩步又回來了,膽更小的也從地上爬起來了,兩人各抓一把尖刀在手,學膽大那人的樣兒,雙腿下蹲,四目搜尋,準備迎敵。三人面朝外,一步一步後退,最終聚成一堆,背靠背,三柄屠刀各震一方。牛二沒動,也沒再出聲。三名賊人靠在一塊兒緊張了五分鐘,六隻眼睛骨碌碌地轉,全身心提防著偷襲……就趁這個空當,驢子一跳一彈蹄兒,撒著歡逃走了,一去不回頭,一支菸工夫便逃得沒了影。羊卻沒動,仍臥在原地一板一眼地反芻,好像事不關己。牛二咬牙切齒在心裡痛罵他家的羊:“日你娘,這情況了都不知道跑?你看看人家驢,都說蠢驢蠢驢,我看羊才他媽蠢!”
賊子們瞧瞧沒人殺將過來,便大著膽子留一人放哨,以防突襲,其餘兩人一起往三輪上裝載贓物,裝完被大卸八塊的牛,眼瞅著就要裝羊,牛二伸長脖子又是一聲咋呼:“抓賊啦!”
聲音從四面八方向墳堆中央聚集,放哨的人猛地一驚,雙手握刀,原地亂轉,生怕有人從背後殺來。裝載的兩人停下手腳,轉著腦袋聽了聽動靜,馬上又動手裝起來。
“他們看出我在虛張聲勢了,”牛二心說。
羊被塞入車廂,僅僅咩了一聲繼續反芻,滿嘴的白沫子垂下來,拉出一條條絲線。
“羊是靠不住了,”牛二忽一下站起身,“只能靠老子了!”他雙手握長矛,斜向上指,猶如出征計程車兵陣前罵敵道:“日你娘,偷了東西還想走?!”然後克服胯下的緊繃感,盡力擺出雄赳赳的氣勢迎上前去。
牛二並非沒想過用他最凌厲的殺招,飛矛刺敵。雖說矛和人都已不復當年,但他仍有把握一招得手;問題是他只有一支矛,敵卻有三人,撂倒一個還剩倆,那倆又不是吃素的,他雙拳難敵四手,何況那四隻手裡還有刀兩把,更何況他又是個硬充好漢的病漢!思來想去,牛二決定長矛不離手,一寸長一寸強,雖取勝不易,但大可立於不敗之地!
三個賊子這回沒有驚慌,見對方僅一人,勢單力孤,不用動員,每人自動操起一把尖刀,排成一行,列隊拒敵。牛二向前進逼了二十米,賊人非但不退,相反也往前進了二十米的軍。中間只隔十米時,雙方站定,開始相持。因為天黑,誰也看不清鼻子眼,只有四個人樣的輪廓站在麥田裡,像極了稻草人。僵持到第三分鐘,旁邊樹上的一隻烏鴉嘎一聲飛起,向遠處逃遁而去,除此再無別的響動。牛二遲遲不動換。賊人們耐不住優勢帶來的衝動,以至於忘了自己是賊,他們繼續前進,但腳步很慢,每個人都想出擊,卻又不想以身試矛。
牛二手裡的長矛指點一下這個,又指點一下那個,三名賊子被一一指了個遍,指誰,誰下意識地向後一縮,也僅僅是一縮,立馬又挺身向前。牛二的腿沒哆嗦,但心裡直哆嗦,他確切無誤地感受到賊人的氣焰正在高漲,而自己的氣勢已遭壓制,再拖下去賊人就要不戰而屈人之兵了。牛二暗罵一句:“日你娘,你們給我等著,咱來日方長!”罵完,矛頭調轉,拍馬便溜。賊人們緊咬不放。牛二聽到身後的麥稈被趟得沙沙響,彷彿有三條響尾蛇正尾隨而來,不過他溜得更快,緊走數十步後,身後的動靜越來越小,終於什麼響動也沒有了。他剎住腳回望,哪還有賊人的影子,遠處的火堆奄奄一息,而三輪早已啟動,三拐兩拐駛上大路,朝另一個方向逃奔而去。
牛二長出一口氣,這會兒才留意到褲襠已經溼透,不是尿,是血;剛才臨陣脫逃,只顧跑路,步子邁得太大,傷口崩裂了。牛二不去管它,望著賊人們遠去的三輪,他猛頓一下手中的長矛,屈辱的淚水像漲潮一般淹沒了眼眶:“日他娘,追賊的讓賊追得滿地跑,說出去還能見人不?”
胯下劇痛如割,牛二拄著長矛一瘸一拐往家走,邊走邊掉淚:“丟人吶,追賊的讓賊追得滿地跑,日他娘!”他反覆唸叨這句話,心裡極為不甘,快到村口時,突然抬頭對著沉睡的村莊大喊了一聲:“抓賊啦!”聲音傳過去,在街頭與小巷間流轉,撞到一戶戶人家的院牆和大門又反彈回來,音量不僅沒減,反而有所增強:“抓賊啦!”然而除了這聲迴響,再無任何變化,村子繼續沉睡,雞不叫,狗不咬,人聲不聞。
因為疼痛與激怒,牛二渾身發顫,他不死心,接著呼喊:“抓賊啦!”這次回聲沒了,忽有一群健碩的年輕人從村子裡急匆匆趕來,人影晃動,如幻如魅,有拿鐵鍬的,有提鐵棍的,還有舉板磚的……領頭那個捲起兩隻袖口,傲氣地說了一句:“老子的飛矛一出手,不見血不回頭!”
幽靜的夜晚傳來尖利的警笛聲,牛二他爹又報警了。牛二不關心警笛,也不理會傷口,直接從那些晃動的人影中穿行而過,就像穿過一團迷霧,他衝著無動於衷的村莊又是一聲喊:“抓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