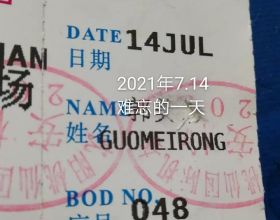前幾天掃雪至後院裡,不經意間車棚牆角處那破舊的木犁、籽耬,輪胎癟癟的架子車,還有用繩索懸吊在草棚木柱上被爹砍削得光溜溜且有很多枝叉的木鉤,牢牢地拽住了我的目光。 木鉤古樸如博物館裡遠古時代始祖們使用過的衣架,每個枝杈間都掛著我家騾子用過的圍脖、夾板、馱梁、鞍子等器物,上面灰跡赫然,仿若沉睡了幾個世紀。
我握著掃帚靜靜地看著這些老舊的傢什,許多許多關於爹的歲月如光影般一幀一幀閃現在眼前。
包產到戶後剛開始那幾年,自家沒有畜力是種不成莊稼的,爹借賬挖窟窿,狠狠心用幾百元買來一個一歲半大的齣鼻子騾子,頭小身矮,蹄圓胸闊,皮毛髮亮,拴在土坯壘起來的槽頭上,漂亮溫順得好像家裡剛娶來的新媳婦。家裡來了客人,瞟一眼騾子,都不由得喊出一聲好來。可它一旦調皮起來,就會抬頭噴鼻如吹銅號,低頭兩個前蹄輪換著刨地,一點都不消停。拉出去飲水的路上,常常人立而起,耍雜技一樣只用後腿走路。全家珍惜的不得了,即使家裡再忙,都會操心著給它按時給水給料。
硬體有了,軟體也得相應的配套。爹又狠狠心,去街上定製了一輛鋼管框架的架子車,在那個年代,這已是很氣派的家當了。
這還不夠,還得給騾子量身打造合身的鞍轡。爹閒時就坐在院落裡,用剪子刀子鉗子在一堆皮條繩索間忙活,額頭上彌一層細細密密的汗珠,晶亮如油,時不時起身拿著做好的繩套在騾子身上比劃長短寬窄。臨了,還不忘用粗糙的手掌在騾背上摩挲疼愛一番,溫柔得像撫摸自己小兒子的頭頂一樣。那神情,由不得讓人鼻管一熱。
第一次使喚騾子,是村組裡要修渠,給各家分配了拉石頭的任務。爹套起騾子車,我跟著爹去發過洪水的石河裡拾石頭。石頭重,爹怕累壞了剛調教的騾子,還怕砸壞了架子車,輕裝慢放的只裝半車。偶遇坡道,爹便重重地喊我,娃,加油搡啊!這一聲喊,就是命令,於是,騾子朝後抿著耳朵,擰著兩瓣年輕肥碩的屁股攢蹄使勁拉,爹斜著身子在前面轅條上使勁拽,我也顧不得屁股上補丁開裂的聲音,在車尾巴上抻長了身體使勁地推。到坡頂了,騾子呼吸平穩如常,我和爹倒呼哧帶喘的。車至平地處,我屁股一轉,偷偷地一蹦子跳坐在了車幫上,爹意識到了,回頭瞪我一眼,我趕緊識相地跳下來,羞臊地連路邊樹上麻雀的嘰嘰聲,聽起來都像是在一聲聲的嘲笑我呢。
在那個以畜力為主的年月裡,對爹來說,騾子就是他的啞巴兒女,理應受到更多的關心和體貼,容不得健全的兒女去欺負。爹還專門從雜物堆裡找出一個破舊的鋼絲刷,閒時就給騾子順順毛,以培養感情。
慢慢的,騾子被爹調教的會拉架子車了,但只會拉車的騾子不算好騾子,還得讓它學會犁地、拉耬、拖耙等等莊稼地裡的全套活路。
可調教騾子得有農具,在那年月,農具一樣是稀罕金貴的物件,哪能經常滿村莊去借別人家的呢?尤其耕種儲墒的季節,錯過時機就會影響一年乃至下年的收成哩。
爹請來村裡最好的木匠,翻騰出數年間陸陸續續積攢的木料,盡由木匠師傅手掌翻飛、砍削刨鑿。不幾日,雙鏵的木犁雙鏵的耬,和渾身長滿釘齒的木耙都做好了,新嶄嶄地散發著木料的清香。爹顫抖著手撫摸著這些屬於自己的農具,眼裡溢淌著幸福的光芒。
有了騾子,有了農具,還得有搭對的牲口。好在已分家另過的哥哥,也騰挪著買了一頭毛驢,雖然兩家土地畝數懸殊,但總是父子間,也無須計較很多。
我家水旱兩地都有,尤其旱地,煌煌野野,一眼望不到頭,竟佔了多半個山嶺面積。這要是在過去,擁有這麼多的土地,我爹肯定是地主老爺了。但現在是新社會,人人平等,都得靠自己的雙手來生活,再說家口眾大,還有未成年成家的兒女們呢,好幾張嘴巴如雛鳥一般等著吃飯哩,犁田耕地對爹來說理所當然就是重中之重了。
由於地塊大,得十天半月才能把該犁的地全部犁過去。天光微亮,爹已經吆著牲口在旱地裡犁了好幾個來回了。
晨風習習中,木犁在犁溝裡順暢地前行,犁齒上不絕地傳來草根被扯斷的叭叭聲,新翻的土地散發著潮溼且甜腥的氣息,像剛出鍋的酒氣,聞聞就醉人呢。
放眼看去,碩大的地塊裡,犁紋如浪,一波波地往遠處山頂的雲層裡盪漾而去。
在後來的日子裡,爹眼巴巴地在等,等一場適時適量的秋雨,好為明年的春種做儲墒準備。騾子則在槽頭上將養著因重役而帶來的疲累。
幸賴政通天應,總能盼風風來,祈雨雨至。一場透雨之 後,爹又趕著騾子去耙地了,來來回回地一耙緊挨著一耙,如同梳子般,把我家的莊稼地梳得毛絨絨的,碩大地塊裡連一個小土疙瘩都找不到。耙地的次數要看老天爺的脾氣,為了儲墒,每下一次雨,就得耙一次地,直到深秋不下雨為止。
人勤地不懶,第二年莊稼上場後,摞起了一個歪脖子大麥垛,遠遠地看,頭往北傾,像鞠躬的姿勢,似在答謝爹的付出。走近了再看,又像一個做了好事的孩子,站在那裡得意地等待著大人的表揚。
那年,水地收了七石麥,旱地也收了七石麥,糧豐倉滿,這在我家的歷史上,是空前的。
這僅僅是夏收的喜悅,地裡還有秋禾呢!
還剩一半的地塊裡,已經分麋的糜子,每株糜穗上都垂掛著數不清的籽粒,如同綴滿了珍珠的女子髮辮,閃著耀眼的亮。望著一大片的糜子地,還有糜地裡套種的麻子,爹走走停停,然後蹲在地頭,手掌託一把糜穗,掂掂分量,眉眼裡含著平日少見的笑,那眼角的喜紋就拉得愈發深長了。
那一年,拔光糜子後的地裡,麻子棵長得像樹一樣高,我們在麻子樹林裡嬉戲打鬧,鼻息裡盡是麻子成熟的味道。置身在麻子叢中的騾子時隱時現的低頭安靜地吃著草,尾巴在秋陽的撩撥下,悠閒地左甩一下,右甩一下,儼然一副衣食無憂的樣子。
在接下來的好多個年份裡,爹的腳掌印和騾子的蹄印,印滿了水旱兩地的角角落落。這點點印跡最後都變成了糧倉裡的顆顆麥粒,變成了我們身上結實的肌肉,變成了一家人的聲聲笑語。
日子一季季不停地遠去,莊稼一輪輪不歇地生長,生活一年年地好了,爹卻漸漸老了,下巴頦的短髭長成了長髯,嗓子眼的短咳也變成了長咳,過冬猶如過難。多年的氣管炎和勞累讓爹一年年的萎頓下來了。
差不多的日子裡,二十齡大的騾子,滿身金黃的毛片也逐年變成了灰黃,也像爹一樣時不時咳嗽幾聲,聲音空曠而短促,只不過行事更加老道和謹慎。說到這裡,有兩件事最是讓人感慨唏噓。
有一次,爹吆著騾車領著孫女去走親戚,半路上途徑一坑窪處,孫女從架子車裡不慎彈落在地,眼看著車輪就要從孫女身上碾壓而過時,騾子一個急剎車,車輪距孫女臉蛋堪堪僅一寸之遙,有驚無險使孫女躲過了一劫。還有一次,那是一年夏天,騾子在槽頭閉眼休息,在抬蹄換腳之際,踩到了鑽在肚皮下的小雞娃,內疚之下,幹了壞事的那隻蹄子,兩三天內不敢落地,就那樣晝夜提著。一提起這兩件事,就不由得使人眼眶發紅,懷念起它來,雖說是個牲畜,可在我們心裡它就等同於我家的大功臣。
人老了,身體就會生毛病,騾子也一樣。騾子先於爹扛不住了,眼眵糊滿了眼角,躍躍欲滴,滿槽的草料,嘴唇翕動就是不肯下嘴去吃。爹說,生病了,去給看去吧!我們拉著騾子到處找獸醫,但最終回天乏術。眼看著一日日消瘦下去的騾子,在糾結、不忍中我們最終把它交給了販子。
爹站在莊門口,眼睛紅紅的,看著販子身後連路也走不動的騾子,漸漸地越走越遠,直到朦朧成一團若有若無的虛影。
沒過幾年,爹也走了,但爹沒給我們給他看病的機會。在那年年關將近的時節,在灑滿陽光的院落裡慢慢低下了他倔強了一輩子的頭顱。
我們把爹埋在了他耕種了一輩子的旱地裡,讓他每天都能看到兒孫們在他的身邊勞作,看那一季季莊稼成熟,看日升日落,看雲捲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