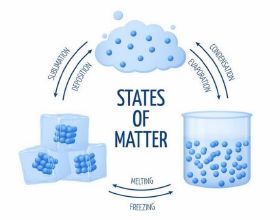入秋時山下的酒家開壇了去歲釀的秋月白,知道周子舒惦記著,於是溫客行早早就下山去買。
那天周子舒做了個夢,本是仰在美人榻上閒閒等著老溫回來,不曾想便睡了過去。夢裡也不知哪年哪月,只朦朧知曉猶是少年時,他獨自在四季山莊的庭院裡練武,手中無劍,只一段香紅花枝。
那時也是黃昏,夕陽斜斜的鋪下來,風過時吹徹小庭深,深深淺淺的紅被吹皺似縠紋,翻花為波,攢香如浪,輕易便撲了人一懷春色。
恍惚間身後有破空聲來,他一個翻身,騰手去捉,落地時緩緩攤手,卻見展開一掌新紅,開到極盛的海棠,小小成簇。
少年溫客行自花樹上探著頭,鮮色的衣衫隱在春光裡,那海棠便彷彿要開到他眼角去了。花影斑駁的拂在他眉目之間,瀲灩著,初融滿池春冰,卻尚未盡數化開,只叮叮咚咚的清脆的碰撞。
東風扶頭軟,少年自那溶溶裡粲然生笑,開口來喚:
“師兄。”
周子舒輕輕一抬手,將手中海棠挑在花枝末端,腕子借力,不偏不倚卻又將那一朵拋了回去:
“師父教的新招數練好了麼,就貪玩。”
哦,那時還有師父。也不知是哪一年。
溫客行笑著接住花,起身躍下樹來,輕巧巧正落在周子舒面前,雙指一併,便將海棠別在他衣襟。溫客行挑著眉,像被風吹開的兩痕春雲 ,被柳染了翠,被山映了黛,被無數的風流顏色捧著——風流、自然是好風流,少年宜笑,春色宜花,皆是上上等風流。
他對周子舒講:“師兄,春色正好,恰要多流連呢。”
這到底是哪一年啊,周子舒在夢裡斷斷續續的想,是哪一年的海棠開的那樣好,哪一年的溫客行這般貪玩愛笑。
又是哪一年的自己,只知風月不知愁。
多情春、無名日、少年時。
周子舒想要拉住溫客行的手,可身子往前一撲,竟然就醒了。
那時天色將暗,屋裡還沒上燈,只一懷空落落秋涼,周子舒緩緩揉了揉額角,暗道好笑,分明已是逢秋,竟還做入春的夢。
還未及再想,卻聽見溫客行風風火火的跑進院子,隔著門望去,他手裡還抱著兩隻圓滾滾的酒罈。
“阿絮,阿絮!”
他這樣喊著。
“你快出來啊。 ”說話時他已經跑進來,急忙忙把酒罈放下就去拉周子舒手臂,“你快出來看。”
“發生什麼了?”周子舒搖晃著被他拉到院子裡,有殘夢未褪時,頭尚有些暈。
就見溫客行抬臂指向遠處,聲線微微揚高:“阿絮,你看,海棠花開了。”
“這時節怎麼會有…”然而他在下一刻怔住,縱目處拂了一際晚霞,烘雲蒸海似的,杳杳似海棠驟然發,一夕之間,映了半邊叢山遠。那紅是徹底紅,只勻了點纏綿悱惻的青,分明照眼而來,醺醺學春醉。
周子舒微微偏過頭,看見溫客行的眉山也勻開抹晚霞的顏色,像是那最嫵媚的花紅都沸在他面上,而溫客行也正緩緩看過來。
“嗯,海棠花開了。”
多情春、無名日、少年時。
逢君便是。
更多浪漫之情,上“愛發電”解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