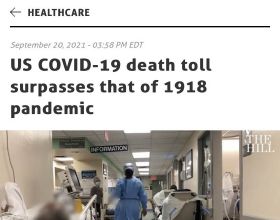請點選上方藍字 關注我們
編者按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被稱為“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上海是黨的誕生地。2017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大閉幕僅一週,習近平總書記就帶領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程從北京前往上海,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嘉興南湖紅船。習近平總書記說,這裡是我們黨夢想起航的地方。我們黨從這裡誕生,從這裡出征,從這裡走向全國執政。這裡是我們黨的根脈。為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我們就中共一大考證的相關問題和研究,採訪瞭解放軍後勤學院教授邵維正少將。
一、關於中共一大召開日期和
出席人數的考證
《上海黨史與黨建》:邵教授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您是第一個準確考證出中共一大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黨史專家。1980年,您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上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引起轟動效應,不僅解決了“一大”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這兩個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且被視為中共黨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開端。當時,是什麼促使您進行這項考證的?
邵維正:關於中共一大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是40多年前做出的。可以說,這件事本身也成為歷史了。1979年,李新同志帶領一個團隊借住在中央黨校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共12卷, 1983年至1997年先後出版)第一卷《偉大的開端》。關於“一大”的考證,那是在當時特殊條件下完成的,是在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引下,是革命前輩胡喬木、李新同志扶持的結果,我只做了一點具體工作,微不足道。
1978年,全國範圍掀起了一場真理標準大討論,開啟了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哲學、歷史、經濟學各個學科的研究也活躍起來。當時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同志,提議要編一部多卷本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為什麼有這個想法呢?他說:俄國十月革命搞了兩個月,蘇聯史學界把它寫成了50多萬字的《蘇聯國內戰爭史》(第二卷),史料挖鑿深入準確,場景描述十分細緻,如寫開會誰坐在哪裡,穿什麼衣服,發言時的表情都有記載。後來電影《列寧在1918》以及反映十月革命的小說、詩歌、繪畫等藝術作品,很多就是根據這本史書改編髮揮而成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搞了30年,從1919年到1949年這30年的鬥爭波瀾壯闊,像戰略決戰的三大戰役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罕見的,革命的規模、拼搏的激烈、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十月革命。所以,胡喬木同志深情地說,我們這代人應該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寫成一個長編,載入史冊,傳至後代。
長編第一卷書名就叫《偉大的開端》,主要寫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這三件大事都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因此叫《偉大的開端》。長編第一卷《偉大的開端》於1983年3月出版發行,產生較大的社會反響。後面的各卷陸續展開,由相關研究單位和高等院校分別承擔,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才把整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12卷圓滿完成。
這部700餘萬字的宏篇鉅著,詳盡而又生動地反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30年曆史,尤其是首卷《偉大的開端》,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當時正處於改革開放的熱潮之中,中共黨史的研究和寫作,更是強調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記得那時陳雲同志曾專門講過,“黨的歷史事實要一錘子一錘子敲定,以後要翻也翻不掉”。胡喬木同志也講,寫黨史一定要把史實搞清楚,一件一件事情都搞清楚。當時這個重大專案的主持人是李新同志,他是老革命,1936年就參加學生運動,在延安時期和胡喬木同志就認識。李新同志是一位非常嚴謹的史學家,親自主持這個歷史長編的研究和編寫,要求我們把《偉大的開端》寫的每一件事都要搞準確。
編寫組分工,我起草《偉大的開端》第二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共一大的初稿部分。關於黨的一大的召開時間,通常說法是1921年7月1日,可是真正查證資料的時候,發現說法非常多。有6月、7月1日、7月5日、7月20日,還有7月23日以及7月底等各種不同說法。而且在海外中共黨史論著中對此也早有議論,有的反動分子還以此攻擊中國共產黨。為了理清思路,把黨的一大召開的具體情況搞清楚,我按寫作時間、刊載日期、作者姓名、發表出處和開會、閉幕日期等各種不同的說法,排列出“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當時就這個問題給李新同志作了彙報,我說:“關於‘一大’召開日期的說法很多,沒有辦法寫,是不是可以先做考證,考證清楚再寫書。”李新同志聽後非常支援,他說:“你先不要著急寫書稿,先把這件事情考證清楚,弄清楚以後再寫。”
《上海黨史與黨建》:的確,您所作的關於中共一大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本身就是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釐清史料、嚴密考訂的過程。您當時是怎麼開展考證的呢?
邵維正:很長一段時間,關於“一大”召開日期的主流說法是1921年7月1日。考證就從一大代表的行蹤開始。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3人,一一考證他們到上海的旅程和時間,結果顯示7月1日在上海的代表只有5人,這樣就先排除7月1日開會的可能性。為了做好考證工作,這段時間我經常奔跑在各圖書館、檔案館和資料室,多次採訪當時在世的“一大”親歷者包惠僧、劉仁靜和王會悟。
1979年,我曾訪問過劉仁靜多次,因為劉老經歷比較曲折,幾經磨難,顧慮很多,對提出的問題回答常常是“年歲大了,想不起來了”“這件事我不知道”。我一想,這事急不了,只有耐心等待、啟發。採訪慢慢有了轉機。有次我問他:“您是什麼時候從北京出發的?您先到的哪裡?”劉老沉思片刻回憶道:“我好像沒有直接到上海,從北京出發以後,我先到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參加過年會後才到上海,但是具體時間記不住了。”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打開了突破口,得到這條寶貴的線索,尤其得知少年中國學會有個會刊《少年中國》雜誌,我接連幾天跑了幾家圖書館、檔案館,因《少年中國》後來未出影印本,原件很難找到,最後還是在中央黨校的圖書館庫房裡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國》雜誌。原件上記載,1921年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是7月1日至4日在南京召開的,每個人在會上的發言也都記載下來了,上面明確寫著劉仁靜於7月2日由北京到達南京。這次年會開了3天半,劉仁靜有兩次發言,而且在“會員訊息”中記載:會後劉仁靜赴滬。這與他的回憶相符,劉仁靜到上海只能是7月5日以後。我趕緊把劉仁靜在會上的發言抄下來,做了一個卡片,也給劉老複製了一份。後來再去訪問劉仁靜的時候,把發言記錄給他看。想不到還能看到自己幾十年前的發言,他看後非常激動地說:“對,這就是我當時講的話。”這樣就把他的話匣子打開了,他終於相信我是為研究黨史來訪問的,而不是要抓什麼問題。之後我再去訪問他的時候,問什麼問題,他就講什麼問題,沒有什麼顧忌了。
歷史考證要儘量避免孤證,因為孤證缺乏說服力,也不足於定論。僅憑一個人的回憶也會有侷限性,所以我對當時在世的“一大”親歷者包惠僧、劉仁靜和王會悟等都作了多次採訪,又儘可能多收集一些文獻資料,相互對照印證,力求準確、合理,有說服力。考證文章從三個方面展開:一是代表行蹤,二是可以藉助的間接事件,三是當時的文字記載。考證的突破口選在代表行蹤,道理很簡單,出席者不到齊不可能開會,而各地代表到上海的交通工具和出發時間各有不同,直至7月20日前後才陸續到齊。這說明中共一大不可能在7月上中旬召開,只能在7月下旬。考證的第二個依據是間接事件,因為中共一大會議的原始記錄未能儲存下來,只能間接求證。其實文內所用孔阿琴被殺案,原本與“一大”沒什麼關聯,只是時間概念的印證。中共一大會議有3個日期要弄清楚,即開幕日期、被巡捕房搜查日期、南湖續會日期。多位代表回憶和當時上海報道的孔阿琴案,與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會址發生在同一個晚間,孔案的時間、地點是公開報道的,這就可以印證搜查是7月30日。嘉興南湖的紅船會議有幾個不同的說法,尚待深入研究。嘉興同志近幾年作了不少努力,希望大家再加把勁找出更確鑿的論證史料。考證的第三個依據是從共產國際檔案中轉來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是比較可信的史料,與前兩個方面互為補充,相互印證,經過綜合分析比較,可知中共一大是7月23日開幕的。具體內容可參考關於中共一大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文章。
這項考證發表之後,在黨史界引起了不小反響,而且還有連鎖反應,比如遵義會議,過去講是在1935年1月8日召開的,實際上不是,經過考證,準確的時間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關於“一大”的考證不僅在黨史界有較大影響,還引起了國外的關注,翻譯成為英文、日文、俄文、法文。國外有位專家評論說:“這項考證說明,中國共產黨開始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研究自己的歷史了,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國內外對這件事的看法,已超越了具體史實的考訂,而上升為思想路線和治學態度,認為這是改革開放的體現和成果,意義自然就更大了。
中共一大的考證,首先要歸功於黨重新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與革命前輩胡喬木同志、李新同志的支援指導是分不開的。“一大”考證初稿寫出來後,李新同志親自推薦到革命博物館的內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上發表。胡喬木同志正是先在這份內參上看到考證初稿,他認為多年沒有弄清楚的問題講明白了,而且還排出了“一大”會議每一天的議程和內容,這樣的成果應該公開向國內外介紹。那時正在籌備《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中、英兩個版本,國內外公開發行),喬木同志親自推薦這篇文章,公開發表時再次作了修改訂正。此外,還應該提到編寫組其他很多同志為考證做的幫助、支援和保障工作。
二、關於李大釗、陳獨秀
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上海黨史與黨建》:今年是建黨百年,方方面面都推出了不少慶祝百年的優秀作品,比如前段時間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從而也再次引發了關於李大釗、陳獨秀兩位黨的主要創始人為何沒有出席“一大”的討論,對此,您是怎麼看的呢?
邵維正: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沒有出席黨的一大,這是多年來人們普遍關切和疑惑的問題,還有什麼比建黨更大的事?有關論著提及此事時,常常以“因公務繁忙”一筆帶過。100年過去了,這個問題也有必要說說清楚。
李大釗之所以沒有出席“一大”,原因之一是北京黨支部沒有選舉他“出席一大”。再一個就是李大釗當時正在北京領導八所國立院校開展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索薪鬥爭”。
1921年6月,北京黨支部接到上海黨組織要求派遣兩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一大”的通知時,正在西城區舉辦青年補習學校,於是就在補習學校裡選舉了出席的代表。據在場的劉仁靜回憶:“1921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兩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於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
1979年9月14日和10月29日,我在兩次訪問劉仁靜時,都談到北京黨支部選舉“一大”代表的問題。他對此作了更為詳細的補充:“那時我們並沒有意識到,‘一大’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覺得只是各地組織派代表去上海碰個頭,不必驚動大釗先生了。第一個提名的是張國燾,此前他去上海就住在陳獨秀家,為李大釗與陳獨秀聯絡溝通,並參加全國學聯的組織工作,是一個很活躍的人物,因此獲得一致透過。第二個提名的是鄧中夏,他自己說要到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年會,接著還要去四川演講,時間上衝突了。第三個提名羅章龍, 他也說暑期已安排好,不便改動。接著提名劉仁靜,因沒有特別的安排就定了,我就這樣做了個不合格的‘一大’代表。實際上當時並沒有推舉李大釗,大家心目中大釗先生是指導我們的,這樣跑跑顛顛的事我們年輕人去做就可以了。”
劉仁靜講的這些理由今天看來,似乎難以成立並顯得幼稚,如果聯絡到黨在建立時期的社會環境,有許多不確定因素,也就不足為奇了。
另一方面,李大釗因領導“索薪鬥爭”,1921年六七月間已經成為北洋政府關注和監視的人物,即便他自己想去上海,那時也是無法離開北京的,因此,“去上海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
而當時李大釗親自領導的“索薪鬥爭”,表面上是為了解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迫切的生活問題,實質上卻是反對北洋政府的黑暗統治。1921年6月3日,李大釗親自帶領八校教工隊伍在總統府前英勇反抗,被反動軍警血腥鎮壓後昏迷在地,不省人事。他負傷後繼續堅持鬥爭,迫使北洋政府最終接受了高校教工的合理要求。這種不畏強暴,甘冒風險維護教職員工切身利益的精神,激勵了成千上萬的教育界人士,並透過經濟鬥爭,達到反對軍閥統治的政治訴求。李大釗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站在鬥爭第一線,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光輝形象。
陳獨秀未出席黨的一大,同樣有著身不由己的特殊處境和具體情況。1920年12月,陳獨秀應陳炯明的反覆邀請,從上海赴廣東擔任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學預科校長,主持教育工作。此前,他曾就去廣東一事寫信徵求李大釗意見,李大釗認為領導廣東教育的同時,還有兩個重要作用:一是可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思潮帶到廣東;二是可以在廣州發起成立共產黨組織。建黨初期以及後來的秘密工作時期,黨員都不是職業革命家,黨組織也要求黨員儘量職業化、社會化,一來可以隱蔽黨員身份,再者也能維持本人和家庭生計。所以陳獨秀在1920年年底離開上海前往廣東,同樣也肩負著建黨的重任。而陳獨秀在廣州期間,曾以不少精力重建和指導廣州早期組織的工作,使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黨組織。“在他的主持下,於1921年春開始成立真正的共產黨。當時取名為‘廣州共產黨’。”廣州黨組織的重建,實現了他與李大釗的約定。
1921年5月初,李漢俊、李達派包惠僧到廣州,要陳獨秀回上海主持黨務或把黨的機關搬到廣州,陳均不同意。5月中旬,由於李漢俊催促,加上教育經費延撥,陳獨秀提出辭呈。陳炯明親自登門挽留,並答應撥款100萬元。6月中旬,陳獨秀接到李達來信,請他回滬主持黨的一大。陳獨秀組織廣州的黨員召開會議,表示他不能回上海,因為他正在爭取一筆建大學校舍的款子,他一走款子就辦不成了,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
1979年4月至6月間,我曾先後四次訪問包惠僧,包惠僧比較詳細談到他兩次去廣州的情形:當時陳獨秀抓廣東教育的力度很大,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遭到守舊勢力的強烈抵制,在報刊和會議上幾次圍攻陳獨秀,罵他為“陳毒獸”。陳獨秀堅持己見,頂著頑固勢力的壓力,一項項抓實,所以他覺得這個當口上不能離開。至於參加黨的一大,陳公博代表廣州,既然陳獨秀自己去不了,委託包惠僧去吧。那時陳獨秀的威望很高,一言九鼎,他定了其他同志也就認可了。
陳獨秀雖然沒去出席“一大”,但他對黨的發展和建設是有思考的。他讓陳公博帶去一封信給與會各同志,信中提出4條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指導;三曰紀綱;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對發展黨員,黨內的民主生活,加強黨的紀律和制度,以及發動群眾、建立工農政權的準備等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意願和建議。
黨的一大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後,馬林多次提出要陳獨秀回滬主持中央工作,並說世界各國共產黨都沒有領導人在資產階級政府做官的先例。上海黨組織又派包惠僧去廣州彙報上述情況,同時接陳獨秀回滬。8月,陳獨秀再次向陳炯明辭職,當時在廣西的陳炯明仍然挽留。9月11日,陳獨秀以治療胃病的名義請假回滬,包惠僧一起同行,仍住在上海老漁陽裡2號,主持中央局工作。不久,陳獨秀在住宅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經多方營救,20多天後交了罰款獲釋。
關於李大釗、陳獨秀未出席黨的一大,還有一種說法:如果李大釗、陳獨秀同時出現在上海,會受到進步青年和新聞記者的熱情追隨。他們都是社會名流,尤其是進步青年的偶像,同時也是北洋軍閥政府重點監控物件,會被反動當局跟蹤監控。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一大的秘密會議也就“秘密”不了了。密探和巡捕房的搜査就不會是“一大”的第六次會議,大會很有可能在一開始就受到衝擊。
李大釗、陳獨秀雖然沒有出席“一大”,但並沒有影響“一大”的召開,也沒有影響他們作為黨的主要創始人的地位和作用。
三、關於包惠僧“一大”代表身份的考證
《上海黨史與黨建》:改革開放以來,關於黨的建立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由於史料等原因,仍有一些問題如包惠僧的代表身份等存有爭議,我們很想就此聽聽您的看法,以及今後《上海黨史與黨建》黨的建立史這個欄目如何辦得更好,希望能夠得到您的指導。
邵維正:我對八位“一大”出席者——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李達、張國燾、周佛海、陳公博、劉仁靜的回憶都進行了整理分析,這八人的回憶都曾提到包惠僧,在包惠僧參加了“一大”會議上是一致的。
至於包惠僧是不是代表以及所代表的地區問題,說法是不一致的,毛澤東和陳公博兩人沒有說明包惠僧代表哪個地區,董必武、陳潭秋兩人說包惠僧是代表廣東出席會議的,張國燾、周佛海兩人說包惠僧是代表武漢出席會議的,李達和劉仁靜兩人則說包惠僧是串門參加會議、是列席代表。此外,還有一種說法,就是包惠僧是受陳獨秀委派去參加“一大”的。這幾種說法哪種更接近歷史事實呢?
包惠僧1921年上半年在廣州住了兩個多月,是在上海參加慶祝“五一”的活動後去的,在此期間參加了廣州黨組織的活動。7月中旬從廣州動身去上海,參加黨的一大。關於這段情況,包惠僧本人有如下回憶:“廣州的黨員有譚平山是支部書記,北大畢業生。陳公博,也是北大畢業生,法專的教授、宣傳員養成所所長、《廣州日報》總編輯。《廣州日報》是陳獨秀辦的,我也為該報寫過文章。還有譚植棠,是教書的,也是北大畢業生。劉爾崧,是個中學生。還有一個姓李的教員,加上陳獨秀和我,共七個人。黨員們每週開一次會。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會後就可以回去(會前陳獨秀與我談過,還讓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經接到上海的信了)。”
首先,雖然包惠僧原是武漢的黨員,但他不可能代表武漢出席。上海發起組通知各地區派兩名代表出席“一大”,董必武、陳潭秋無疑是代表武漢的,武漢不可能派出3名代表。而且,包惠僧1921年上半年沒有在武漢工作,從這方面講他也不可能是武漢代表。
其次,包惠僧作為廣州代表證據也不足。雖有兩個當事人和包本人說是代表廣州的,包也的確是從廣州動身參加“一大”的,但有些疑點還不能排除。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記載:“參加大會的有十二名代表,他們來自七個地方,包括上海在內,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有兩名代表的地方是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這是無疑的。一名代表的地方就是廣州和日本了。陳公博的回憶中也只說包惠僧參加了會議,並沒有說他代表廣州。如廣州只有一名代表的話,首先應是陳公博,包惠僧畢竟是後來去廣州的,而且時間也不長。至於文中所說十二名代表,是指“來自七個地方”的代表,並沒有排斥還有第13人參加會議的可能。因為當時上海已有李漢俊、李達兩名代表,他們又請陳獨秀回上海參加會議,假如陳獨秀當時回上海參加“一大”的話,出席“一大”的也不是12人。所以,這段引文對判定包惠僧是不是廣東代表還是起作用的。
第三,說包惠僧是串門碰上參加會議、是列席代表是不合情理的。黨的一大是在秘密狀態下召開的,不可能隨便允許人串門參加會議。退一步講就是串門參加的,碰上一二次會還有可能,何以能從上海開幕到南湖閉幕都碰上參加呢?再者,當時還有幾個黨的骨幹在上海,他們怎麼沒有參加,而唯獨包惠僧千里迢迢從廣州到上海來串門參加呢?因此,這個說法是站不住的。至於說包惠僧是列席代表, 那是用後來的習慣推論的。事實上“一大”並沒有嚴格的手續和程式,沒有正式和列席代表之分,只要參會就有同等的權利。包惠僧在“一大”會上先後就黨的綱領、職工運動、對孫中山的看法等內容發表了意見,並參加了最後的選舉,不能說是列席代表。
第四,說包惠僧是由陳獨秀委派參加“一大”的,比較符合事實。包惠僧在入黨前就和陳獨秀相識,後來交往也多,彼此較為了解。包惠僧當時也具備參加“一大”的資格,陳獨秀對他今後工作又有些打算。加上陳獨秀自己不能去上海參加“一大”,就委派從上海來和他聯絡的包惠僧參加。實際上,包惠僧在“一大”以後再次到廣州,傳達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央局的意見,請陳獨秀回上海主持黨的工作。另外,從陳獨秀當時的地位和威望來看,他委派包惠僧參加“一大”也是完全可以的。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地,建立史的研究既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又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貴刊建立史欄目辦得不錯,已經有很大成績,本著精益求精的要求,提3點建議:一是加強建黨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的研究,充分用史實而不是概念,論證黨的誕生是歷史的必然、人民的選擇。二是對黨的建立作理性昇華。黨的一大、二大,包括四大都在上海召開,黨中央早期的很多機關也在上海,一方面要注重從黨的綱領、決議等檔案中提煉總結黨的早期探索和基因密碼;另一方面加強對黨的建立的系統研究和對中國建黨特點的研究,以及初心使命的認識。三是由於建黨處於秘密狀態,加之原始文獻大多未儲存下來,史實的考訂還要繼續做下去,尤其是新史料的挖掘更要下苦功夫。
《上海黨史與黨建》:您對中共一大若干史實的考證,體現了您實事求是、嚴謹細密的治學思想,建黨百年之際作一回顧,使我們獲益匪淺。您對黨的建立史欄目和刊物的寄語,使我們備受鼓舞,激勵我們繼續把黨的建立史研究推向深入,把刊物辦得更好!謝謝!
(整理:賈 彥)
(原文刊載於《上海黨史與黨建》2021年第3期)
掃碼關注我們
來源 / 《上海黨史與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