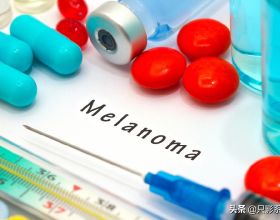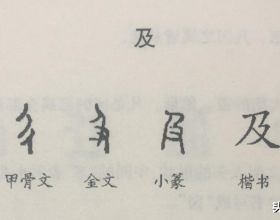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愆”是一個形聲字。本義是過錯;罪過的意思。《說文》給出的解釋是:“愆,過也。”
夫子說:“在所侍奉君子的面前說話容易犯三種過失:直接說的話,卻說不到點子上,叫心浮氣躁;說話能夠說到點子上,但這時候卻不說了,這叫隱瞞;不看君子的臉色就貿然開口發言,這叫盲目。”
我們來看經文,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子說:“在所侍奉君子面前說話容易犯三種過失。”
“侍”的本義是在尊長旁邊陪著。《說文》給出的解釋是:“侍,承也。”還有服務他人的意思,引申為服侍、侍奉。
《論語》中,“侍”出現五次,顏淵季路侍。(《論語·公冶長篇》)“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論語·先進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論語·先進篇》)這句話的“侍”意思是學生陪從於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論語·鄉黨篇》)指地位低的人陪從國君。本章句《論語》的“侍”也是地位低的人陪著地位高的人。
中國自古就有禮儀之邦之美譽,地位低的人在上司、尊者面前,是要嚴格遵守各種禮法制度的,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下級在上級的旁邊陪著應該注意的事情。在“君子”面前,地位比較低的人一定要小心,孔子講了說話的三個注意事項,否則就容易發生“三愆”。我們看,這三種過錯就可以避免,誰需要注意啊?當然是侍奉君子的人了。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出現,那就是我們了。如果一注意,你自己就有可能少犯這三種錯誤。到底是啥樣的過失啊?我們接著看。
“三愆”的第一“愆”是“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直接說的話就叫言,和人家討論的話,甚至還稍稍有點責難的意思,就叫語。
“躁”是一個形聲字,本義是出現眾多的事物要動。《說文》給出的解釋是:“作趮,疾也。”引申性急,毛躁,急躁,不冷靜。
孔子說;直接說的話,卻說不到點子上,叫做心浮氣躁。“未及之”意思是沒有說到重點,這就是說,有說話的積極性,但能力不夠啊,效果是“言不及義”,沒說到點子上。一個人光有態度,卻沒有內涵,說話都是假大空。孔子說,這叫“躁”,這是一個人急於表現自己,出發點是為了自己的名聲,甚至利益。
陳蔡絕糧期間,孔子一直在撫琴,引導同學們唱誦《詩經》,不讓弟子們和圍困他們的兩國大軍動手,如果真打起來了,孔子和弟子們都不能存活下來,這樣的話,孔門恐怕真的成空門了。陳蔡兩國大軍一圍困孔子師徒七天,看這些人只是彈彈琴,唱唱《詩經》,覺得孔門弟子不像是壞人,就放他們走了。
就在第六天的時候,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論語·衛靈公篇》)子路來到老師身邊發牢騷說;君子也有窮途末路的時候嗎?一看子路耐不住性子了,孔子說;君子固然免不了有窮困的時候,但君子能堅持操守,不像小人,窮困了就開始胡作非為了。意思是,急什麼啊?急只能壞事,其實,孔子早已安排子貢同學去楚國搬救兵了。
如此來看,子路一急,說話說不到點子上。老師說;子路,你這是心浮氣躁。
還有一則《論語》,講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說;說說你們的志向吧。子路愛出風頭,搶著第一個發言,立即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孔子當時的態度是“哂之。”淡然笑了一笑。後來孔子解釋了原因,那就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不懂得禮讓,還是修行不夠啊!孔子強調的是“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說話急躁,就容易失於謹慎。因為話一出口就無法收回,所以儘量要少說或者慢說。
反過來看“言及之而言。”“言及之而言”就是孔子所說的“中”,說話點中關鍵,切中要害。這樣呢,孔子自然很是喜歡。我們來看下面一章句《論語·先進篇》,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魯國的執政者計劃改建藏放財貨的長府庫。閔子騫說:“保持原有的老樣子,怎麼樣?何必一定要改修呢?”孔子說:“這個人平日不大開口,但一說話就切中了要害。”閔子騫是孔門四科之一德行科的第二名,修行的功夫相當高,自然不會心浮氣躁,“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是孔子老師對他的褒獎。
有些人自以為是,又很急躁,喜歡打斷別人的發言,喜歡在別人說著說著就插話,這都是輕浮不穩重的表現。前兩天,我在周口市區七一路八一路交叉口悅學書院下面的一個英語培訓機構參加周口市朗誦學會籌備會。期間有一個叫踏青的老同志,是一位醫生,他很喜歡朗誦,只是表現欲太強,生怕別人不知道有自己這麼一號人物,生怕埋沒了自己學問才能,一有機會,他就不厭其煩的說自己多麼多麼的厲害,殊不知,參加籌備會的很多人都是周口市區專業的主持人和音樂界的高手,本來不會唱歌的他給大家說樂理知識,真是魯班門前弄大斧——充內行!讓人很是生厭。
《論語·憲問篇》記載公明賈說公叔文子是“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公叔文子啊,他該說的時候就說,所以別人不討厭他說話。這是智慧啊。當然了,不該說的時候,你在那兒說,這就是輕浮,不穩重。
我們來說“三愆”的第二“愆”,那就是“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隱”的本義是藏匿;隱蔽。《說文》給出的解釋是:“隱,蔽也。”
“言及之”就是說話點中關鍵,切中要害。但這時候卻是“而不言。”這究竟怎麼回事兒?我們慢慢聊。
孔子說這句話的前提是“侍於君子”,就是作為一個地位低的人,你在一個地位比你高的人面前,用毛主席的話說,你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孔子怎麼做的啊?當魯哀公問他“弟子孰為好學?”孔子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在季康子問他同樣話題的時候,因為兩人的地位基本平等,孔子說:“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同樣的話題,省去了“不遷怒,不貳過”這六個字。對於魯國的國君,凡是知道的,全部都說出來,毫無保留。對於一個在魯國處處僭越禮制的當權者,你搭理他那麼多幹啥啊?
你能做到“言及之”,但這時候“隱”。這裡面有幾點可以思考的。一、本來你能說到點子上的,但怕這件事情會牽涉到一些人的利益,於是,你就“不言”了,這是什麼?一切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天下人的利益出發的。就像商朝的丞相比干,他為什麼要“諫而死”啊?是因為他如果不這樣做,他覺得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儘管知道可能自己要死,但能為國家留住一些正義,他依然無怨無悔的勸諫商紂王。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再回頭想象《論語・季氏篇》開篇章節,孔子批評冉有季路的一段話,覺得很有意思的。明明季氏攻打顓臾是不對的,冉有季路不去阻止,還說那是季孫氏個人的想法——“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立即對冉有的說辭給予批評說,你們是季氏的家臣,你們的主人將犯下錯誤,你們應該拉一把的——“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季氏危險而不能護持,跌倒了不去攙扶,那麼,還用你們這些家臣幹什麼呢?意思是你們這些人幹啥吃的啊?食人之祿,忠人之事,這是必須的;否則的話,就是“則將焉用彼相矣?”君子對於一個事情,你要麼贊同,要麼反對,說出自己的理由就可以了,你不說,“隱”,我對這個問題沒什麼意見?你們怎麼做?我都是沒有意見的。明明你有能力“言及之”,但卻選擇了“隱”。孔子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錯誤的,為啥呢?因為一個人對於上級,或者是父母尊長,應該坦誠以待。“言及之”說明你有一言中的的能力,但這個時候卻不說了,“隱”了!這似乎有些“欺上瞞下”的味道,與儒家提倡的忠恕之道是相違背的。
“三愆”的第三“愆”是“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顏色”指面容和表情。以此可以瞭解一個人的心情,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謂的察言觀色,根據情況對說話內容和表達方式適時做出調整,這是能夠贏得對方認可,這是講說話要注意時節因緣。
“瞽”是一個形聲字。本義是瞎眼,雖瞎但有眼珠。這裡表示沒有見識、沒有觀察力的人。
相傳,一縣官借壽辰之便,邀縣裡名流赴宴,伺機斂財。一賓客借行酒令的當頭,編詩諷刺:“生得長臂兩條,專把油水來撈。慣於挑肥揀瘦,也愛戳戳搗搗。本性兒貪得無厭,混得個油頭滑腦,若得此君不幹,除非它已吃飽。”縣官一聽,登時紅臉,場面一下子冷了。
此時一個舉人插話說:“兄臺的謎底,可是筷子?”眾位賓客大笑,尷尬立解。出謎的賓客借題發揮,固然伶俐。可縣官也不傻,抖了這個機靈,早晚引火上身。答謎的舉人則真是有智慧。他看準了無人開口的時機,從容應答,既幫著席間一眾度過了尷尬場面,又把畫風轉移給筷子,變相援護了出謎者,可以說是一個察言觀色的人。
孔子說:“未見顏色而言”,不看君子的臉色就貿然開口發言,這叫盲目,叫做睜眼瞎。有個笑話,說一個人請客吃飯,第一次僕人問他:“客人中只有一人沒到,可以開席了嗎?”他說:“唉,該來的沒來。”過了一會,僕人又問:“客人都到齊了,可以開席嗎?”他回答說:“唉,不該來的全來了。”結果,所有客人都被得罪。雖然是個笑話,可也反映出會講話有多重要!
說話不合時宜,這也是過失。與君子談話要抓住談話的時機,既不能早,也不能晚,既不能多講,也不能不講。要恰到好處,拿捏好分寸,把握好火候,這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過猶不及。
孔子所列舉的“三愆”,不僅對弟子們以及當時的人們有幫助,而且對現代人也有啟發。
孔子總結了三條準則:直接說的話,卻說不到點子上,叫做心浮氣躁,這是愛出風頭,沒有禮貌,修養不夠的表現。說話能夠說到點子上,但這時候卻不說了,這叫隱瞞,這最容易讓人懷疑你有什麼企圖。不看君子的臉色就貿然開口發言,這叫盲目。
禍從口出,事實上,“三愆”近乎自取其辱,如果不注意,受傷的只能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