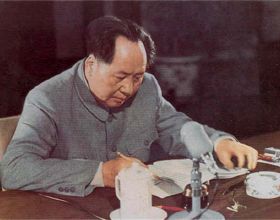毛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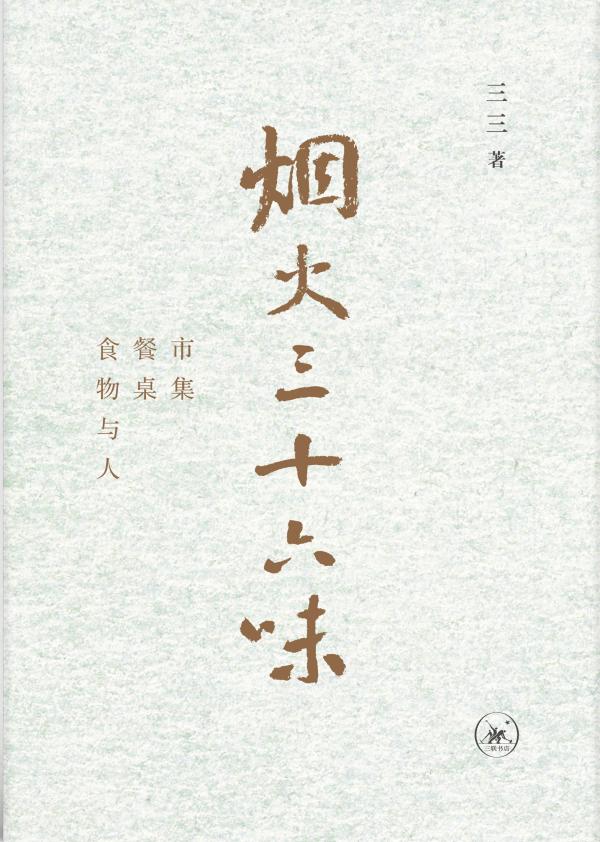
《煙火三十六味:市集·餐桌·食物與人》,三三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10月即出,358頁,78.00元
我小姨父不善言辭,家境不好,外婆最後鬆口,是因為小姨夫會吃。懂吃愛吃的男人,不會對女人太不好的。這是中國人的信仰。
如果有一個吃的奧運會,蒸、煮、煎、熬、滾、汆、涮、煲、燙、炙、滷、醬、風、臘、燻、糟、醉、釀、炒、熗、炊、燒、爆、炸、灼、焗、燜、炆、燴、熘、焯、煨、烘、燉、煸、烤,估計場場飄五星紅旗。從小到大,人生最隆重的事情都必須體現在吃上。生日,一桌。祭日,一桌。工作了,吃,失戀了,吃。我小時候有個鄰居叫八爺,八爺花哨,整個弄堂的年輕女孩都被他吃過豆腐,夏天晚上,乘涼的時候家長裡短有人替八大娘鳴不平,我外婆一句話就噎死他們,你們要有八大娘福氣,天天起床被伺候一碗牛肉麵,再替她喊冤。
忙完早飯忙中飯,忙完中飯忙晚飯,食物是最好的感情表達。契訶夫有個短篇叫《牽小狗的女人》,苗師傅在《文學體驗三十講》裡提到過。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古羅夫在雅爾塔對安娜·謝爾蓋耶芙娜,一個寂寞的上流社會女人動了心,一個回合之後,他向她提出,“我們到您的旅館裡去吧”。契訶夫沒有接著描寫他們在旅館裡做什麼,隔一段,他寫了這麼兩句:房間裡的桌子上有一個西瓜。古羅夫給自己切了一塊,慢慢地吃起來。在沉默中至少過了半個鐘頭。
苗師傅很有把握地說,這是一塊事後西瓜。納博科夫也同意,他認為這個西瓜時刻是契訶夫的高潮,“這裡有普通人稱為浪漫史的東西以及契訶夫稱為散文的東西”。俄羅斯文學史上特別迴腸蕩氣的室內一刻,就因為是西瓜嗎?因為西瓜清甜,多汁,粘手嗎?
西瓜當然是有功勞,不過重點在吃。慢慢地吃。就像《花樣年華》(2000)裡,梁朝偉和張曼玉對切牛排,但在他們之間轟鳴的是一次次的蓄勢待發。劉別謙的電影《天使》(1937)中,黛德麗的丈夫突然帶老友道格拉斯回家用餐,僕人端上牛肉,三人中,只有被綠的呆萌男主人把牛肉吃了,女主沒吃,道格拉斯把牛肉切成一小塊一小塊,也沒吃。
所以啊,食物從來都是最完美的人生譬喻。工作是飯碗,失業炒魷魚,嫉妒是吃醋,雄起時候就甩對方一句,小爺我也不是吃素的。吃是漢語中最活躍的動詞,也是最有抒情能力的詞彙。香港電影能抗衡好萊塢,首先就因為港片為全球電影示範好吃。
許鞍華的《女人,四十》(1995)開場煙火流麗,阿娥菜場挑魚,逡巡好一會,看中一條,老闆過秤,“一百五”,阿娥說,“五十,上面不是寫了嗎!”老闆解釋,那是死魚價,阿娥理直氣壯,我在你這裡站這麼久,不就為等它死嗎,老闆茫然之際,阿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拍出了魚的最後一口氣。鏡頭一轉,魚已經在阿娥的砧板上。
香港導演拍吃有傳統。食神系列倒是其次,最好看的吃常常發生在段落間歇。早些年,像成龍在《醉拳》(1978)裡吃麵,元彪在《雜家小子》(1979)裡吃白斬雞,洪金寶在《鬼打鬼》(1980)裡吃烤鴨,都屬名場面,不過打的都是吃的形意拳。然後周潤發出來,《老虎出更》(1988)雖然算不上好電影,但發哥一口氣在玻璃杯中敲下十二個生雞蛋,然後一口乾的場面,直接把吃變成了港片全型別裝置。像銀河映像,電影中大量接頭、轉折和收場,都選在餐桌或餐廳爆破。杜琪峰的《放·逐》(2006)中,有一場戲,五個殺手,放棄各自背道而馳的任務準備攜手幹一票。於是,他們一起做了一頓飯。張耀揚林雪搭建大飯桌,張家輝收拾椅子,黃秋生摘菜,吳鎮宇炒菜,這是杜琪峰蝕骨柔情的銀幕表達,四分鐘的吃飯戲用了高對比暖光,每個男人都性感又美好,既是童年,又是愛情。
吃就是命。吃就是天。吃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歌可泣的行為。愛人會欺騙,同志會背叛,吃卻從不歪曲也不糾正我們的情感和慾望。吃好了,片子就有了精氣神。葛優倪大紅吃得好,《羅曼蒂克消亡史》加一分。劉若英烤鴨沒吃好,《天下無賊》就減一分。前不久剛播完的《叛逆者》,鱔絲面的表現比王志文和朱一龍都好,而因為鱔絲面這麼好,再也吃不到鱔絲面的王志文才會讓人格外痛心。相反,後宮劇裡的那些塑膠滿漢全席,憑空就增援了小主們的演技塑膠感。當代文藝,太輕視食物的表現力。當年,《愛情麻辣燙》裡,和邵兵一見鍾情之後的徐靜蕾隔夜清晨下樓去買早點,結果端著一鍋豆漿油條,卻找不到邵兵家在哪裡了。這一段油條演技出奇的好,剛出爐的油條開始生機勃勃,被徐靜蕾端著走了幾戶人家敲錯幾個門後就躺平了。油條,在那一刻,幾乎讓徐靜蕾進入了教科書。
吃就是我們本質。《我的團長我的團》憑著第十二集就能名垂影史,龍文章鼓唇弄舌說了整整一集,開始報地名,後來報吃食:“北平的爆肚,涮肉,皇城根;南京的乾絲燒賣,還有銷金的秦淮風月,上海的潤餅,蚵仔煎,天津的麻花狗不理,廣州的艇仔粥和腸粉,旅順口的鹹魚餅子和炮臺,東北地三鮮,酸菜白肉燉粉條,火宮殿的鴨血湯,臭豆腐……”
吃就是祖國,祖國就在我們的味蕾裡。最好的家國教育,永遠是餐桌教育。所以,看到三三的《煙火三十六味》,真是太有好感了。
三三是美食專欄作家,但不染美食作家的習氣,沒有常見的富貴盈桌,也沒有行業的年份官氣。一簞食一瓢羹,食物是大地恩情,也是人間喜悅,三三筆下的鴨子長魚白米青蟹,幾乎有春秋風。從平常心進,以平常心出,她和食物,圖一個彼此清歡,也因此,飲食中最難寫的食材和蔬菜,三三反而駕輕就熟。她寫南京人吃草,夏天的蘆蒿,春天的馬蘭頭,還有清明時分的金陵菊花腦,汪曾祺看了,估計也坐不住。到台州,把台州的海鮮寫得活色生香不稀奇,因為大自然豐沛到目不暇接,但三三把台州的時蔬寫得人舌尖生津,是本事。看過三三筆下的台州“糕”“水”,幾乎憑生惆悵,如果瞿秋白臨刑前吃一口台州的豬油紅糖饅頭和豆腐,我們後人會覺得安慰許多呀。
因為這個緣故吧,大魚大肉我大抵走馬掃過,最好的人生在雜咸和醬料裡。“小魚小蝦,菜梗樹葉,切塊切粒,鹽醃、曝曬、封浸,鹹中帶甜,鹹中帶辣”,這是最低階也是最高階的人生。一個女人就是在醃菜中建立她的霸權和王國的吧,我那半封建半女權的老媽,常常就一邊醃冬瓜一邊教育我和姐,不會醃菜怎麼嫁人。
當代社會已經把醃菜的位置讓給了撒嬌撒野,而透過《煙火三十六味》,我們得以一瞥在進化過程中,當下丟失了多麼隆重的手藝和品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我們學校後門做鍋貼下餛飩的阿姨如今在哪裡啊,在她那一把蔥花撒上去之前,我們一個個俯首帖耳,生怕惹她不開心,把一整鍋煎得過熟,那一口汁就沒了。因此,三三寫下的,不僅是天南地北的人生,更是食物民族誌。
也不知道是先天的家學基因,還是她後天的個人修為,她的食物書寫特別秉具一種歷史感,常常,在開頭,她寫一句,“2018年出梅的日子提早了一週”,然後,她會信手拈來一些史料片花,比如,“茶館在成都遍地開花,不過是兩三百年間的事。這習慣似乎始於清初,朝廷為徵西藏、川西大小金川,調滿洲蒙古兵二十四旗入川”。一個美食作家的胸襟憑空開闊,如此,她寫下的香格里拉,才是掃蕩了小資情調的飄著飯香的一個平民高原。
平民性,是食物和美食的區別,也是這本書最有親和力的地方。一路看,一路想到我自己的食物往事。如果要問我最好吃的一頓飯,我會回答你,那是在南潯,薛毅熬了一鍋雞湯,燒了薺菜豆腐羹,我們問他,雞怎麼整,他吐一口菸圈,說,扔了。羅崗燒了八寶鴨,鴨子是他親自從集市上挑的,他還讓鴨子出來走了幾步,親切地摸了摸鴨子的頭,讓賣鴨子的女人深深覺得自己遇到高手了。紅燒肉,文尖偉哥曉忠煉紅本來想競爭上崗,不過在羅崗說出“外焦裡嫩”四個字後,大家都默默退下了。小董包了餛飩,小雷拍了黃瓜,餛飩裡有手剝的蝦仁,黃瓜裡有臨時的蔥花,最後春林不服氣,斜叼一支菸從廚房端出乾煸四季豆。那一頓飯,適合用《百年孤獨》的開頭句式:多年以後,面對薺菜豆腐羹,我們都會想起那隻被始亂終棄的走地雞。
食物串聯一生。一生就是一個飯局。我外公從來不讓大人在飯桌上訓斥我們,飯桌就是現實主義最浪漫的時刻,就像《放·逐》中的四分鐘。電影最後,李雪有一個發問:一噸夢有多少?一噸愛有多少?一噸辛苦有多少?李雪夢一樣的問題,其實電影都已經回答,那就是:一頓飯。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