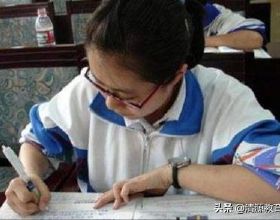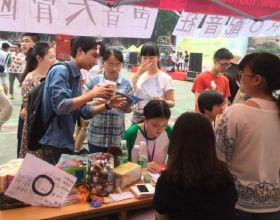宋寶穎/製圖
我有過的閱讀經歷,可能你也有過。
初學寫作時讀到一篇名家散文,感覺寫得好,欣賞佩服,水平太高。忍不住再讀一遍,然後再讀一遍,就不覺得高不可攀了——我也可以用他的寫法,寫出這個事物的另一方面,或者去寫另一個事物,同樣會讓人欣賞,讓人佩服。
在這個時候,名家散文的高度沒有降低,閱讀者的高度有了升高,也就拉近了距離。我說的是這種應該有的狀態,可以有的狀態,在一些寫作者那裡確實有過。他們低頭向名家學習,為的是抬起頭來,成為新的名家。
不然的話,長江的後浪怎麼能高過前浪?
好作品的一般標準,一是內容好,二是技巧好。你要把這二者加上聯絡,再融合起來。簡單來說,在你的筆下,好內容需要好技巧,好技巧需要好內容。這些都要從模仿開始,學到優秀作家的本事。
舉例來說,很多作家寫過喝茶,有的給人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有的就沒有。
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中用了很容易理解的比喻:嚴格地論起來,茶在第二泡時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個十二三歲的幼女,第二泡為年齡恰當的十六歲女郎,而第三泡則是少婦了。
郁達夫在《故鄉的秋》中對比了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在北平即使不出門去罷,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來住著,早晨起來,泡一碗濃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綠的天色,聽得到青天下馴鴿的飛聲。
汪曾祺在《泡茶館》中寫了聯大學生的喝茶,用了與郁達夫相似對比:學生生活窮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卻能自許清高,鄙視庸俗,並能保持綠意蔥蘢的幽默感,用來對付惡濁和窮困,並不頹喪灰心,這跟泡茶館是有些關係的。
三毛看到非洲沙漠上人們愛喝苦茶,找到了一個比喻,在《三毛傳》裡可以看到:飲茶必飲三道,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甜似愛情,第三道淡如清風。
上面的幾個例項,兩個對比,兩個比喻,手法都很簡單。當然,複雜的手法也有,這裡沒舉例,一堂面對隱秘讀者的散文寫作課,可不想讓人眼花繚亂。
簡單的寫作手法,也能創造神奇。
蘇童《一杯茶》寫道:喝的不僅僅是茶味。有時透過玻璃凝望水中那些綠色的芽尖,你可以輕易地獲得對水泥牆鋼條窗外的山野自然的想象,想象萬樹萌芽,想象雨露雲霧,想象日出月落時的大片大片的綠色世界。
在《黃雀記》中,蘇童用了茶的比喻:他們之間的默契脆薄如紙,稍不留神,便破壞了。他們的過去是一杯腐茶,盛在同一只杯子裡。必須小心杯蓋。打開了杯蓋,腐茶的秘密也就暴露了。不能開啟。不能相認。不能說話。
前面兩個示例,蘇童也用了對比和比喻兩種手法。很明顯,他的敘事更靈活和開闊,有了延伸。如果說蘇童有過模仿老作家的經歷,我們就可以說他拉近了距離,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超越。
蘇童是小說家,寫過的散文不多,其中有些好作品,能給初學者當範本了。那些散文出了一種又一種新選本,也有人願意讀。
有讀者評價蘇童散文時,說的是自己喜歡的理由,無意中說出了他與前輩作家的不同:智慧來自對世界冷靜的觀察和醒悟,這樣的文字是有力量和重量的,沒有任何賣弄才華之嫌,卻讓人印象深刻。他不僅提供了細膩的生活枝節,而且直接指向精神的內涵,還有觀察世界的角度。
看起來,以前我們要與林語堂他們拉近距離,現在要與蘇童拉近距離。
都想拉近,怎麼拉近?
我建議:要學蘇童與前輩作家拉近距離的方法。
首先在閱讀中確立楷模。每個作家靈魂深處至少有一個精神導師,一位也許已經逝去多年的、時代久遠的作家,能激起寫作的興趣,帶來思想的碰撞,陪伴孤苦的練筆。
“現在寫不好不要緊,不知道寫什麼的時候就多看看老作家們是怎麼寫的。”蘇童說,“每一個初涉寫作的人都要耐著性子大量地閱讀偉大作品,珍視每一個與偉大作家精神相通的機會。那些讓自己記憶深刻的作家作品會影響自己一生的寫作。”
其次是閱讀要講究質量,講究體悟,讀得好才能寫得好。
“如果只是普通的文學愛好者,怎樣閱讀都無可厚非。但如果希望透過閱讀對寫作有一定的益處,系統合理地讀書就顯得格外重要了。”他說,“要能夠從書中有所得、有所思。在讀書時應當適當地做筆記,不光是優美的詞句,還有作家對文字、情節的某種處理方法。”
像蘇童說的那樣,大量閱讀偉大作品,我們會結識一位又一位精神導師,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被他當成精神導師的博爾赫斯,曾在隨筆中寫道:我一貫主張要反覆閱讀,我以為反覆閱讀比只看一遍更重要。我對書就是這樣迷戀,這樣說未免有點動情,當然我們不想太激動,我只是對你們說說自己的心裡話。
博爾赫斯是世界上閱讀最多的作家,也是被人閱讀最多的作家。他寫小說,也寫散文、詩歌。他的散文讀起來像小說,小說讀起來像詩歌,詩歌讀起來又像散文。
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克塔維奧·帕斯特別欣賞博爾赫斯那句話:“時間是構成我的物質。時間是帶走我的河流,但我即是河流;時間是燒掉我的火,但我即是火。”他覺得博爾赫斯的小說詩歌散文是罕見的完美作品,是文字和精神物件,是一種幾何構成,充滿了幻想,既理性又任性,既堅固又耀眼。
約翰·厄普代克向博爾赫斯學了更多的東西。比如,在敘述的創新方面,萌生了一種對技巧危機的清醒意識,還覺得博爾赫斯在文學本身之內提出了某種本質的改變,似乎讓技巧和風格的改變已經結束,把文學的未來變成了現實。
卡爾維諾也把博爾赫斯當成精神導師,覺得他極其豐富的意念,他的敘述和暗示,他的理念和密度,都在他語言節奏的多樣化、句法運動的多樣化中傳達出來,並不讓人感到擁擠。他創造了風格上的奇蹟。
餘華認為,博爾赫斯洞察現實的能力超凡脫俗,他外表溫和的思維裡隱藏著尖銳,只要進入一個事物,就能深入進去,這正是博爾赫斯敘述中最為堅實的部分,也是一切優秀作品得以存在的支點。比如他在《秘密奇蹟》的最後這樣寫:“行刑隊用四倍的子彈,將他打倒。”這是一個奇妙的句子,博爾赫斯告訴了我們“四倍的子彈”,卻不說這四倍的基數是多少,於是這個無法計算的數字顯得無限遼闊。
在上面幾個舉例之外,學博爾赫斯的作家還有很多,卻沒有聽說誰宣稱超越了他。他是個很高的標杆,很難越過。
但我們仍然要有這樣的標杆,當作跨越的目標,然後一直去跨越。到後來,我們可能發現,我們終於沒有跨越博爾赫斯,但我們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目標,才跨越了除他之外的很多作家,這是一種意外的收穫。
特邀編輯:董學仁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