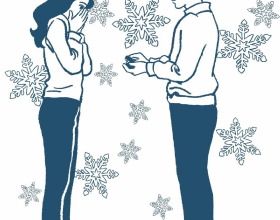在雁北,蓋新房都要盤炕。盤炕之前先要脫大坯,大坯就是炕板子。脫大坯屬於“四大累”之一:“脫大坯、修大壩、站著××、牛頂架!”××是什麼?不能說,太黃!
脫大坯先要挖土,得勝堡外御河邊上的土地特粘鍬,幾鍬下去汗就上來了。脫大坯光粘土不行,還要摻黃土和沙子,比例要適中,要不日頭一曬就變裂子了。和泥的勞動強度非常大,屬於民間俚語“四大累”之一。先在小山一樣的土堆中間挖個坑、灌滿水,此舉叫洇泥,泥洇到了才能和。和泥前,還要撒上大橪,大橪就是鍘碎的麥杆麥秸。
為了把泥與橪和勻,必須用二齒耙一遍一遍地捯。然後兩腳上去踩,一腳下去沒過了膝蓋,甚至到了腿根。兩腳不停地交換,直到把泥踩得像和好的面一樣柔韌。此時人泥合一,象上帝初創世界時的亞當與夏娃。
脫坯其實很簡單,就是找一塊平整的場地。把一個正方型的木框坯模擺好,然後把餳到了的泥鏟進坯模裡,再在泥裡擺上幾根木棍作為加強筋。泥一定要塞實、塞嚴、塞勻,坯面一定要刮平。如果鼓出個包來,炕不平,晚上咋睡?
說慢做快,其實真脫起來一氣呵成。最爽的一道工序就是,兩手猛然往起一抬,瞬間提起坯模。但見一塊齊稜齊角、平平整整的大坯,就這樣誕生了。
數天後,大坯基本乾透了。然後把大坯集中在一起,兩橫兩豎地摞起來。再在坯垛頂上苫上草簾子,就等著秋高氣爽那最佳的盤炕季節到來。
盤炕是一門非常艱深的手藝,涉及到建築學、材料學、燃燒學、熱力學、流體力學等諸多的學科領域。在炕和灶臺的連線處,我們當地稱之為“嗓子眼”的地方,就是雙曲線造形的,現在火力發電廠的冷卻塔外形採用的就是雙曲線。至此,你才知道老祖宗傳下來的炕,還有這麼深奧的學問吧?
過去的手藝人盤炕全憑經驗。比如,嗓子眼留的小了。沒風天時抽力小,煙氣就排不出去;嗓子眼留的大了,有風天時,炕內抽力大,煙火都抽進炕內,鍋暫且開不了,做不成飯。
如果炕內冷牆部分單薄,保溫不好,冬季冷牆就會上霜、掛冰,熱量損失很大;同樣,如果冷牆抹得不嚴,走風漏氣也不會好燒。
炕面不平,上面可以用泥找平。但煙氣接觸炕板子底面時流動的阻力就大,影響分煙和排煙速度,又直接影響炕面的傳熱效果。
炕內的迎火磚和迎風磚擺放不當,也會造成炕內排煙阻力大,造成排煙不暢,增大炕頭與炕梢的溫差。
另外,如果“炕洞”“狗窩”“落灰坑”太深,炕內就會積存大量的冷空氣。灶鑊點火時,炕內的冷空氣與熱煙氣就會形成熱交換,產生渦流,致使灶鑊不好燒。
灶鑊裡的柴禾燃燒後,產生的熱量和濃煙,要在炕板下面彎彎曲曲的煙道里“繞行”一遍,才能順著牆上預留的直洞往上猛衝,冒向天際。為了增強吸力讓煙冒得更順利,這個直洞的出口,不能與房頂齊平,而是要高出房頂三尺多,這高出的部分就叫煙堗(雁北音窯)。煙堗用四塊磚靠邊直立,中間形成一個方形的口子,上面兩層是兩縱兩橫花擺著的四塊磚,形成東西南北各留一口的格局,上面再用平磚蓋頂。風力不大時,炕煙會順利地冒出。如果風力太大,產生“倒灌”時,則需要人上房用磚把上風方向的口子堵上,讓煙從下風方向的口子往出冒。
經過世世代代的使用和改進,雁北的“炕文化”已然成熟。記得我那時爬上得勝堡的堡牆,家家戶戶房頂上高高低低粗粗細細的煙堗一覽無餘。如果正趕上做飯的時分,每家的煙堗裡都冒著縷縷的青煙。煙堗裡冒煙,是人丁興旺的象徵。如果哪家的煙堗裡不冒煙,那就說明這家沒有人生活了。過去得勝堡人還把“叫你家煙堗裡不冒煙”作為咒人的惡語。
風不順時,煙堗的煙會倒灌。遇到這種情況,就要有人上房去用磚擋一下。據傳,得勝堡某家,一日灶鑊往外倒煙,老父讓笨兒子上房擋煙囪。他不知該如何擋,上房後大聲問老父:“擋哪邊?”
“風從哪邊來就擋哪邊。”
“我看不見風從哪邊來。”
“你抓把土揚起試試!”
可房頂上無土。有一把細瓦礫,抓起一扔,直上直下,遂自言自語:“噢,是上下風。”於是把磚頭平堵在了煙堗的口子上。
雁北人常說的一句話是“手藝人藝習人,吃不上就捉哄人。”如果得罪了盤炕師傅,不用怎麼坑害你,只給你炕洞子裡頭擺上一塊土坷垃,似堵非堵。三個月後,你家的灶鑊就開始倒煙,莜麵十幾分鍾還蒸不熟,因此盤炕師傅一定要招待好。
記得有一次五舅家盤炕,飯菜那個豐盛呀,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那張油光黑亮的榆木方桌上的兩個大海碗裡,白白的豆腐燉著白白的肥膘豬肉;黃愣愣的油炸糕堆滿了盤;粉條拌綠豆芽裡面還有瘦肉和豆腐絲。尤其那盆粉湯上面還飄浮著黃黃的胡油花和綠綠的蔥花,真是饞死人不償命。最恨人的是大碗裡一絲一縷的熱氣四散開來,專往我鼻子裡鑽,我就用兩隻小手直往鼻子裡緊摟。
那個師傅也太可恨了,譜大去了,全然不理我的痛苦。滋拉一口酒、叭嗒一口菜,五舅頻頻給他夾菜,他沒完沒了地滋潤啊!不過那位大俠真不白吃,炕盤得真好燒。
後來聽五舅說,得勝堡有一家人盤炕時沒招待好那位師傅。炕盤完,生起火來直倒煙,家裡煙棚霧罩地就像在燻耗子。第二天晌午又叫來重新招待,吃飽喝足後,這傢伙還在炕上睡了一覺。睡醒後,他又上了房,讓東家給他遞上一瓢涼水,往煙堗裡一灌,立馬煙氣噴湧而出。灶鑊裡的火苗舔著鍋底,歡快地叫著,鍋裡的水即刻就響了。
五舅說,其實是這傢伙在砌煙道時做了鬼,在裡面鋪了一張麻紙。水一灌進去,麻紙一破,煙氣自然通暢了。五舅由此推理舊社會的地主,他說:你不給長工吃好,他能給你好好幹?吃虧的還是東家。昔日,得勝堡的長工端坐在炕上喝酒吃肉,地主兩口子蹲在灶鑊圪嶗子吃剩飯是常事。
在得勝堡,除了蓋房壘牆、開山挖渠之外,最累的營生就數打炕了。一般土炕用個兩三年,最多四五年就要打。打炕就是清菸灰、換炕板子。農村做飯大多燒柴草,炕洞子裡積累了大量的菸灰。時間久了,煙不能順利從炕下面的煙道透過,就會影響做飯和取暖,所以必須適時把炕洞子裡的菸灰掏乾淨。炕面日久天長也會變形和開裂,煙從裂紋處冒出,所以過幾年也得拆了換新的。
打炕是個名副其實的“灰”營生,也是個苦差事。打炕前要先把傢俱行李鋪蓋苫嚴實。當你把炕板子揭開時,一股熱浪騰空而起,整個家裡充滿了煙塵,嗆得氣也喘不過來。等把炕拆完打掃乾淨,再看拆炕人,全身上下早已烏黑,好像剛從煤礦出來的下井工人。
舊炕板子是很好的肥料,人們絕不會丟掉。把舊炕板子粉碎,在下雨前灑到地裡,炕肥借雨水力量,很快就被莊稼吸收了。
關於老家的炕還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愛和溫暖蘊藏其中。火炕凝聚著親人無盡的愛,講述著家鄉最美的故事。
得勝堡是我的故鄉,我總想寫點東西給這個曾經養育過我的地方。自己雖有艾青對故土的深沉大愛,卻無沈從文清新雋永的筆端,只好細數碎念記憶的片段了。
後記:
炕是中國北方住宅裡用磚或土坯砌成,上面鋪席,下有孔道和煙囪相通,可以燒火取暖的床【kang,a heatable brick bed】。
“客則鼾睡炕上矣。”――明·魏禧《大鐵椎傳》。
隨著城市化的程序及高層商品房的開發,炕已漸漸退出了歷史舞臺。(作者 韓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