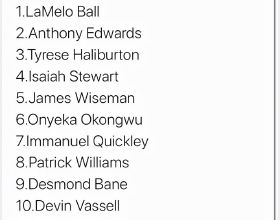《大伯朗格斯》
文/羲和餘軍
朗格斯不是大伯的真名,叫他這個名子的人也都是一些和他關係不和諧的人。大伯是父親的堂兄,但實際年齡也就比爺爺小八九歲,所以記憶中的大伯好像和爺爺那代人倒有好多的交集。
小時候,聽到大伯的話總是說他是多麼多麼的壞,說他曾經和爺爺如何如何的吵架,指著爺爺的後背罵爺爺。所以出於義憤或者自我保護,常常和大伯保持一定的距離,甚至遠遠的看到他,會自覺不自覺的躲避。後來,慢慢長大了,不再刻意和大伯保持某種距離,但對他的看法還是沒有改變,總覺得他過於刻薄尖酸,頑固且不近人情。最要命的是他經常和大表哥吵架,一度砸壞家裡的東西,不是嫌大表哥為人懶惰,就是嫌大表哥不諳世事,不會活人。應該是零二年臘月吧,那時我正上大學,因為快過年了,表妹帶著男朋友回家探親,本該是一家團聚享受天倫的好日子,但大伯就是一天到晚的拉著臉,照誰都不自在,不是指桑罵槐,就是陰陽怪氣。終於在臘月二十九的早晨,和大表哥吵開了,好在那天,表妹和她男朋友趕集不在家,還不至於讓大家太尷尬,但關於他刻薄尖酸的形象一下子得到加強,總覺得他有些沒事找事。再後來,結婚,參加工作,不可闢免的和大伯一起處理一些事務。我覺得,大伯除了要強,說話打比方時愛說“朗格斯”三個字以外,也沒有什麼毛病,為什麼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要聽到那麼多關於他的壞話呢?
大伯已經去世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好像已經模糊,但關於他的生平,在大家斷斷續續的敘述中不斷的圓潤豐富。應該說大伯也是一位苦命的人,幼年喪母,少年喪父,與繼母相依為命,先後取過兩位妻子,撫養了四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中年喪妻的厄運大伯也不期而遇,一生苦楚可想而知。記憶中大伯母出殯那天,雨下的很大,我和不到三歲的表妹爬在視窗看雨,大伯父站在廊沿上看我們,望著我們淚眼巴巴的樣子,跑到廚房給我們端了一碗豆腐,頭也不回的跑進了送喪的隊伍。大伯母去世後,大伯一個人拉扯著四個女兒和一個兒子。為了生計,常常違反當時的生產規定,偷偷的跑出去“搞副業”,要知道在當時這可是非法的。所以,大伯常常要被生產隊的幹部拉出來,作為“走資派”的典型在大會上批鬥,本來低個頭認個錯也就沒事了,但大伯天生的頑固,往死裡抵抗,就是不“認罪”。所以,常常是臺上死扛到底,私下裡又挑幹部們的理,給幹部們找麻煩,久而久之,各種關係越來越臭,以至於成為大家口中的“壞人”。
其實,大伯高興的時候也是很討人歡心的。一隻腳向前站著,一隻手搭在背上,一隻手向上微微抬起,數著指頭,堆著滿臉的憨笑,“今年的糧食比往年又多了,朗格斯四月裡的那幾場雨下到時候上了”,“朗格斯外幾年,莊稼撒時候長的這樣好”,“朗格斯王家今年麥子打了八十多袋子”。大伯最高興的莫過於說大表哥出門掙了多少錢,誰家多打了多少糧食,誰家引進了新的糧食種子,村上又多了幾位大學生,……。當然,大伯說的最多的是表妹和他的大孫子,說道他們時總有使不完的勁兒,反正是三句話裡總有兩個“朗格斯”,不知道是打比方,還是引用,說的頭頭是道的,不允許別人持一點兒不同意見。我想大伯就是喜歡跟人狡辯,而且是一根筋的狡辯,只要他高興喜歡,他絕對能說出成千上萬的好處來,當然,對於不喜歡的人事,他也絕不含糊,即便是心上已經服輸了,但嘴上就是不饒人。
大表哥剛結婚那幾年,表哥買了頭騾子替別人轉礦,跑山賣木頭,表嫂養了頭母豬,一年下兩次崽,一次十來個,雖然幸苦,但日子過的歡實。大伯見誰都笑,逢人就誇,“我的新莊子還是聽話,朗格斯這樣下來,一年存萬把錢還是不成問題的。”在後來,表妹考上了西安航空工程學校,表哥的兒子考上了哈爾濱工業大學,大伯喜上眉梢,走在路上,看著影子都笑。都說大伯為人刻薄尖酸,我覺得他除了要強,一點兒毛病都沒有。
大伯一個人操持家務慣了,家裡家外安排的井然有序,即便是院裡院外的空地,也要精心種上幾棵梨樹,來補貼家用。但是,小時候我們淘氣、嘴饞,常常在大伯不在時偷摘大伯的梨子,大伯知道是我們害的,但還是要故意的大聲叫罵幾聲,甚至當著我們的面往樹上打農藥。他一邊打藥,一邊大聲的罵,“看誰還敢偷摘我的梨子,朗格斯鹽關前兩天就把客偷蘋果的娃娃毒死了”。一時間我們都很害怕,就不敢再偷摘大伯的梨了,但後來,大伯給我們說,“朗格斯就是裝樣子嚇唬人,朗格斯有那錢賣農藥,都打到莊稼地裡了”,大伯裂開嘴爽朗的笑著,“朗格斯不那樣,也把你們莫辦法”。說實在的,我小時候也沒少吃大伯的犁,但吃的最溫馨的一次是上大學的那個寒假。那一天,大伯刻意把我領到他家,非要我和他坐一會兒,說話的時候,大伯就站起身來,從牆臺上取下八九顆碩大的八盤梨,說是家裡終於出了個大學生,說什麼也要讓我嘗一嘗他的勞動果實,大伯說:“今年梨子長的圓潤,好賣,朗格斯兩天就把七八百斤梨全部賣啦!這些是給你留著點,再不吃朗格斯就朽了。”
大伯是二零一一年去世的。臨終前,五個孩子輪流陪床,大伯走得很安詳。
202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