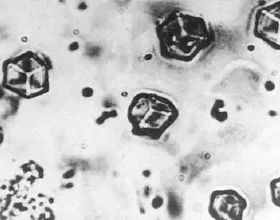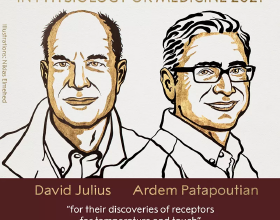北京時間10月5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學院揭曉20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兩位氣候學家——真鍋淑郎和克勞斯·哈塞爾曼,因其“對地球氣候進行物理建模,量化可變性,並可靠地預測了全球變暖”而獲獎。這是氣候學家首次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
義大利科學家喬治·帕裡西因其“在從原子到行星尺度的物理系統中無序和波動的相互作用方面的發現”同樣獲得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北京時間10月8日下午,新京報記者影片連線評選諾貝爾物理獎的機構——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華人院士陳德亮,瞭解他對今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首次頒給氣候學家的看法。
陳德亮是一位國際著名的氣候學家,2010年當選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2017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他的博士生導師是1995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保羅·克魯岑。近期,他被瑞典國王授予8號HM國王勳章,以表彰他對瑞典和國際氣候研究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陳德亮認為,雖然前兩位獲獎者的研究更偏重於氣候系統,但三位獲獎者其實都研究了一個同樣的問題——複雜系統。
外界認為此次氣候學家獲得諾獎可能為國際氣候談判帶來有利影響,陳德亮指出這確實可能存在,但國際談判政治因素完全不會影響諾獎的評判過程。對於下一次氣候學家再獲諾獎的預測,陳德亮表示,這可能會發生在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領域。
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陳德亮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新京報知道影片出品
“他們都研究了複雜系統”
新京報:大氣科學是物理學的一個應用分支,今年評審委員會把物理學獎頒給氣候學家的理由是什麼?
陳德亮:這個問題需要把第三位獲獎者和前兩位放在一起看,他們獲獎的理由最主要是都研究了一個同樣的問題——複雜系統(complex system)。
在物理學裡,有各種各樣的複雜系統,從鳥的飛行到氣候混沌,到材料科學裡的分子運動。這三位獲獎者的研究在複雜系統這一層次上都有非常巨大的貢獻。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里存在很多複雜系統,所以他們的研究有很大意義,不僅限於氣候方面。
前兩位獲獎者的研究比較偏重於氣候系統,後一位則研究材料及一些非常複雜的化學生態現象,他建造的模型可以應用於很多領域,小到分子領域,大到全球氣候。
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陳德亮。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今年兩位獲獎者在氣候變化相關領域的研究,是否足以消除氣候變化懷疑論者的質疑?
陳德亮:這要看氣候變化懷疑論者是什麼樣的態度。很多人不從科學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那拿出多少科學研究,他們也不會相信。但如果有人是從科學角度質疑氣候變化,那這次的諾貝爾獎會給他們一個資訊,就是科學界是很認同氣候變化研究的。
第二位獲獎者哈塞爾曼的研究就解答了人類活動是不是在影響全球變暖的問題。他發展了一個新的模型和方法,利用“指紋”概念,將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的影響痕跡與自然變化的影響痕跡區分開,這樣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人類活動確實影響了氣候變化。
“諾獎評判沒有任何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政治考量”
新京報:下個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即將舉行。此次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氣候學家,會不會進一步加強世界各國對氣候變化的重視?
陳德亮:我想會有一定影響,目前在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化學獎和物理學獎都頒給過氣候學家,表明人類活動確實在影響我們生存的地球環境。
但此次獲獎的影響可能並沒有那麼大,兩位獲獎氣候學家的研究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展的,已經過去了五六十年。目前科學界作出更大貢獻、有更大影響的應該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我也是IPCC報告的領銜作者之一。
IPCC近期釋出了第六次評估報告,作為更權威的機構,它帶來的國際政治壓力會更直接,這一系列氣候報告的影響會更大。
今年兩位獲獎者的研究對IPCC系列報告的貢獻也是非常巨大的,他們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奠定基礎的作用,具有里程碑意義。
新京報:你認為,將諾貝爾獎頒給氣候學家背後,是否有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方面的政治考量?
陳德亮:這裡面不會有任何政治性考量。諾貝爾獎被外界這麼看重,是因為多年來一直堅持很嚴格的科學原則,從科學角度來評判,不會受任何公益因素影響。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方面,氣候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確實會帶來一定影響,但這絕對不是他們獲獎的原因。
氣候變化相關研究第四次獲諾獎表彰
新京報:在氣候變化相關領域,此前在1995年、2007年和2018年,分別有諾貝爾化學獎、和平獎和經濟學獎頒給氣候變化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或組織。今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也首次頒給氣候學家,這意味著什麼?
陳德亮:我以前的導師克魯岑在1995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因為他對大氣中光化學反應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特別關注汙染物排放可能導致平流層中保護性臭氧層耗竭的風險。
今年兩位獲獎的氣候學家指出,二氧化碳排放會加劇全球變暖。我認為克魯岑的研究和今年兩位獲獎的氣候學家的研究是在一條線上的,它們表明了一個同樣的資訊,就是人類活動已經成為影響地球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新京報:你此前曾提到,克魯岑先生曾開玩笑地說很遺憾沒有諾貝爾氣象獎。你覺得克魯岑先生如果還在世的話,是不是不會再有這個遺憾了?
陳德亮:如果克魯岑先生還在世的話,肯定會很開心,因為我們地球科學的研究人員得到了化學獎,也得到了物理學獎,證明我們的工作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他說這句開玩笑的話是在1990年的一天,我和他當時在奧地利的聖奧斯瓦爾德教堂,瞻仰諾貝爾獎獲得者歐文·施羅丁格的墓地。
在那個小村莊裡,他說,得諾貝爾獎是很不簡單的,今天下午我們就不工作了,喝啤酒放鬆一下,反正我們也得不了諾貝爾獎。雖然這是他一句開玩笑的話,但在當時,做大氣研究的學者確實沒有得過諾貝爾獎。
“下一次氣候學家可能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新京報:在今年兩位獲獎氣候學家的研究領域裡,你如何評價中國氣候學界的研究貢獻?中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與諾貝爾獎的差距在哪裡?
陳德亮:中國的現代科學起步比較晚,在最近幾十年我們才真正有了很大發展。但在短短几十年裡,我們的進步非常快、非常大。可以看到,目前IPCC報告裡中國作者的人數不少,所做工作的質量也很高。
我對中國科學界未來的發展很有信心。特別是在目前的氣象科學領域,我認為我們中國科學家還是站在前沿。
新京報:能否預測一下,下一次氣候學家再獲得諾貝爾獎會是多少年以後?
陳德亮:既然在諾貝爾獎的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學獎和化學獎都頒給過氣候學家,那我想接下來就是生理學或醫學獎了。
我個人比較看重系統性研究,目前空氣汙染每年會導致數百萬人死亡,未來氣候學家能否在大的框架下研究氣候變化和人類之間的互動,取得大的研究突破,這是我所期待的。
目前還沒有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是與氣候變化研究相關的,20年後,我想應該會有與此相關的有分量的氣候變化研究。
新京報:大氣科學是地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評價今年兩位獲獎者所代表的研究方向在地球科學中的地位?
陳德亮:目前地球科學已經發展出一個“地球系統科學”的概念,今年兩位氣候學家獲獎的一個很重要原因也是他們是在複雜系統的框架下開展地球系統的研究。
地球科學系統包括五大圈——大氣圈、水圈、冰凍圈和岩石圈以及生物圈,最新理論認為人類活動對地球有很大影響,應該再加入一個新的“人類圈”。我認為在將來的地球科學裡,將會探究“人類圈”和現有五大圈之間的相互作用。
今年獲獎的氣候學家真鍋淑郎在被記者問到將來的研究方向是什麼時,他回答說是生物圈。五大圈中的生物圈和大氣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很重要的研究問題,在我看來,從地球系統科學來看,人類活動和大氣之間的相互作用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值得研究的問題,對將來的科學發展十分重要。
“我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表現有點失望”
新京報:近幾年,我們感受到全球變暖似乎帶來了更多、更嚴重的極端天氣事件。今年,我國和全球多國都因極端降雨天氣遭遇嚴重洪災,熱浪、野火也在全球多國頻繁出現。你對目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表現有何看法?
陳德亮:我覺得有點失望。這個問題不是科學範疇了,而我作為一個公民,我認為目前的應對速度還不夠快。
這裡面有很多原因。一些發達國家儘管有良好的科技和經濟發展,但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仍出現一些特別不科學的表態。另外,減少碳排放也和經濟發展有關,全世界有很多國家正處於發展階段,也有一些國家還沒來得及發展,所以平衡這裡面的複雜關係、達到真正的減排很不容易。
IPCC近期釋出的最新報告中給出了不同減排背景下可能出現的5類情景,而我認為全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是向著較壞的情景在前進,我們可能很難達到《巴黎協定》設定的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1.5℃或2℃之內的目標。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知道這個問題很嚴重,還是必須要保持樂觀。
新京報:我們還應做哪些工作來更好地應對全球變暖所帶來的氣候危機?
陳德亮:有害氣體排放問題不僅影響氣候,還會影響人體健康,研究顯示全世界一年有幾百萬人死於空氣汙染。所以我們需要認真看待這些問題,並在個人層面做一些事,減少自身行為對環境的破壞。
應對全球變暖,就必須要減排,這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一方面要減少需求,改變不太環保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例如減少一次性包裝的使用,多使用公共交通,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減少煤炭資源的使用。
新京報:氣候變化科學對於普通公眾來說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從科學普及的角度,你有何建議?
陳德亮:新聞界和公眾都需要更多氣候變化相關的知識和資訊。在這方面,我要對我們科學界自身做一些批評,我們在這方面做的工作還很少。
我們只關在自己的小屋子裡做研究,和公眾沒有太多接觸。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學習做得更好的一些國家,那裡的大學教授除了授課和做研究外,還有和公眾交流的任務,而且這是寫在工作合同裡的。
氣候變化是關係到民生、生態文明和人類未來發展的重要問題,我們科學家需要深思,如何與公眾溝通,提高大家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瞭解。
新京報記者 向晨雨 劉婧瑜
編輯 張磊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