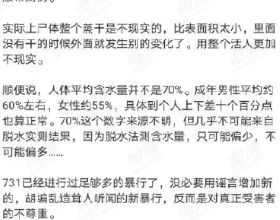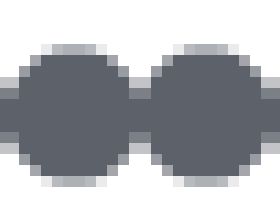1921年,魯迅的工作重心在翻譯。他翻譯了若干篇日本現代小說,並從德文轉譯了俄國、芬蘭、保加利亞等國的文學作品。魯迅翻譯的兩位日本作家森鷗外、芥川龍之介,與社會主義都頗有淵源,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魯迅在翻譯和創作中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關注,及與日本作家的共鳴。
魯迅與森鷗外
1921年4月21—24日,魯迅翻譯的《沉默之塔》發表於《晨報副刊》。這是日本文豪森鷗外的作品,原發表於1910年11月《三田文學》;1911年10月,作為序言刊載於生田長江翻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卷首。魯迅與森鷗外在經歷上存在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學醫出身;都通漢文、日文、德文;都熱心於翻譯與文學創作,有過作品被禁止出版的遭遇;都有在政府機構任職的經歷等。森鷗外政治上偏於保守,魯迅對他的關注不如對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以及白樺派作家。
森鷗外
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開始於日俄戰爭之後,明治政府對之採取了壓制的態度。1909年5月,幸德秋水等人創刊的《自由思想》遭禁,社會主義者無法合法活動,計劃暗殺天皇;計劃敗露後,相關的24人被以大逆罪起訴。次年1月,幸德秋水等12人被處決。森鷗外的《沉默之塔》正發表於預審判決之後。幸德秋水是日文版《共產黨宣言》的譯者之一。這一譯本也是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所依據的主要底本(同時參照了英譯本)。
1910年9月16日至10月1日,《東京朝日新聞》連載《危險的洋書》,其匿名作者對於新思想、新文藝極盡謾罵之能事。其中第五篇是《危險的洋書(5)春情發動之小說及其介紹者》,痛罵將德國劇作家弗蘭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1864—1918)的《春之覺醒》譯介到日本的森鷗外。可見,森鷗外的文學與翻譯也被視為“危險”之物。
森鷗外寫作《沉默之塔》,目的在於諷喻日本政府對於新思潮的壓制。作品中14次出現“危險的書籍”“危險的洋書”等詞語,列舉了約20名西方思想家、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包括聖西蒙、馬克思、巴枯寧、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莫泊桑、梅特林克、易卜生、蕭伯納、魏德金等,幾乎涵蓋了當時日本流行的西方思想。
1920年8月,魯迅翻譯了尼采的《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他有可能是在翻譯時看過生田長江的日譯本,從而接觸到森鷗外的《沉默之塔》。次年1月3日,魯迅收到胡適的來信。這封信是胡適寫給陳獨秀,後交給魯迅等人傳閱並徵求意見。胡適認為《新青年》雜誌“色彩過於鮮明”,主張“不談政治”。魯迅在回信中明確答覆:“至於發表新宣言說明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眾所周知,《新青年》對於推動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普及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胡適主張“不談政治”,而魯迅回覆“以為不必”,表明了他對於新思想的擁護。
魯迅的創作與《沉默之塔》也存在諸多共鳴之處。首先,“沉默”是魯迅作品中十分重要的意象。“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1934年,魯迅的多部作品被禁,文章也難以刊載。他因此寫了一首七絕,末句“於無聲處聽驚雷”,恰如其分地體現出他不甘於沉默的態度。
《沉默之塔》透過“沉默”“黑暗”“死亡”等一系列意象,建構近代日本新思想受壓制的現實。魯迅則藉助“吶喊”“火”“新生”等意象,顯示出摧毀“沉默”與舊秩序的可能。在《吶喊·自序》中,魯迅創作了著名的意象“鐵屋子”。“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不妨說,魯迅將“沉默之塔”的意象置換成“鐵屋子”,保留了“禁錮”“死亡”等資訊,進而提示了打破“沉默”、摧毀“鐵屋子”的可能性。
魯迅與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
魯迅翻譯的另一個作家——芥川龍之介,於1921年3月30日抵達上海,並於4月下旬拜訪了李人傑,即李漢俊。李人傑(1890—1927),原名李書詩,號漢俊。根據中共一大紀念館的東京大學就學證書影印件,學籍姓名是“李人傑”。李漢俊1904年留學日本。其後在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期間,深受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影響。1918年回國後在上海從事寫作、翻譯工作,傳播新文化與馬克思主義。1920年,與陳獨秀等人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後組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李漢俊之兄李書城的寓所召開。芥川訪問李漢俊時,正值李漢俊、陳獨秀等人組織籌劃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他在遊記中描述的地點即為中共一大會址。
芥川寫道:“就信仰而言,乃社會主義者,上海‘少年中國’之代表人物。”芥川記錄了李漢俊對於時事的點評,從中不難發現李漢俊推動“社會革命”的抱負,以及透過政治宣傳啟發民智的雄心。1920年,陳獨秀、李漢俊主持的《星期評論》邀請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並由戴季陶提供日譯本,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英譯本,提供給陳望道作為翻譯的底本。譯稿完成後,經李漢俊校閱、陳獨秀審定,於1920年8月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
在芥川中國旅行期間,魯迅翻譯了芥川的兩篇短篇名作。1921年5月11—13日,《鼻子》發表於《晨報副刊》;6月14—17日,《羅生門》發表於《晨報副刊》。《順天時報》1921年6月14日第7版刊載了一則題為《日前到京之芥川氏》的簡短啟事,魯迅翻譯的《羅生門》正是在芥川抵達北京後開始連載。某種意義上,這也是魯迅獨特的歡迎方式。
芥川在北京見了胡適、辜鴻銘,沒有與魯迅見面。歸國後,他在隨筆《新藝術家眼中的中國印象》(1921)中寫道:“周作人氏因病在西山靜養,最終沒能見到。”可見,他想見的是魯迅的弟弟周作人。而在《日本小說的中譯》(1925)裡,芥川高度評價了周氏兄弟翻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以我的作品翻譯來看,譯得相當準確。而且地名、官名、道具名稱等等,都妥當地加了註解。”從文章中的表述來看,芥川在北京想見周作人,極可能是誤以為周作人是自己作品的譯者。周作人撰寫的《現代日本小說集》的序言中,存在一處錯誤:“這裡邊夏目森有島江口菊池芥川等五人的作品,是魯迅君翻譯,其餘是我所譯的。”文中列舉的日本作家分別是夏目漱石、森鷗外、有島武郎、江口渙、菊池寬、芥川龍之介,總共應為六人,而非五人。芥川有可能依據人數進行判斷,把自己作品的翻譯歸在了周作人名下。
芥川的《鼻子》講述一個地位甚高的老和尚,因為長了異於常人的長鼻子,始終為之苦惱。弟子從來自震旦(中國)的僧侶處得到偏方,使老和尚的鼻子變短了。然而周圍的人習慣了老和尚的長鼻子,見到變短的鼻子卻更覺得可笑。這又一次傷害了老和尚的自尊心。一天鼻子又恢復了原來的長度,老和尚如釋重負,“既這樣,一定再沒有人笑了。”(魯迅譯)
1920年10月10日,魯迅發表了小說《頭髮的故事》。作品以雙十節為背景,借N先生之口,講述中國人因頭髮而吃的苦頭。“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只因為這不痛不癢的頭髮而吃苦,受難,滅亡。”然後,N先生講述了自己留學時剪去辮子,回到中國不得已裝上假辮子,反而更受矚目,索性廢了假辮子,又被罵作假洋鬼子。“我最得意的是自從第一個雙十節以後,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罵了。”頭髮是身體的一部分,辮子的去留是改造身體的行為,也是如實反映旁觀者視線的鏡子。從《頭髮的故事》的創作到《鼻子》的翻譯,存在這樣一條潛在的邏輯脈絡:魯迅從自身以及同時代中國人的經歷出發,發現《鼻子》中存在視覺性、身體改造的主題,因而產生了共鳴。
魯迅翻譯《鼻子》的年末,12月4日,小說《阿Q正傳》開始在《晨報副刊》連載,至次年2月2日。《阿Q正傳》延續了《頭髮的故事》中關於辮子的敘事,塑造了阿Q這一經典形象。英文“Queue”一詞,發音與“Q”相同,意為“辮子”。在小說的第二章《優勝記略》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阿Q“先前闊”,見識高,而且“真能做”,本來幾乎是一個“完人”了,但可惜他體質上還有一些缺點。最惱人的是在他頭皮上,頗有幾處不知於何時的癩瘡疤。這雖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為不足貴的,因為他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
《鼻子》開篇就寫了老和尚異於常人的長鼻子。“一說起禪智內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沒一個不知道的。”長鼻子與癩瘡疤,都是身體的缺陷:
五十多歲的內供是從還做沙彌的往昔以來,一直到升了內道場供奉的現在為止,心底裡始終苦著這鼻子。這也不單因為自己是應該一心渴仰著將來的淨土的和尚,於鼻子的煩惱,不很相宜;其實倒在不願意有人知道他介意於鼻子的事。內供在平時的談話裡,也最怕說出鼻子這一句話來。
不難發現,不僅長鼻子與癩瘡疤因為缺陷而成為被觀看的物件,兩位主人公忌諱聽到與此相關的詞語,也顯示出相同的心理反應。在接下來的文章裡,芥川寫道:“內供之所以為苦者,其實卻在乎因這鼻子而傷了自尊心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自尊心”這個詞。芥川的《鼻子》改寫自平安時代的《今昔物語》中《池尾禪珍內供之鼻》及《宇治拾遺物語》中的《長鼻僧之事》。然而,“自尊心”是近代譯介到東亞的心理學術語。同樣,在魯迅筆下,“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裡”,兩位作家從主人公的“身體”切入,進而挖掘其“心理”的問題。《阿Q正傳》中“辮子”的長短變化與《頭髮的故事》《藤野先生》(1926)、《病後雜談之餘》(1935)諸篇中的記述大致相近,不再贅述。魯迅在《病後雜談之餘》寫到,自己除去假辮子後走在街上時想著,“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這麼受苦”,在魯迅看來,辮子與鼻子同屬被觀看的物件。
最後講一個小插曲:芥川在北京時拜訪了辜鴻銘。辛亥革命之後,辜鴻銘獨立特行地繼續留著長辮子。芥川在遊記中寫道:“他見我穿了中式長衫,評價道:‘不穿洋服令人佩服。唯一遺憾的是沒有辮子。’”因為沒有辮子而成為被觀看、被評價的物件,是芥川始料未及的。不知芥川在那時,有沒有想到自己在《鼻子》中所提示的視覺性問題。
作者:鄒波(復旦大學外文學院)
編輯:陳韶旭
責任編輯:任思蘊
來源:文匯學人
*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