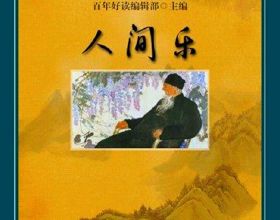上海大學文學院 王培軍
1988年3月18日,《新民晚報》“夜光杯”刊載了一篇《也來“聒噪幾句”》,是訂正電視劇《西遊記》錯誤的,署名“中樞”,那是錢鍾書先生的化名。在我國四大名著中,錢先生最喜歡的是《西遊記》,所以,電視劇的《西遊記》為他“愛看的節目”,也就可以理解。這也表現了他的頑童式的淘氣。這篇訂誤之文,不過四百二十二個字(據吳泰昌《我認識的錢鍾書》131頁所計,我沒有重數),是真的“豆腐乾式”,但出人意外的,影響卻相當深遠,三十年過去了,還時不時被人提起。其中的第二段說:
第十五集《鬥法降三怪》裡孫行者把“社稷襖”和“地理裙”變成“一口鐘”。“一口鐘”就是長外衣或斗篷,《西遊記》本書三十六回也提起寶林寺有些和尚“穿著一口鐘的直裰”;把貴重衣裙變作破爛衣服,順理成章。電視劇中卻把它變成一座銅鐘,似乎編劇者對詞義缺乏理解。
電視劇把“一口鐘”誤作“一座銅鐘”,是不必多怪的,因為給《西遊記》作注的學者,在“一口鐘”的底下,並未下注。拍電視劇的人,“疏於學問”,自難免望文生義。而大學問家的錢先生,訂人之誤,卻也沒能“毫髮無遺憾”。追本溯源,錢先生的這一節,是必本於工具書的。1979年9月版的《辭海》:
一口鐘,也叫“一裹圓”。即斗篷。一種長而無袖、左右不開衩的外衣。《西遊記》第四十六回:“櫃裡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上冊,第3頁)
1979年7月版的《辭源》:
一口鐘,指一種無袖不開衩的長外衣。以形如鍾覆,故名。又叫鬥蓬、蓮蓬衣、一裹圓。明方以智《通雅》三六《衣服》:“周弘正著繡假鍾,蓋今之一口鐘也。凡衣掖下安襬,襞積殺縫,兩後裾加之。世有取暖者,或取冰紗映素者,皆略去安襬之上襞,直令四圍衣邊與後裾之縫相連,如鍾然。”《西遊記》三六:“有的披了袈裟;有的著了偏衫;無的穿著個一口鐘直裰。”(第一冊,第8頁)
在整部《西遊記》中,提及“一口鐘”凡三處,錢先生只提及兩處,卻都已見引於《辭源》《辭海》。另外一處,則是作“一口中”,見第二十五回《鎮元仙趕捉取經僧、孫行者大鬧五莊觀》,行者對八戒說:“這先生好意思,拿出布來與我們做中袖哩!——減省些兒,做個一口中罷了。”黃肅秋注之雲:
僧衣。形狀如鍾,上窄下寬,所以叫一口鐘。中與鍾同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印本,326頁)
假如拍電視的人通讀了《西遊記》,並且記性不壞,那個“一座銅鐘”的錯,就可以避免了。假如錢先生作文時,想得起這一回,以他的行文風格,一定還要再加幾句,“以博其趣”。“一口中”在明代小說中,也還出現過,如《警世通言》第三十三卷《喬彥傑一妾破家》程五娘說的:“我丈夫頭戴萬字頭巾,身穿著青絹一口中。”嚴敦易注:
古時衣服有外(衫,袍)內(中單,中衣)的分別,這裡所云“一口中”,是說只有一件內外通用的短衫,顯示出他的窮苦。青絹是明代普通人著的衣服的顏色和質料。現在人稱斗篷為“一口鐘”,和這“一口中”有分別,並不是一樣的服裝。(人民文學出版社,528頁)
此注之解“中”字,不免迂曲了,在俗小說中,字音同而字形異寫,其實是常有的事。黃肅秋說“中”即“鍾”,是正確的。《警世通言》的這一卷故事,在馬隅卿發現的《雨窗欹枕集》中為《錯認屍》,其文字略同:“程五娘道:‘我丈夫頭戴萬字頭巾,身穿著青絹一口中,一月前說來皮市裡買皮。’”程毅中《校注》本改“中”為“鍾”雲:“‘一口鐘’即斗篷,無袖的外衣,形似銅鐘。”(見中華書局本《清平山堂話本校注》349、362頁)解釋不算太錯,但改字未免太勇。其實,就是《辭源》所引方以智《通雅》“周弘正著繡假鍾”,“鍾”字也是本作“種”,見於《南史·周弘正傳》: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眾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中華書局本,第三冊897-898頁;《陳書·周弘正傳》不載此事)
《辭源》引《通雅》的一節,見今人編《方以智全書》第六冊56頁,前面刪去一句:“假鍾,今之一口鐘也。”“假種”之作“假鍾”,是方以智的改字。周弘正是周顒之孫,裴松之的曾孫裴子野之婿,為人“醜而不陋,吃而能談”,在“著繡假種”之前,另有一事:“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禈,錦絞髻,踞門而聽,眾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也可見其為人。至於方以智對“假鍾”的描述,文字古奧,讀了很不易懂,如“掖下安襬,襞積殺縫”,“掖”是“逢掖之衣”的“掖”,也就是“腋”之古字,“襬”應是指裙,《方言》:“裙,自關而東或謂之襬。”“襞積”是指褶襉,“殺縫”是上銳下廣之縫。既雲“掖下安襬”,則必有袖,有袖就不是斗篷,斗篷不穿袖,是無所謂“掖下”的。《辭源》、《辭海》的那個說法,不知有什麼根據。
就是看錢先生及《辭源》所引《西遊記》第三十六回的“穿著個一口鐘的直裰”(按原文無“的”字,“的”字為錢先生所加),也不能說是鬥蓬,而應該是直裰。“一口鐘的直裰”,只可理解為那是叫做“一口鐘”的那種“直裰”,也就是說,“一口鐘”是“直裰”之一種,而如果“一口鐘”是斗篷,那就等於說穿著“斗篷的直裰”,斗篷是斗篷,直裰是直裰,本是截然二物,如何可作定語?就算標點作“穿著個一口鐘、直裰”,看作兩種衣服,也是不能通的,——僧人不以斗篷為常服,一般而言,他們所穿著的,無非袈裟、偏衫及直裰等(見白化文《漢化佛教法器與服飾》137-143頁及《石窟寺研究》第二輯王振國《偏衫與直裰》)。另據第二十五回說的:“不做中袖,減省些做‘一口中’”,中袖為半袖,那麼“一口鐘”的裁製,要更簡單些。大概直裰而無袖、不開衩,便為“一口鐘”。至少在《西遊記》的本文中,是這樣子的。
晚方以智一百年的胡文英,有一部《吳下方言考》,其書卷一有“■(音中)”條雲:
許氏《說文》:“■,㡓也。”案:■,用成幅布縫如囊,無兩袴,取蔽前後,大如犢鼻,直如煙衝是也。吳中謂不穿袴曰“一口■”。(見《吳下方言考校議》,第1頁,參看下圖)

“一口■”也就是“一口鐘”。胡氏是乾嘉時的樸學家,其好用古字、奇字,可以理解。“成幅布縫如囊”“無兩袴”“直如煙衝”,“煙衝”便是“煙囪”,這比方以智說的,清楚得多了。“成幅布縫如囊”,也正可以與《西遊記》第二十五回行者的那句,相為發明。“縫之如囊”,是決不能為斗篷的。又近人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三五《服飾》,謂“一口鐘”即“一裹圓袍子”,並引西清《黑龍江外紀》雲:
官員公服,亦用一口鐘,朔望間以襲補褂,惟蟒袍終不用一口鐘,滿洲謂之“呼呼巴”,無開偧之袍也,亦名“一裹圓”。今雲“一裹圓袍子”是也。(中華書局本,586頁)
西清為滿族學者,稍後於胡氏。既雲“一裹圓袍子”,“無開偧之袍”,又云“蟒袍不用一口鐘”,則“一口鐘”之為物,為袍子的一種樣式,當可無疑。“開偧”之偧,“音吒,張也”(見《康熙字典》),換言之,也就是“開衩”,因為一般長袍左右側有衩,故云。“一口鐘”既為袍之屬,則決非鬥蓬又可知。
也許有人要問,既說“一口鐘”是直裰,又說它是袍,不是矛盾了嗎?其實也並不。袍在周時本內衣,與襦無異,漢代始著於外,至唐宋為朝服,是士大夫所著的。《黑龍江外紀》說“官員公服,亦用一口鐘”,“一口鐘”既然是袍,當然就可作“官員公服”。而直裰則稍有別,直裰是道者之服。據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四雲:
古人戴冠,上衣下裳,衣則直領而寬袖,裳則裙。秦漢始用今道士之服,蓋張天師漢人,道家祖之。周武帝始易為袍,上領、下襴、穿袖,幞頭,穿靴,取便武事。五代以來,幞頭則長其腳,袍則寬其袖,今之公服是也。或雲古之中衣即今僧寺行者直裰,亦古逢掖之衣。(中華書局本,60頁)
可見僧人所著的是直裰,與士夫所著之袍,是有所區別的。但若究其形制,則“直裰,亦古逢掖之衣”,與古儒者之服,亦深有淵源。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論衣冠異制”雲:
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皂,下加襴,前系二長帶,隨按即隋字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為直掇。(《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云:“逢,大也。大掖大袂,禪按當作襌衣也。”“逢掖”與“馮翼”音相近。)(人民美術出版社,13-14頁)
“逢掖之衣”,就是古之所謂“深衣”,是儒者所服的。其實也還是袍服。直裰雖為袍,但一般為道者服,與士夫的朝服、公服有別。俞樾《茶香室四鈔》卷二十四“褐即直掇”雲:
宋程大昌《演繁露》雲:《張良傳》有“老父衣褐”,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太平御覽》有《仙公按公應作翁請問經》,其文曰:“太極真人曰:‘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裾通冒其外衣也。今世衣直掇為道服者,必本諸此。又《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裾,不著褐。”則是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襲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按鄭《箋》以褐為毛布,《孟子》雲“許子衣褐”,即毛布是也。張良所遇老父衣褐,疑亦謂此,是以《史記》無注,師古注《漢書》乃有此解,則是褐有二說矣。至上衣下裳,古之定製,婦人連衣裳不異色,見《周禮·內司服》注。今則男女之衣適與古反。觀晉時羊欣白練裙,則晉時猶上衣而下裳。疑後來崇尚老莊,故多著道袍,至今循之,士大夫皆衣褐矣。(中華書局本,第四冊1866-1867頁)
按照俞樾的意見,“褐”即“道袍”,也就是“直掇”(即直裰),後來計程車大夫,都著“直掇”,也就是以道袍為服。所以袍之與直裰,其制雖有異,本質卻是無大別的。“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是古之所謂“上衣下裳”,不是“道家服”。這種“上衣下裳”,在宋人是所謂的“野服”,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二“野服”條雲: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雲:“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嘆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餘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中華書局本,146頁)
這一種退居時的“野服”,也就是蘇軾過金陵時,見王安石說的“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的“野服”(見朱弁《曲洧舊聞》卷五),與我們今天的“上衣下褲”,精神是一致的。宋人以束帶為敬,不束則為不敬,《老學庵筆記》所謂“散腰則謂之不敬”,“散腰”即不束帶,所以“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直裰與袍,皆是連上衣下裳為一體,所以皆可作“一口鐘”,這是沒有問題的。
直裰可以寫作“直掇”,《通俗編》卷二十六《服飾》“直掇”條雲:
按《說文》:“■,衣躬縫也。”《集韻》雲“或作■■”,又《周禮疏》:“中央為督,所以督率兩旁。”《莊子·養生主》“緣督以為經”,《音義》亦云“中也”,《六書故》雲:“人身督脈,當身之中,貫徹上下,故衣縫當背之中達上下者,亦謂之督。”據此,則“直掇”字本當作“■”,而“督”亦可借用。若“裰”則補破之義,不應連“直”字為名,作“掇”則更無義矣。(中華書局本,下冊351頁,參看下圖)
這與胡文英寫“一口鐘”作“一口■”,同其一揆,都是學者的好古癖。其說是否確當,姑且勿論,但“直掇”之即“直裰”,“鬥蓬”之即“斗篷”,“一口中”之即“一口鐘”,是無疑義的。至於李百川《綠野仙蹤》第五十三回《蕭麻子想錢賣冊頁、擋人碑裝醉鬧花房》寫的:
見一大漢子將簾子撾起,踉踉蹌蹌的顛將入來:頭戴紫絨氈帽,外披一口鐘青布哆羅,內穿著藍布大襖,腰裡繫著一條搭包;入了門,將屁股一歪,就坐在炕沿邊上。(北京大學出版社本,下冊42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點校本為八十回本,無此節。“哆羅”為毛織呢料,《紅樓夢》第四十九回李紈穿著“青哆羅呢對襟褂子”,亦是此物。)
或者俞萬春《蕩寇志》第一百十三回《白軍師巧造奔雷車、雲統制兵敗野雲渡》的:
白瓦爾罕到內帳相見,眾人看那人中等身材,粉紅色麵皮,深目高鼻,碧睛黃髮,戴一頂桶子樣淺邊帽,身披一領大紅小呢一口鐘,像煞西洋畫上的鬼子。(人民文學出版社本,下冊631頁)
以及為徐一士激賞的晚清小說《負曝閒談》第二十九回《坐華筵像姑獻狐媚、入賭局狎友聽雞鳴》的:
順林叫天喜到裡面問師孃要件狐皮一口鐘來,替汪二爺蓋著,回頭省得涼了他。(上海古籍出版社本,146頁)
都可能另是一物,另有所指,不得與《西遊記》第四十六回的並論。物之名隨時而變,隨地而異,甚至“名同而實異”,“名異而實同”,在在而有,所以清人小說中的“一口鐘”,與明人小說中的是否為一事,也就很難說了。
與方以智說的“假鍾(種)”很相近的另有一個晉南北朝的詞,叫做“徵鍾”,亦為一種衣服。不妨順便一提。其物見於《宋書·五行志二》:“桓玄時,民謠語云:‘徵鍾落地桓迸走。’徵鍾,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稱。玄自下居上,猶徵鍾之廁歌謠,下體之詠民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驗明矣。”(中華書局本,第三冊919頁)讀書不下於北皖人方以智博雜的南皖人俞正燮,在《癸巳類稿》卷七“衷邾椶反切文義”條引之並加按雲:
其解迂曲。《晉書·五行志》“詩妖”及《通考·物異考》不載其文,蓋由義晦難明刪之。今案其文當作“徵鍾落地丸迸走”。解雲:徵鍾者,衷衣之衷兩合音也;徵鍾落地者,徵鍾之廁,如《魏書·於什門傳》言“披袴後襠”,褫衷衣落下也;“丸迸走”者,下體之稱也。(《俞正燮全集》第一冊,330頁;按,“‘披袴後襠’,褫衷衣落下也”句,原誤標作“‘披袴後襠褫衷衣落下’也”,遼寧教育出版社本誤同)
其實作“披袴後襠”的是《北史》,《魏書》作“被”字,“披”“被”雖可通,但畢竟一字之差,錯了出處。《漢語大詞典》第三冊933頁“徵鍾”條,即據俞氏書解之,雲:“衷衣,貼身小褲。”也是錯的,因為衷衣並不指褲,並且那時的褲,也還只是脛衣,而不與襠連,與今之縫襠褲大別。這是不明古制,想當然的解釋。俞氏所云“褫衷衣落下”,是指古人如廁大遺,必定脫衣之意。《世說新語》中王大將軍在石崇家如廁,當著諸侍婢,脫換衣服,神色傲然,即是其事。至於“假鍾”一詞,實出方以智之書,嚴格說來,與《南史》的“假種”並不能等同,釋之為“一口鐘”,是否真的可取?而《漢語大詞典》第一冊1583頁“假鍾”條雲:“即一口鐘。”不過據《通雅》而已,別無他證。這些都是可議的。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