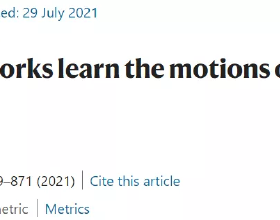來源:新甘肅
【校園文學】
圖書館的月亮
吳奕昕
由於母親在大學的圖書館工作,我小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每當學校放了學,家裡又沒有人,便一個人跑到圖書館裡來尋母親。母親在前臺斂著聲為學生借書,我便獨自在林立的書架後坐著。
晴日裡,總有金龜子從窗外撞進閱覽室來,金屬色的脊背朝下翻著,四條短腿蹬向空中。陽光從明亮的玻璃外流瀉而下,在地上晃盪出明亮的光斑;我便在陽光下和那些小蟲戲耍,一玩便是半日。玩累了,便將它們又送還到窗外的廣袤天地中去。如有幾日沒來圖書館,窗沿上必然會多出幾具金龜子的屍體,明顯是無法翻身而力竭死去的。那些絢爛的小“寶石”失卻了耀目的光澤,僵硬地臥在窗沿,如小小的沉寂的石粒。我遠遠地望著那些小生物死氣沉沉的軀體,頭一次在內心感到了恐懼:金龜子的死亡,讓我尚且幼小的心靈生髮出憐惜之情。
南方的小城,晴天終是少見的,雨霧的陰影便常常籠罩到圖書館的屋簷上來。雨日的圖書館,彷彿和晴天裡有了些許不同。雨水從天穹墜落,耳邊便迴響起嘈雜的炒豆似的樂聲。屋裡的光線較平日黯淡,書架間於是投下大片的陰影,對孩童來說,似乎顯得有點怕人。圖書館裡存放的多是舊書,在雨天,便滲出淡淡的氣味來。
一次,我對母親說:“書發臭了!”母親回頭瞪我道:“那是書香!”當時以孩童的眼光判斷,終究是察覺不出那獨特的氣味如何可以被稱為香氣,只覺得屋內的氣氛神秘得迷人。書架間似乎也瀰漫著極淡的雨氣一般,借閱者的腳步聲迴盪在這氤氳的潮氣中,便顯得比平日輕微些,常常是隻聞其聲不見其人。恍惚中,便覺得行走的不應當是人類,而是書頁間飛騰的魂靈——那時我認為,書中的“顏如玉”,理應是精怪一般的存在,自會在有心人面前顯示出如花似玉的面目來。於是,便自然而然地將那行走在書架間的陌生人認作是那筆墨化身的精靈了。
母親每日總要等到閉館時才會離開。我坐在視窗,母親熄了燈,閱覽室內便徹底暗下來。滿天的月色一瞬間湧進屋裡,頃刻便潑下白花花的一地碎銀。我獨自坐在月色下,當時的心情已經不記得了,或許想過一些東西,又或許什麼也沒想。書架的高塔在背後聳立成黑黢黢的一大片森林,月光便於塔間流照出一道道銀白的清光。
我望著月亮,心中很沉醉似的,為了配合這皎美明淨的造物,便有意在月下念起背過的詩句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可是霜是什麼呢?南方是見不到霜的。“霜”這個字念起來倒是清清爽爽的,明快而好聽。而故鄉在哪裡呢?故鄉就在腳下。我不認得霜,也不需要懷念故鄉。月亮卻只是像李白千年前曾遙望過的那般,潔白而冰涼,獨自掛在高遠的夜空上。
後來讀了初中,搬了家,圖書館的記憶便在腦海中模糊了。再後來,獨自一人於秋日北上,在某個落著寒雨的夜裡,第一次走進了生命中的第二座圖書館。閱覽室裡安安靜靜的,紙頁的翻動聲像是某些熟悉的魂靈。我在窗下一個人坐著,聽著窗外淅瀝的雨聲,望見山脈的輪廓在遠方寂然地橫臥;圖書館像是天地之間的一顆沙礫——一顆安睡在萬里群山和瓢潑雨幕間的沙礫,大度地懷抱著無數人無法忘卻的歲月,沉默地孕育著無數人期待的明天。
等閉館時走出門來,才發覺不知何時雨已經停了,天空被雨洗得澄澈,一輪泛黃的滿月忽然從雲層上掙躍出來,清澈如水的白光將遠山的輪廓照得通透明亮。我提著電腦包在門口站定,掏出手機來想要拍那天穹上的月亮,卻又不期然想起那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霜終究是見過了無數次的,在每個天光未上的清晨,都如約而至地攀爬在我的腳踏車坐墊上,總要把它們拭盡後才能正常騎乘。而故鄉又在何處呢?故鄉那片熟悉的雲水,卻已然沉默在兩千公里之外的江南了。眼睛忽然沉重地酸澀起來,這遲來的遊子的情思,竟有朝一日也允我向它臣服了。
我和圖書館的交集究竟還會有多少年呢?我明白,即使是在此處——在北地,我也終有一日要離開的,那時,這望過無數次月亮的、陪伴過我無數個清晨暗夜的圖書館,也只能留於我的記憶中了。我向前走去,一座座圖書館卻仍在原地靜靜地佇立,沉默地等待著另一批學子的到來。到那時,晨光和夜色還會按時交替,不同的清澈目光依舊透過閱覽室同一扇清澈的窗,歸往遠方遼闊的天地。
寫到這裡,想起曾經的很多事,心情漸漸變得踏實而開闊了。我放下筆,默默走出圖書館去。月亮一如既往,靜默而亙古地高掛在夜空。
本文來自【新甘肅】,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資訊公共平臺提供資訊釋出傳播服務。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