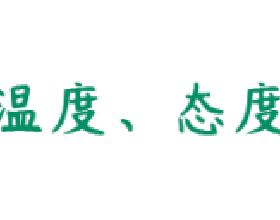【追 憶】
白化文,北京大學教授。曾兼任中華書局《文史知識》雜誌編委、蘭州大學《敦煌學輯刊》編委、《敦煌學大辭典》編委、中國楹聯學會顧問、中國俗文學學會常務理事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分會副秘書長。此外,他還曾擔任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委員、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委員會委員等職。
“不能不佩服李清照。李清照就是李清照。”在一次講解古漢語的對偶結構時,白化文先生曾舉李清照詞為範例,這樣稱讚其精妙。此刻追憶先生之時,我要借用他的話:“不能不佩服白化文。白化文就是白化文。”
知識廣博,在這一點上,我尤為佩服白化文先生。在我認識的學人中,博學多識、治學領域寬廣者不少,不過如白化文先生這樣對社會文化知識幾乎“照單全收”者,真的稀見。我這用詞毫無誇張,因為他的學識涉及領域,遠非我等一般專業工作者可以比擬:從古代漢語、書法到敦煌學,從《昭明文選》到《紅樓夢》《西遊記》,從《大藏經》到《明代版畫》,從宗教廟宇建構到法器服飾演變,從六經典籍到歷代出版和手書篇章,從高雅的皇家秘藏到底層民眾的生活細節,從佛學、儒學、道學到民間信仰和習俗,當然還有上千年的詩詞小說紀傳各體文學,幾乎全都成為他的知識庫存。至此,你大概可以設想這裡面的豐富性、複雜性,達到了何種程度吧。
《文史知識》的老一屆編委來自北京各大學和學術出版機構,都是文史領域和教育界的學者。記得編委會開會時,凡討論種種學術問題或者教育問題,自有各路專家發言應對,高見迭出,但對諸多問題都能提出中肯意見的,白先生當數第一人。有時候開會遇到一個有點複雜或者比較陌生的問題,大家態度持重,陷入凝思,一時無人發言,主持人楊牧之就會說:“那大家思考一下。我們先請白先生談談吧?”於是他就以很平靜的聊天語調開腔說起來。記得有一次他是這樣說的:“啊啊,慚愧啊!我先來個投石問路吧。不過我可能胡說一氣,把大家引入歧途,各位就當我是反面教員吧。”會場上,一下子氣氛就輕鬆起來。接著他就從清理題目開始,把問題捋出一個大體的思路,再逐步分析演繹,說出他個人的意見。就這樣,眾人的思路也被漸次引發開來,而真正的問題討論也就由此開始了。這種場面並非個別。正因此,有時正逢他偶然有事難以分身,未能出席《文史知識》會議,這會盡管照樣開得下去,問題照樣得以解決,但總是少了一點特別的活躍氛圍,感覺上好像總有一點不夠意思。每次眾人皆感慨,有白化文與沒有白化文,是不一樣的。
《文史知識》當年還多次舉辦過一些與讀者的交流溝通活動,活動有時是書面的,有時是現場的,這是它的辦刊特色之一。有的活動比較重大複雜,一時難以抉擇應對,這時候往往也能顯示出有白先生與會的重要性。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電視臺要在春節期間舉辦全國性的書寫春聯比賽,邀請《文史知識》派專家出席,眾編委聽說,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但又怕萬一出錯,影響太大,無法挽回,所以議論半天,終於一致推薦白先生為代表。他在節目上果然不負眾望,神色祥和,儀態端莊,侃侃而談,從楹聯的產生歷史到社會價值,從欣賞重點到編寫要領,都講解得深入淺出、簡明扼要,把一個有點古奧的陌生內容,硬是搞成了通俗的熱門節目,增添了春節喜慶氣氛,吸引了大批觀眾的眼球,此後竟接連辦了好幾屆。《文史知識》風頭出盡,名聲大振,白先生厥功至偉。
開會需要他,活動需要他,即使平時閒談之際,他的存在也是不可替代的。主要就是他出於廣博知識和活躍思路,使得話題可以朝你意想不到的方向展開,令人意外受益。對此,我體會殊深。有一次我們倆閒談,他忽然問我:“徐公,您是搞建安文學的專家,我請教您:建安七子為什麼是七個人不能是六個或者八個人呢?”面對問題,我當時回答說:“白先生我不敢妄稱專家。不過您老的問題呢,我是這樣理解的:大概正好有這麼七個人吧?在曹丕心目中,當時寫作水平最高的人就是這七位了。”“可是問題來了:您《魏晉文學史》裡說了這七人中第一位是孔融吧?孔融固然名氣很大,但他與其他幾位特別是王粲,並沒有一起待過呀!王粲是建安十三年才從袁紹手下來到曹操幕中的,孔融在此前好幾年就被曹操殺了,應該說他們連互相認識的機會都沒有,怎麼可以把他們強按在一起,說成是建安七子呢?說建安六子,不是更符合實情嗎?”至此,我認可他說得有道理,但一時也說不清曹丕為何就不考慮這一點。我就反問他:“那白先生您認為這是怎麼回事呢?”“那我就班門弄斧啦——我覺得,曹丕的七子說法是有點兒勉強。他為什麼要勉強呢?我覺得他就是為了湊一個‘七’,為什麼要湊七?就因為孔子說過‘作者七人’嘛!他湊成了‘七’,那豈不就可以向孔子那裡靠了嗎?要是被他靠成了,他曹丕不也就成了第二個孔夫子、孔聖人嗎?這有多光榮偉大啊!所以他要說‘七子’,而不願意說‘六子’或‘八子’。至於孔融與王粲他們是否在一起待過,是否互相認識,那不重要,可以不管。——我這是瞎說啊!”
聽到這裡,我真的深受啟發。此前我也曾對曹丕“七子”之說,有過懷疑看法。但我懷疑的重點是“七子”應該包括哪些人,特別是為何有孔融而沒有楊修。楊修聰明異常,文采斐然,而且與王粲、劉楨等人年齡接近,同處一時,他顯然更合適進入“今之文人”的“七子”中;我思考的結論是隻因楊修與曹丕關係不睦,曹丕要排斥他,於是拿孔融來填補。但是我這思路是在“七”的數目之內挑毛病、做文章,而白先生則是要對“七”這數字本身開刀。他這是另起爐灶,在“問題意識”上要高出一籌,而且所說頗有道理。白先生並不是專門研究魏晉文學的,這段偶然談話印證了他學問的廣博性,當然還有他思維的精細靈活和觸類旁通的本事。
類似情形我遇到不止一次。在他與別人談話中,我作為“旁聽生”也曾有過好幾次,而對方也與我一樣,對他的高論,開始往往是愕然,結果則一定是由衷佩服。
在此需要說明一點,博學多識的白先生,與人說話總是“您”“您”的。先生比我大十歲整,我內心視他為師友,他這種尊稱口氣我怎麼受得了啊!為此我曾多次請求他不要這樣稱呼我,但是他不改變,而且解釋說:“我這是老北京的習慣了”,我一聽是這樣,心想我受不了也得受著唄。不過後來我學他每次也必稱他為“您”,甚至還要在後面增加一個“老”字,這似乎有點兒像“以其人之道”,結果他也有些難受了,提出希望我不用“您老”,我當即回答說:“這也是我的習慣啊。”二人相視,哈哈大笑。白先生為人謙遜,本質上擁有真正學問家待人接物的宏大氣度。
我佩服白先生的第二點,是他對問題的詮釋和表白能力。白先生談論問題,哪怕是一個很冷僻很專門的問題,只要從他嘴裡說出來,那一定會拉近與你的距離,變成平易而有趣,讓你儘量理解,充分感動,並且接受它。在《文史知識》會議上,他每次的發言都會冒出幾句幽默話語,引發鬨堂,瞬間能提高會議室的“氣溫”。在他的字裡行間也是如此。他的十大冊“文集”,裡面論及的問題有的很深奧,很偏僻,例如關於佛教印度原始含義和來華後的變化形態,是公認的冷僻問題,懂行專家稀見,一般人更是接觸不到。而他對此就做了成功的梳理和解釋,讓一般讀者也能窺知其大略門徑,同時還能品嚐到或濃或淡的閱讀趣味。有一段他是這樣寫的:
第二十位是閻摩羅王。中國人在他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十殿閻王”,並熱熱鬧鬧地把地獄變成中國式衙門,有判官和牛頭、馬面等鬼卒,有灌黃湯即迷魂湯的黃婆等等。佛教怕他們過分脫離因而獨立化,派出地藏王菩薩掌管。南亞地獄原分男女兩處,由閻魔王和他的妹妹(一說是妻子)閻蜜分管,因不合中國國情,閻蜜被暗中取消,這都是中國人的漢化發展……
這裡的敘述內容,是關於“地獄”之說在中國的傳播和變化,所述完全符合印度佛教的原始教義和落地華夏以後的真實狀況。但是如果把相關佛典經籍裡的原文擺出來,恐怕一般人根本看不明白,因為光是裡面的許多專門名詞術語,就會把你立即弄迷糊了。例如,與“閻摩羅王”有關的典籍文字就有:“道名閃多為閻摩羅王名閃多故其生與王同類故閃多復說此道與餘往還善惡相通故名閃多……”(《法苑珠林》卷九“阿修羅部”)諸如此類,連斷句都很困難,還怎麼去理解它的本義?別說中學生,就是大學裡的文科生也未必能讀懂。但是經白先生的筆寫出來,就很明白順暢了,而且富含生動幽默的情趣。他使用諸多通俗話語,來闡釋“佛教漢化”這個深奧的話題,連“不合中國國情”這樣的當代語詞也用上了,叫你在“熱熱鬧鬧”的閱讀氣氛中,不費勁地領悟一種深奧知識。這樣的本事非同小可,就我所知,在學界白先生是做得極好的。這種化繁為簡、深淺轉換的功夫,本質上是對知識融會貫通的自然結果,這也正是他的功力所在。
白化文先生為何能夠做到以上兩點?這當然歸功於他的勤學,還有在“學以致用”上狠下功夫。他生活中的第一要務,就是看書,什麼書都看。他有一句五字“名言”——“白看?不白看”。意思是,你讀任何書都有益,哪怕是一本“無用”的書也這樣。只要你認真“看”了,你就應該看出它為什麼是無用的。在這過程中,你的鑑別能力和思維境界都能夠得到提升,所以“不白看”。他本人的確是讀書範圍非常廣,非常雜,不但內容上,就是書的品類上也是,他是雅俗共賞,否則他怎能既知道佛教中的原始神像與中國不同地區民間佛像的異同詳情呢,而且地點、位置、佛像形態、姿勢、大小、用料等,說得那樣頭頭是道。不但具體生動,還有圖片配合;道聽途說或者引用他人成果,豈能達致如此境界?結論只能是透過勤奮閱讀和辨識資料,外加悉心思考得來。20年前,我去過位於北大西門外的“承澤園”白先生家,面積不大,裝修陳舊,但室內滿是藏書,排列有致,品類廣泛,內容多樣,它們也體現著白先生的知識構成和治學風采。我這裡要補充說一點:白先生的博學和表述才能,並非憑空產生。他不是天生奇才,是刻苦煉成的。他不但長期在大學裡任教,還曾擔任過中學教師。要面對不同年齡段、知識基礎差異很大的學生,對教師而言,無疑是一種苛刻的教學環境。而白先生無論在哪裡,都是課上課下深受學生愛戴的優秀老師。在這種環境裡,鍛煉出了他既胸懷廣博學問艱深,又口含平易生動話語的大智慧。而這,同樣是融會貫通的本領。
朱熹曾說:“舉一而反三,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晦庵集》卷五十二)這話用在白化文先生這裡,挺合適。
(作者:徐公持,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