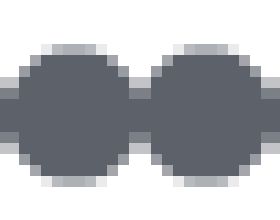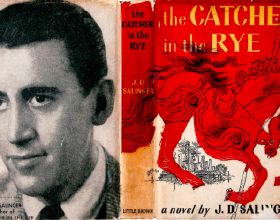在1400年的歷史長河中,都柏林經歷了令人吃驚的變化。在世界和歐洲範圍內,有許多城市在彼此競爭,但卻幾乎沒有一座成為歐洲首都。
都柏林在愛爾蘭歷史以及愛爾蘭想象中佔有非常獨特的地位。愛爾蘭知名作家、都柏林三一學院現代史教授大衛·迪克森(David Dickson)在《都柏林:滄桑與活力之城》一書中,以愛爾蘭歷史的權威人士身份,為我們帶來了生動的都柏林——從它中古時期一路演進至新古典時期的十八個世紀。他以編年的方式記錄這座城市的廣闊與多變,講述了愛爾蘭島的故事:它不斷地在被來到這座城市中的人所塑造,也在不斷地影響著這些人。
以下內容選自《都柏林:滄桑與活力之城》,較原文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都柏林:滄桑與活力之城》,[愛]大衛·迪克森著,於國寬、鞏詠梅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2月版。
作者丨[愛]大衛·迪克森
摘編丨安也
將都柏林這座城市架構起來的,是其寂靜無聲的歷史
都柏林詩人兼記者詹姆斯·斯蒂芬斯(James Stephens)在1923年寫道:“沒有哪一座城市能夠橫空出世卻一成不變,她必是先祖遺傳的積累,這些積累起來的傳統反過來又深刻影響現在的城市居民。居民年輕的時候,城是老城;城中居民變老的時候,城卻再次顯得年輕起來,青春絢麗,令人稱奇。”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是更近代一些的文化評論家,他的看法似乎不那麼樂觀:“過去建造的城市今日不復存在,也沒人能真正瞭解。”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過去確實已經消逝,線索再難尋覓。而大約處於1995—2007年愛爾蘭之虎(Celtic Tiger)時代的都柏林,則如青春四溢的年輕人一樣,活在當下才是人們所熱衷追求的。
然而,將這座城市架構起來的,卻是其寂靜無聲的歷史。就是現在,其悠久歷史也是該城商業名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柏林的歷史從未被如此包裝和商業化過。可愛的導遊們在“美妙的舊時光”上大做文章,更有水準的文旅商人會喚醒喬伊斯筆下利奧波德·布魯姆(Leopold Bloom)的世界以吸引遊客,而市政府會組織一些城市歷史慶典活動,大力宣傳其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然而,這座城市到底是由什麼構成的呢?都柏林單單就是市政管轄下的那塊地域嗎?那樣的話,從19世紀中葉以來就已經完全都市化的很多區域就被排除在外了,而20世紀另外一些城市化的地區就更不用說了。就目前而言,從都柏林北部的馬拉海德郡到威克洛郡的佈雷(Bray),向西到基爾代爾郡的萊克斯利普,都柏林指的就是所有這些城市化的地區嗎?
從政治角度講,這個過百萬人口的“城市”,其內部是各自為政,目前總共有六個郡議會。而如果從都市與周邊可通勤地區的角度看,還存在著一個更大的都柏林;人們每天都在其間往來、工作、求學、娛樂。
1791 年繪製。從埃塞克斯橋對面、沿著議會街的角度所看到的馬爾頓的景色。《都柏林:滄桑與活力之城》插圖
老都柏林人的身份鑑定則涉及完全不同的一些問題——不是關於都柏林在哪裡,而是關於都柏林是什麼的問題。這座城市曾被冠以非常多的標籤,維京人(Viking)、諾曼人、英國人、新教徒、喬治王(時代)的人、民族主義者和共和派。這些標籤幾乎都是過於簡單化了。毫無疑問,自愛爾蘭海以西出現城鎮以來,在這個深陷紛爭的島嶼上,都柏林一直是最大的城市化地區。七個世紀以來,這裡是英國影響力向外擴散的震中地帶,是那一時期大部分時間裡周邊民族英國化的主要渠道。但是對於反對英國的各種勢力來說,這裡是為他們提供喘息機會的避難所。
所以,在不同時期,都柏林都是殖民者的堡壘,也是充滿紛爭的地方。在歐洲和地中海也有很多紛爭不斷的城市,其中有些地方經歷的殘酷遭遇,比都柏林更甚(如布拉格、哥尼斯堡/加里寧格勒、士麥納/伊茲密爾和阿爾及爾)。都柏林與英國和西歐的許多城市不同,幾乎完全逃脫了20世紀工業革命引發的戰爭所帶來的毀滅性影響。但是往更久遠的歷史追溯,都柏林歷史上發生的間歇和倒退,其嚴重性卻是任何其他歐洲都城無法比擬的——有歷史烙印為證。但有一點,像所有的大都市一樣,都柏林也有文化融合的現象。雖然文化差異有時會導致矛盾和衝突,但是這種融合使城市歷史擁有了富含創造性的特點。
1922年,喬伊斯使這座城市廣為人知
都柏林在階級和財富方面極端分化並以此著稱,拿破崙式的奢華與難以名狀的貧困在此共存。就這一點而言,原因同樣極其複雜。都柏林是愛爾蘭全國範圍內社會和經濟創新的中心,但每當發生變革的時候,這裡便成為經濟利益爭奪的戰場;而擁有大城市的身份並得以在城裡工作的優勢卻又是貧困產生的原因。一個世紀以前,這裡有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廠,該廠為其員工提供相當優厚的福利待遇;在那個時候,城中勞動階層的住房難題卻是國際上人盡皆知的醜聞;並且,當地人的酗酒問題已經是極為普遍的現象。
在1916至1922年世紀性動盪的歲月裡,人們思想意識上的混亂和前後矛盾空前突出。1916年4月的復活節起義宛若晴空霹靂,百孔千瘡的城市再次陷入驚恐之中。這次起義一開始並沒有得到很多人支援;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輿論開始轉向,很多市民轉而支援激進的分裂運動。
不到三年,主張分裂的新芬黨竟然在市長官邸的附樓裡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屆愛爾蘭議會)。隨後發生在農村各地的游擊戰以及英軍所進行的相應抵抗,雖然大部分都發生在都柏林以外,但無論其激烈程度如何,源頭都在城裡。1921年圍繞《英-愛停戰協定》或《英-愛條約》所進行的大部分政治角力,主要發生在都柏林市內。
斯蒂文斯醫生醫院的方形庭院。這所醫院 1733 年開業,有 87 張床位,是 18 世紀都柏林最大的醫療醫院。《都柏林:滄桑與活力之城》插圖
然後,在1922年1月,到了移交都柏林堡的時刻。這座城堡是12世紀以來英國統治愛爾蘭的標誌。從12世紀到20世紀,都柏林的命運與英國統治共沉浮。那麼,在1922年的這個時候,當這座城市首次作為‘愛爾蘭人的愛爾蘭’的首都時,她能夠再造新生嗎?政權正式交接之後五個月,內戰爆發。首次衝突雖短但異常激烈,位於都柏林碼頭旁的愛爾蘭公共檔案館的四法院大樓遭到轟炸之後被毀。擁有七百年曆史的愛爾蘭英轄中心檔案館,在幾小時之內灰飛湮滅。
1922年還見證了一部獨特的文學作品的誕生。詹姆斯·喬伊斯用七年時間寫成“一天中的小故事”(指的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這本書)。這部小說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都柏林為背景,卻與《荷馬史詩》中的《奧德賽》遙相呼應。該書在巴黎出版。都柏林本地人對這本書的態度並不明朗,甚至持反對意見,其國際影響力也遲遲打不開局面。可遠在20世紀結束之前,《尤利西斯》就已成為廣為人知的現代主義作品範本之一。可以想見,都柏林歷史上的這一年,因此成為每一位當代英語文學研究者熟知的時刻,而都柏林則成為世界文化園林中與眾不同的角落。這一年,喬伊斯使這座城市廣為人知;但也正是這一年,公共檔案館的一場大火卻將探索城市深層歷史的潛在資源毀於一旦。這真是一件具有諷刺意義的事情。
人們對都柏林歷史的學術研究收效甚微
當時曾有兩個旨在挖掘都柏林歷史的專案。第一個是《都柏林古代紀錄年表》(Calendar of ancient records of Dublin)的出版,這項工作早在1889年就開始了,最後一卷,也就是第19卷,於1944年出版。該書由約翰·吉爾伯特爵士(Sir John Gilbert)及其遺孀編輯完成,是1447年至1840年政府重組之前城市管理部門釋出官方政令合集的評述版。這些珍貴資料同其他重要市政檔案一起並沒有受到公共檔案館大火的影響;這套書記錄了城市深層的、錯綜複雜的歷史,能夠得到當時民族主義地方政府的認可,得以完整出版,實屬不易。
吉爾伯特在19世紀50年代曾寫過一本關於都柏林城市發展歷史的著作,頗具創新意義。他終其一生致力於檔案蒐集、整理、保護和出版工作。他是倡導對城市檔案進行專業保護以及愛爾蘭公共檔案館建設的主要發起者。另一個“政權末”(fin de régime)專案則完全是非官方的——成立於1908年的“愛爾蘭喬治王朝學會”(Irish Georgian Society)是一群業餘愛好者組織的,政治傾向主要是統一黨派,公開的使命就是整理和出版都柏林的建築和裝潢歷史,即18世紀漫長的“古典”時期的建築史。到1922年的時候,已經出版五卷,包括1916年復活節起義和1922年內戰時毀壞的很多建築和檔案的詳細圖片和文字記錄。到了這個時候,使命的初衷已經不知不覺被放棄了。
約瑟·都鐸1752年所作全景畫,從伯格的圖書館建築群延伸至荒蕪的林森德半島和繁忙的都柏林灣。《都柏林:滄桑與活力之城》插圖
這些事件之後,人們對都柏林歷史的學術研究收效甚微。事實上,在很多方面,老都城融入新愛爾蘭的過程頗為艱難。其特別的英系歷史經歷使其無法輕易適應民族主義為主導的大環境。對新政權來說,公民道德建設完全排不上議事日程。無論是位於城中的民族文化機構,還是當地政府,即都柏林市政廳,都沒有資源和遠見支援和發展都柏林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研究。由個人愛好者管理的一所城市博物館於1944年開館,一直低調運作。國立博物館對都柏林歷史的處理態度(至少到20世紀90年代為止)僅限於慶祝一下復活節起義而已。
“老都柏林學會”成立於1934年,幾十年來,一直是學會的業餘愛好者將都柏林的過去展現在大家面前、讓人們熟知。他們偶爾也會發表演說、呼籲對其進行保護。透過回顧,我們看到1952年出版的莫里斯·克雷格(Maurice Craig)的著作《都柏林社會和建築史》(Dublin: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這是對都柏林歷史進行嚴謹學術研究的開始。這本書對都柏林兩百年來的自然歷史所做的講述,文字優美、描寫細膩,不僅高超的學術水平貫穿始終,其說理過程也是透徹、深刻,入木三分。克雷格認為,由奧蒙德伯爵提供保護的“復辟之城”是“喬治王”時期都城的仿製品。其全盛時期是在18世紀晚期,社會和政治領域由新教統治階層全面掌控,到1801年英-愛議會聯盟成立之後便基本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克雷格的這份研究很有價值、一版再版。最近三十年裡也出版了很多關於都柏林歷史的書籍,數量大為可觀,前所未有,部分可做典藏,其他則是面向普通讀者的普及讀物。再就是貫穿20世紀70年代的一場曠日持久的公開論戰:當時,在伍德碼頭(Wood Quay)和基督大教堂(Christ Church Cathedral)之間發現了維京時代的文物寶藏。公眾對這座中世紀小城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由於一個考古研究專案一直處於進行當中,並且以《中世紀的都柏林》為名出版了系列專著,藉著這樣的東風,遺址得以儲存下來。無論在考古、建築還是文獻方面,對中世紀後的研究,雖然水平參差不齊,但著述頗豐。
自1988年都柏林千年慶典以來,對城市歷史所進行的研究、思考和著書比之前一千年間所做的都更多。想到這一點,會讓人頗感欣慰。
一位詹姆斯·喬伊斯的同時代人在1902年寫道:“都柏林就是一座大村落,一個骯髒的村落,謠言是這裡的最高統治者。”幾乎一個世紀以後,一位頗有見地的外鄉人對都柏林的特點做了這樣的概括:“社群內的居民關係密切,這在如此規模的城市裡並不多見,人們聚在一起談天說地,各個階層都不乏文韜武略、機智應對之士……”喬伊斯在《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中,捕捉到這種市井談天的情景。自那以後,很多寫作高手對此都有成功嘗試。歷史文獻很少能夠捕捉到口語語言的力量,而有實體的手工藝術品則完全不能。現在有關現代都柏林的聲像資料極為豐富,但從史學家能夠採用的角度講,時間上不夠久遠不說,內容也過於繁雜。所以,文字記載的歷史只能建基於文獻、歷史圖片、建築、考古以及物質文化上。
我在這裡的目標是嘗試理解過去,而不是再造。但是在歷史的大舞臺上,有些演員卻將同臺人擠進了陰影,因為那些有能力、富有的成年男性主導了20世紀前所有形式的歷史記錄,這一點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任何一篇常規的歷史分析中。退一步講,如果我在這裡的目的是理解都柏林的演變史,那麼焦點就應該仍然特別停留在確實有影響力的人群當中。小人物的聲音,即使是在20世紀也無人聽到——就是那些囚犯、無人收留的病人,以及受欺凌、虐待的人們——他們在歷史記錄中寂靜無聲,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命運毫無辦法,對城市的發展也毫無影響力。唯有非常事件、自然災害、爆炸和惡性犯罪才構成都柏林人的雜史,這些雜史只會被正常歷史隱藏;在可能的情況下,這類能說明問題真相的配角人物才會被善加利用。
作者丨[愛]大衛·迪克森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張進
導語校對丨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