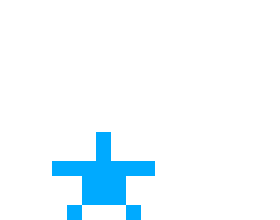這是一個路邊攤,賣大餅。門口外搭一個簡單遮雨棚,煙熏火燎中夫妻兩人正忙得歡實。我還記得那位女攤主,是個牙尖嘴利的,上次不知哪位主顧得罪了她,她便大聲喝罵:就你多嘴,看不找根繩把你拴門外樁子上去!對方見討不到什麼便宜,也只是呵呵的笑。其實也是一種默契,罵人的爽快,捱罵的受用,是老熟人專屬資格。
我站在餅攤旁邊等人,女攤主正用一根兩尺多長的竹片,從餅鏊子上挑下來,又耍起一把菜刀,刷刷把餅劃作幾片,手不停嘴不停:你要多少?好嘞,3塊2的,算你3塊錢的餅,卷多少肉?有剔骨肉有正宗鉅鹿香腸,要哪種?要不要香菜,要不要辣椒?拿好,慢走?你要要多少餅?——他的丈夫在擀餅的空隙裡,幾步搶過來,啪啪地磕開幾個雞蛋,噼哩啪啦地在碗裡打散,那邊,女攤主歪著脖子夾著電話,在給不知何方的神聖隔空喊話:嗯嗯,沒問題。你要的不是雞蛋的嗎?正下鍋炒著呢,你到了,這邊也正卷好了。沒問題,瞧你說的!……來來,下一個,要什麼肉?
下一個站在我的身邊,也是一位女顧客,她說:4塊錢的餅,嗯……呃……4塊錢的肉,香腸就行了。
女顧客說話聲音很小,我幾乎就站她的身邊,也還是聽不清楚。聽她的說法,我還是有點奇怪。因為,一般情況下,4塊錢的餅,配肉少說也要8塊錢才算正常。她這種要法,很少見。我不禁扭頭看一下:中等偏矮,偏瘦的個子,臉皮暗灰色,穿一件半舊的蔥綠色羽絨服。那邊女攤主沒說什麼,還是嘴裡應承著,手腳麻煩地把大餅稱好,又在電子稱上稱了短短一截香腸,用菜刀切成片,隨手撒到大餅上。大大一張餅,零零散散幾片香腸,看上去不太配套,攤主又去盛青椒的瓷盆裡,抓了一小把青椒末,又在另一盆子裡抓了香菜,撒在鋪開的大餅上,青青的菜末,和上幾片香腸,蓋在大大一張餅上面,還是顯得破綻百出。
餅攤子對面女顧客正掀開羽絨服,從褲兜裡拿出錢來,幾隻零票子在手裡數著,抬頭看見攤主正要把大餅捲起來,她趕忙叫了一聲,止住對方的動作:誒!你別。……他……我不吃肉,你只卷一個有肉的就好了。她的聲音很小,但還要讓對面的攤主聽到,於是也不得不讓我聽在耳朵裡一些。
攤主“哦”了一聲,反問:是說只卷一個肉的嗎?那一個還卷不捲了?
女顧客說:卷,卷,一樣卷。
女攤主明白了,就又把一張大餅在案子上鋪平,五指輕輕扒過去,把幾片香腸全部趕到右邊一半處,左邊空出來,兩頭按住,捲成一個圓筒,順勢中間一刀下去,截成兩個餅卷。從外表看上去,兩截餅卷沒有什麼區別,真正的不一樣在裡面。攤主知道,顧客也知道,我也碰巧看到了。
女顧客交了錢,拿好兩個餅卷匆匆地走了,她的電動車就停在路邊,我看她騎了車子,轉過前面的牆角不見了。我忍不住問一下攤主:她剛才說的,自己不吃肉,那個有肉的餅卷是給誰的?
雞蛋已經炒好了,定製雞蛋餅卷的人還沒有出現,女攤主“譁”地把雞蛋撒在鋪好的大餅上:這人啊,說是不吃肉,真的不吃?還不是捨不得?那個肉餅卷是給她老公的唄!聽她說“我當家”的!好像在前面工地上幹活的,說是一天一百多塊,可都是力氣活,這麼大一摞瓷磚搬著上五樓,不吃點肉怎麼行?頂不住!嘿,您要點什麼?餅卷,有肉的雞蛋的,紫菜湯、餛飩……裡面有座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