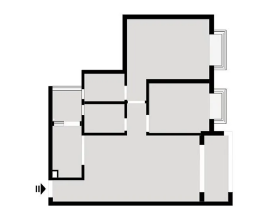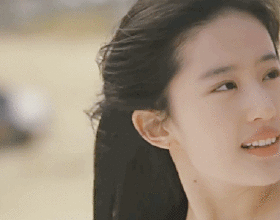今年是基耶斯洛夫斯基80週年誕辰,當人們談起這位偉大的波蘭導演,最先想到的總是“紅白藍”,而對《兩生花》的評價往往是“不夠深刻”,但今天當我們回看這部好看的電影,也許我們會意識到任何解讀,都不如“沉浸”其中。
《兩生花》的魅力在於“喚起”
不得不承認,對於電影來說,這是一個我們會害怕表現出對“低階品位”不敬的時代。我們現在甚至會屈服於某種低階品位,特別是當一部藝術品質不高的影片成為票房大熱時,我們總是怕所表達的某些觀點會惹了“眾怒”,總是將自己的真實評價隱藏起來。這時候,再讀一下著名影評人羅傑·伊伯特的《偉大的電影》是非常必要的,羅傑的文章最大的優點就是毫不做作,他只用三言兩語便可以告訴你,有些電影因何“偉大”,你只管大大方方地去愛就是了。
最近《偉大的電影》中文版第三卷出版。這裡面收的文章是羅傑罹患絕症之後的作品。但是用大衛·波德維爾的話說,這批文章是羅傑影評的巔峰。拿到書的那一刻似乎又得到一個保證:封面用的劇照來自波蘭導演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薇洛妮卡的雙重生命》(1991,又譯《兩生花》)。
今年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80週年誕辰。想到這一點,便意識到他去世得的確太早了點,但是在有限的生命裡,他作品的數量和質量都是驚人的。那麼,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中,羅傑又為何獨獨選了《兩生花》呢?(或許有人覺得羅傑點讚的美國電影太多了,但這無可厚非,他日常接觸最多的就是美國影人,而且,美國電影也有很多佳作確實是我們並沒有注意到的。)
有意思的是,人們在評價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時,通常《兩生花》都不是得分最高的那部。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的思想性,或者政治性,更吸引“學院派”的影評家(比如《機遇之歌》《永無止境》等或許更吸引他們)。但羅傑·伊伯特不是學院派,用波德維爾的話說,他是作家(他用的詞不是writer,而是manofletters)。這個評價很高的,可能蕭伯納、蒙田、桑塔格、本雅明都可以用這個詞去稱呼。坊間大學教授多矣,但這樣真知來自真摯的“作家”卻極為稀有。我認為羅傑·伊伯特對《兩生花》的偏好就是出自一個“作家”的本能直覺。
《兩生花》可能也是最容易挑出毛病的,比如它的故事結構是鬆散的,好像也沒講出什麼故事來;比如有人批評它是“迷信”的,“心靈感應”這些東西,怎麼證明?此外,它還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票房最高的作品,在世界各地至今都有很多“鐵粉”,其中不乏眾多的少女粉絲,這部影片很可能還衍生了不少以“世界上的另一個我”為題的同人文學或漫畫創作,故事裡的木偶故事也相當具有“二次元”的意味。這種大眾接受度很可能讓人覺得它不夠“深刻”。
《兩生花》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裡的確也算是另類,所以不能按慣常的思路去看它。羅傑·伊伯特准確地指出了這部電影的魅力在於“喚起”。它並不負責解釋——我們可能會有的某種神秘主義體驗,本來就無法用實證主義的思路去解釋。雙胞胎通常都認為彼此之間有一種“心靈感應”,一座島上的黑猩猩掌握了一種技能,另一座島上的黑猩猩也會發展這種技能。“去過某地”“現在這一切好像以前發生過”的體驗也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確會偶爾遇到的,那麼這部電影就是讓我們深入其中,但就像羅傑·伊伯特所說,看完這部電影,你最不願意做的就是揭示劇情,那就等於把雲朵變成了雨滴,而我們要做的其實就是“沉浸”其中。
拉斐爾前派的美
但我們還是可以分析,這種體驗是如何在大銀幕上被“喚起”的。
《兩生花》的核心人物是薇洛妮卡。她是絕對第一女主角、視覺中心,這部電影情節發展和故事推進都依賴於她那女性的直覺,所以,這個面孔(以及氣質)是決定性的。基耶斯洛夫斯基非常準確也非常幸運地找到了伊萊娜·雅各布來演出這個角色。大導演和演員的關係其實常常是微妙的,塔可夫斯基和佈列松這樣的導演對演員是無情的,只將他們視為工具(模特兒)。夏布羅爾甚至毫不客氣地建議,要避免在演員的空檔期與他們見面。但基耶斯洛夫斯基和演員的關係似乎還不錯。一開始他聯絡過好萊塢影星安迪·麥克道威爾,安迪最初同意,但後來又變卦了,接了一部純粹的商業片——假如她來演出,這將是一個成熟的女人而不是一個女孩的故事了。很可能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看到雅各布之後就改變了這個故事的基本氣質。當時伊萊娜·雅各布只有24歲,她的美麗和奧黛麗·赫本一樣(儘管他們的相貌完全不同),屬於東方人和西方人審美的最大公約數——嬌小、柔和,沒有攻擊性。
粉絲濾鏡總會誇大演員的重要性,但對於這樣一部討論女性感覺的電影來說,她的面孔的確非常重要,這種重要性可能不亞於德萊葉的《聖女貞德》。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本事就是在24歲的雅各布的面孔上面看到了一種拉斐爾前派的美,一種不可思議的、無法褻瀆的純潔感。這就使得她的裸體鏡頭儘管美得驚人,卻不讓人產生邪念,而這一點的確和所謂“顏值”的關係並不大。
這也就是使得“波蘭的薇洛妮卡”得以成立的秘密——雅各布在波蘭古城克拉科夫的環境裡絲毫不令人感覺突兀,或有“外國人”的感覺。克拉科夫是歐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多處世界文化遺產,有各種哥特式、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的教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攝影師將雅各布拍得就像宗教題材繪畫中的人物(當然他使用了不少黃色濾鏡),因為波蘭的薇洛妮卡就是要有聖潔感。她明知道自己有心臟病,唱高音會有很大危險,卻為了唱聖詠不惜冒險——這裡和“敬業”或者明星選秀沒有任何關係。“好女孩”薇洛妮卡也不是世俗意義上的,儘管我們看到所有的人,從長輩、老師、同學,都很喜歡她。
而雅各布又能勝任不算“好女孩”的法國小城女孩薇洛妮卡,甚至她的法語還帶點兒口音,不那麼“巴黎”,非常接地氣。這可能更接近於她本人生活中的樣子。法國的薇洛妮卡透過波蘭的薇洛妮卡對生命有了別樣的感悟,確認了靈魂的存在——這種過程就是“喚醒”,假如雅各布沒有將這個過程真實地演繹出來,觀眾也無法被“喚醒”。
聖詠的“喚起”
可能我們很難設想這是一部音樂片。當然它不是好萊塢的那種音樂歌舞片,但它算得上是真正的一部音樂電影。或許它的音樂段落並不多,但就像基耶斯洛夫斯基說的那樣,“美國人從頭到尾都把音樂塞得很滿……”
《兩生花》和《藍色》一樣,都是關於音樂的電影,是同一個作曲家基紐·普雷斯納。他的一大特點是從影片創作一開始就參與進來。這意味著什麼呢?當然是真正的音樂創作。這需要音樂家與導演建立起真正的夥伴關係。所謂“電影音樂”中,最常見的是“電影配樂”,大多數電影音樂是“音配像”,或者透過閱讀劇本來創作主題音樂,但是那樣就意味著將文學語言“翻譯”成音樂,這和開始就用音樂思維效果當然是不一樣的。
舉個例子來說,比如要傳達“莊嚴”,作家、畫家、音樂家的思維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都經由另一種媒介“翻譯”一下,比如文字工作者經常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可以用文字描述給藝術家“命題作文”,這根本就是錯的。一段音符從內心的流出,甚至總是發生在語言組織的文字描述之前。
《兩生花》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音樂形象,主題音樂就是在克拉科夫的一箇中古時代的地窖式教堂裡響起的——普雷斯納本人就來自克拉科夫,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學之一雅蓋隆大學畢業的,主修歷史學。為什麼要選擇一個地窖式的教堂呢?因為在外敵或“異教徒”入侵的時候,它能夠保護人們的靈魂不被魔鬼侵襲。無需多解釋它的“意義”,或“辯解”它與聖詠之間的關係。它就是一種聖詠。這方面真的需要作曲家是個有“靈魂”的人。影片中假稱這是十七世紀的一個荷蘭音樂家某某寫的,恐怕真的騙過了很多人吧。
這段聖詠是用古義大利語唱的,歌詞是但丁的《神曲·天堂》中的一小段:
哦,你們划著小木船
因為渴望聆聽我的歌唱
為隨載滿我聲音的木筏駛向彼方
請回到你們熟悉的故土
不要尾隨我冒險飄向茫茫的海洋
以免失去我而迷航
我要橫渡那無人越過的大洋
因為我有智慧女神吹送
有阿波羅導航
九位繆斯示意大熊星引領方向……
或許不必去推敲但丁每句話都說了什麼意思,但是音樂本身就是“語言”。這種音樂就是“喚起”的。和世俗音樂完全不同,聖詠是需要仰望著去聽的,這個姿態就是一種心靈向上的運動,是通往神性之路的。為什麼薇洛妮卡的面容有一種沉靜的喜悅感?她說的“我並不孤獨”是什麼意思?只有當視覺和聽覺組合到一起,我們才能強烈地感受到自己在被“喚起”,接下來就是“喚起”之後好奇地去探尋“為什麼”的過程。
當木偶藝術家亞歷山大用一個芭蕾舞演員的死帶給小學生們一種關於死亡的教育時,這段主題音樂同樣“喚起”了一種精神上升的運動:死去的芭蕾舞演員長出翅膀,變成飛昇的天使。
反套路的成長
《兩生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西方的第一部影片。跟有的電影大師不同,他很重視觀眾的理解程度,隨時會調整,儘量將故事講得好理解。但這並不意味著他遵從於票房邏輯。為什麼這個講兩個女孩心靈感應的故事不是一部“小妞電影”?因為影片中的精神成長就完全不是少女讀物的內容。即便從女性成長的角度來看,這部影片也完全不是套路式的,雖然“愛情”在其中也佔有很大的篇幅。
法國的薇洛妮卡開始其實是孤獨的,因為她不理解“愛”,即找不到與他人情感連結的方式。她道德感模糊(作偽證,難以體察他人的痛苦),跟漂亮男孩上床,但肉身的快樂依然令她孤獨。看了木偶藝術家亞歷山大的表演後,她跟爸爸說,“我想我戀愛了。”這本身就是一種成長。但是最大的成長是在最後,觀眾可能以為她和亞歷山大“在一起”了,這不是最美的安排嗎?
但其實是相反的。亞歷山大只是在一個層面上“喚醒”了她,讓她知道自己與波蘭的薇洛妮卡的關聯,並在最後指出她早已在克拉科夫偶然拍過波蘭的薇洛妮卡的照片。在短暫的接觸之後,她覺察到亞歷山大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他只愛故事,他和自己的關聯也是因為故事。用今天的話講,她是“工具人”。但他對故事的攫取,其實已經侵佔了她私人擁有、不宜外宣的那一部分。當她看到亞歷山大興奮地製作了兩個薇洛妮卡偶人的時候,她是沒有愛意的——用基耶斯洛夫斯基本人的話來說,就是“她在電影結束時比一開始聰明多了”,這又是一層成長。
《兩生花》的原聲唱片僅僅在法國就銷售了超過五萬張。考慮到西方正版音像製品高昂的價格,這在當年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也讓普雷斯納聲名遠播。基耶斯洛夫斯基英年早逝的時候,普雷斯納非常悲傷,很久走不出來,他對媒體說:“我感覺自己生命裡的一部分死去了。”他可是一個相當高大魁梧、滿臉鬍子的漢子(波蘭是一個盛產大力士的國家),但這相當《兩生花》,也有力地證明了它所能夠“喚起”的絕不僅僅是女性。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