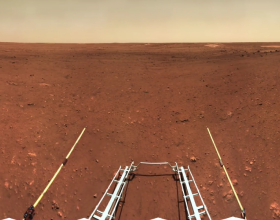《梁莊十年》是作家梁鴻繼《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後的第三部梁莊故事。“在梁莊”“出梁莊”是以梁莊為原點的空間轉移,“梁莊十年”則開啟時間之維,重在記錄“變動中的感覺”。作者以梁莊與梁莊人十年來的現實遭際與命運浮沉,勾勒出中國當代村莊與時代共振的軌跡。
《中國在梁莊》與《出梁莊記》均彰顯出梁鴻強烈的問題意識與介入現實的有力姿態,她以“參觀者”“訪問者”的身份出入梁莊,運用學者的理解與視野觀察梁莊人的生存境遇,並藉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物故事叩問反思關乎社會、國家、歷史命運的深層結構性問題,其中不乏充滿人文關懷的自省意識。一般而言,先在的主題預設既是理解描寫物件的線索,也有可能限制讀者的闡釋空間。因此,梁鴻在後續的《出梁莊記》中避免預設判斷,而是“從人物的行動、語言和故事中尋找他的結構和邏輯”。她不是輕率地站在道德與公理的制高點上發出譴責,而是試圖努力看見、理解梁莊人“心裡面的深流”,揭示現實的複雜性。
與《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不同,新作《梁莊十年》在創作上的變化,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呈現出結構與情感的“內化”。具體表現為在書寫物件上由事件化轉向日常化,作家的寫作意識從外部旁觀化為內在沉浸。全書共5個章節,分別從房屋、女性、土地、回鄉和生死角度觀照梁莊人。梁鴻延續了將敘述者“我”的所見所聞與梁莊人的自述記錄相結合的形式,但“我”時常退場、隱於幕後,取而代之的是基於合理想象的文學性描寫,賦予文字更強的故事性與可讀性——這從“福伯有福氣”“五奶奶上街去理髮”等平實而有童話意味的小節標題中便可窺見一二。
與前作相比,《梁莊十年》顯得更“輕”,“輕”既指字數所標識的篇幅體量,也與基調的“沉重”相對。梁鴻適當收斂理性啟蒙式的批判鋒芒,轉而關注梁莊個體的生存境遇與生命體驗,呈現出對鄉村倫理人情的迴歸與認同。這並非簡單的倒退,而是建立在深刻反思基礎上的回撤——回撤到“人”的存在本身。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二章“芝麻粒兒大的命”,梁鴻第一次將凝視的目光轉向梁莊長期缺乏關注的女性群體上。她將象徵一個人主體身份的名字還給失落在時間深處的梁莊女孩們,並設法與分別近30年的燕子、春靜、小玉重聚,傾聽她們真實的往事與心路歷程,“讓她們重新在梁莊的土地上生活,盡情歡笑,盡情玩耍”。
末章“生死之謎”是有意味的收束,關懷“人的消失”這一終極問題。“門開著開著就不開了”,既指涉破敗不堪卻“毫無意義地上著鎖”的老屋之門,也隱喻不經意間戛然而止的歲月與生死之門。梁鴻寫下逝者的名字,逐一交代他們的生平:清立、梁清發、梁清朝、梁萬生、梁興隆……直到最後,梁鴻的父親,梁光正。作者以文字為媒介,以紙張為載體,為遠去的鄉人們在紙上立起一座座小小的碑。“這時,紀念才真正開始。遺忘也真正開始。”
最後一節“少年陽陽”寫“我”和村人坐在五奶奶的院子門口聊天,秋風捲起金黃的落葉,“我”視野中的公路、藍天、麥秸垛乃至文哥家的破三輪車,在金色的光與葉籠罩下如夢似幻——“我”第一次意識到梁莊竟如此美麗。誠如梁鴻自言:“我和梁莊的關係變成了一個人和自己家庭的關係。”這一“覺”,用了十年光陰。十年間,梁莊的人來來去去,離鄉或返歸、逝世或成長、失落或重聚,每個個體的經歷都是梁鴻“長河式的記錄”中真實的浪花,梁鴻與這些浪花的遭逢,也構成了她審視、清理自我生命的契機。
《梁莊十年》以“我”和“少年陽陽”分別“往前走”的場景作結,留下近於“光明的尾巴”,其中隱含著梁鴻的生命哲學:“生活如此古老又新鮮,永恆存在,又永恆流逝。但並不悲傷,甚至有莫名的希望所在。”梁莊系列未完待續,但已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梁莊傳”,熔鑄了梁鴻對梁莊這片故土的眷戀、深情、反思與悲憫。下一部梁莊書寫何時問世?我們和梁鴻一樣,“幾乎等不及時間的到來”。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