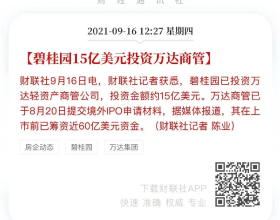楊國強
以陳寅恪先生的學問而論,我們隔了好幾層,所以不敢妄發議論。今天應會議的安排在這裡略陳一己之見,只能是把陳先生當成中國近代歷史變遷中產生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象,選取他的三段話,就我的認知所及,說一點個人的理解。
一
第一段話,陳先生說:“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
這段話分三層表述,意思其實是一樣的,不古不今對應的是咸豐同治,湘鄉南皮對應的也是咸豐同治。與歷史中國的古老相比,其心目中的咸豐同治已是不古。這種不古反映的是西人東來,而後中西交衝所催發的世變。以歷史時序而論,西人以武力作前導的苦相逼扼此前二十年就已經開始。但作為對比,是發生於道光一朝的鴉片戰爭兵火沿及江浙閩粵,而當時僅以海疆騷動視之。戰爭起於地方,也止於地方,並因其與中原和內地空間上的相隔遙遠,對當日士大夫群體的實際影響非常有限。所以後來的二十年裡,中國遠看西方世界仍然一派懵懂而未知回應。至咸豐年間,第二次鴉片戰爭先起於廣東,又在七年之後打到北京,進入了王朝的中心和重心,並燒掉了圓明園。在這個過程中倉惶出逃的咸豐皇帝第二年死於熱河。由此造成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衝擊和震動。當時人說二十年之間中國再敗於泰西,說是“相對一哭”,“為之大哭”。而後是衝擊和震動之下的中國人不得不正視原來不在視野之內的西方人,對於身當其衝的那一代士大夫來說,這是一種深重的痛楚和茫然。曾國藩謂之“不知所以為計”,王先謙說是“智勇俱困之秋”,陳述的都是以中國人的歷史經驗作比照,則西方人帶來的已既是一個歷史經驗之外的陌生世界,又是一箇中國人擺脫不了的世界。再敗於泰西說明中國人的辦法對付不了西方人,所以回應西人的衝擊只能借法自強,即借用西方人的辦法對付西方人,這個過程以造船造炮為起點,牽連而及,新的經濟關係,新的技術,新的觀念,新的文化沿借法之途由外而入,遂使舊日的中國隨之而變。咸豐同治因此而與康雍乾嘉道判然不同。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近代化的實際開端是由咸豐同治之際為起點的。主導了這種變化的中國人都長懷一腔無可奈何的意不能平,以沈葆楨創辦福州船政局之日自謂“以萬不得已之苦心,創百世利賴之盛舉”為例項,正說明這代人的心中之所願,是取彼之長,以新衛舊,是中體西用。而兩千年曆史之古,遂不得不因之而變為“不古”。
以咸豐同治為“不古”,則“不今”應是咸豐同治以後到二十世紀前期的歷史變遷,尤其是十九世紀後期因甲午戰爭而促成的戊戌變法,以及二十世紀初年因庚子辛丑之變而促成的清末最後十年新政。在咸豐同治以來的三十年取新衛舊之後,這一段後起的歷史已經把古今中西之爭的重心移到了除舊佈新一面。戊戌年間康梁力倡大變、速變、全變,以此效西法,其要旨已是在變中國的本身,變中國的內裡,因果相及,便是中西之間不復再能以體用分界。以心中之意態論三十年之間的變遷,顯然是前代人的萬不得已,這個時候變已成了對西方世界文物制度的仰慕。至庚子辛丑之後,仰慕又變為崇拜,梁啟超說其時的中國無人敢為守舊之言,與之對應,則是當時人眼中常見的“奉西人為帝天,視西籍為神聖”。
十九世紀的中國曾經屢戰屢敗,但屢敗的中國人仍然與西方人相持相抗。從四十年代以來的半個世紀裡,中國人備受勒迫逼扼,但中國人仍然相信以理抗勢,所以仍然屢仆屢起。歷史中國留給後來中國的觀念,是以是非善惡為理,強弱利害為勢。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進化論傳入,已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古今中西之通則,倡說的都是由強弱利害分是非,以勢和力分優劣,以此為天演之公理,則中國人久有而深信的觀念已完全顛翻。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社會上層變得今時不同往昔,社會下層也變得今時不同往昔,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裡說,劉半農有個黃包車伕,當年曾是義和團,此日(二十年代)已變成一個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從打洋教變為信洋教,他說是因為他們的菩薩厲害,我們的菩薩不行。二十多年之間歷史劇變,有此戊戌變法和十年新政為前史,而後有新文化運動的大幅度反傳統和大幅度西化。以先後而論,三者雖然分屬不同的歷史階段,但就文化趨向而言,則其前後相承,都是在以中國的西方化回應西人的衝擊。然而年復一年,西化猶未成模樣,中體所守定的文化本位已面目全非而無所託身。以這一段歷史為反襯釋讀陳寅恪先生所說的“不古不今”,正說明他既真知近代中國變古的合理,又深知變古的不能沒有限度。因此以“不今”對“不古”,表達的正是對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以來這個過程衝擊中國文化本位的不能認同。
陳先生生於1890年,離咸豐同治之交相差三十年,所以他的“不古不今”實際上是後人對前一段歷史的反思。與這種反思相伴的心路,他說自己“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以開新(變法)的王安石與守舊的司馬光為比,陳說自己少年和晚年的識度不同,心境不同。這種變化是觀察世變造成的。戊戌變法後數十年,他作“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追溯數十年以來的新舊之變,概而論之說“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一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退化論之說者”。這個過程與天演進化之公理導引下的全變、大變、速變俱來,而所得則不見進化而見“退化”。顯見得當進化論籠罩中國思想界的時候,他似乎很少受進化論的影響。作為對比,他又在同一個題目下追述戊戌年間其“先世”參與變法,而歸之於以“歷驗世務”為本,並以其“先祖”和“先君”之與郭嵩燾相近,說此中的源流相承,以見“歷驗世務”猶是沿借法自強那一脈演化而來,然後以此與“南海康先生”之借“今文公羊,附會孔子改制”相比而見的路數“本自不同”,以說明“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這種區分說的是以源頭而論,前者仍然未出咸豐同治那一代士大夫取新衛舊的宗旨和範圍,立意並不在大變、速變、全變。五十年之後申論當日的“不同之二源”,其著力辨析的,是“歷驗世務”那一路猶在中體西用之中,而“附會孔子改制”的一路則一旦啟端便已無分體用之界。因此,六十年代吳宓到廣州見他,之後在日記中說:寅恪兄仍然堅持一貫主張中體西用,並特為註明:(中國本位文化)。以這種“一貫主張”詮說“不古不今”,則具見“不古不今”所守定的,正是中國本位文化。而“咸豐同治”和“湘鄉南皮”之能夠與之相近相須,也在於兩者作為古今之變中的歷史階段和歷史人物,都猶未失其中國本位文化。
但這種對於數十年文化遷流的反思,以直觀而見,便成了身在二十世紀的人懷念十九世紀。所以和他同處一個時代而年輩稍輕的文化人,遂有稱他為遺少、遺老者,客氣一點的把他比作伯夷叔齊,不客氣的說他是“殷之頑民”。但這種由直觀而得的判斷,又因其止於直觀而不能體會他內在的那種中體西用的本來含義,以及這種含義中的歷史內容。由此反照的,正是抽象的進步主義籠罩之下,今人眼中新舊之界的太過明瞭和絕對。
我讀這段話有體會,也有感慨,概而言之,一、以中國本位為舊,則今日的中國本由歷史中國而來,守舊並非全然無道理。而身當古今中西交衝之間,中國意識和中國本位又總是與傳統長相依存而無從切割的。二、二十世紀之後,守舊比開新更難。因此新舊之界的太過明瞭和絕對,更容易顯示的,常常是新舊之界更容易淹沒中國意識。
二
第二段話,陳寅恪先生說“天水一朝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而“吾國學術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獲新宋學之建立是已”。
宋學之名與漢學相對而見,其實又主要是與清學相對而見。十八世紀後期和十九世紀前期,乾嘉之學如日中天,相映而反照的正是宋學的衰落。當這個時代過去之後,盛世日去日遠而四海變秋氣,宋學曾隨嘉道之際經世之學的浡興而重起。但其氣象猶未廓然大張,西學已在時勢亟變中倒灌而入。之後的中西交衝裡,與不涉安身立命的樸(清)學相比,以安身立命為大題目的宋學與西學之扞格更深,因此受到西學直接摧鋤的仍然是宋學。
陳寅恪先生深通清學的治學方法,並用之於自己的研究之中,因此他在一個宋學非常衰微的時期裡推崇宋學,便尤其引人注目。由於宋學之名與清學(漢學)相對而見,所以他在二十世紀講宋學,便一定會與清學映照,從而一定要同清學比較。其間尤被舉為兩相歧異的是,“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但史學則遠不逮宋人”。而沒有史學的經學,則既沒有整體性,也沒有確定性,遂成其“以謹願之人而治經學,但能依文句各別解釋,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以夸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斷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之殘缺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徵之結論,而其論既出之後,固不能犁然有當於心,而人亦不能標舉反證以相詰難”。因此“其謹願者止於解釋文句,而不能討論問題;其夸誕者又流於奇詭悠謬,而不可究詰”的各成偏失。
前一種毛病更多的可能牽及古文經學,後一種毛病更多的可能牽及今文經學。但這種有毛病的清學,在西學傳入,又直接促成和化生為中國的新學之後,則其以實證為長技的特點,卻能夠非常自然地融入於實驗主義派生的所謂科學方法,以及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名目之下,成為其中一部分。新文化風動天下之日蔡元培說胡適,尤以“適之先生出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所以他有漢學的遺傳性”為優長。他以一種非常真誠的推重寫照了清學之容易為新學收納,而後借得科學之名的事實。但在陳寅恪先生的意中,這種清學(漢學)化了的科學和科學化了的清學其實並不足以維繫和傳承其心目中的中國文化。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他評說當日的學界風趨說:“今日吾國治學之士,競言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夸誕經學家之所為者。”又說“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並概括而言之曰“此今日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之狀況”。
漢學和宋學相比,前者重知識,後者重義理,從而前者重文義,後者重意義;前者重小題目(訓詁音韻,辨偽輯佚),後者重大題目(天理人慾,安身立命),而知識的背後沒有義理、沒有意義、沒有大題目,則知識之所見和知識之所得,都以各成片斷而不能入人之心為當然。清代的漢學之被看成是餖飣瑣碎正在於此。曾國藩舉其極端而言,說是“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結果便不能不成為“一種破碎之學”。破碎之學,說的正是見不到整體也見不到內涵。以此為對照,則陳寅恪論宋學,著眼的是“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論,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力,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近之淳正”,並由此起講,而歸於“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說的都是因內涵而有整體,而後義理入人之心,文化成為民族的骨架,因此,被看成是空文的義理其實於人世尤其切近。作為實證,梁啟超曾舉數十年治學以持論貶抑宋學為常態的戴震,臨死之日自謂:“平生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養心正言其能夠安身立命。他最終承認有沒有義理是不一樣的。這兩節文字都說明,對於中國文化來說,義理比知識更內在。以此通觀清代二百多年漢學與宋學的盛衰消長,俱見二百多年留給近代中國的正是義理的稀薄。義理稀薄,則內無所立,從而內無所守。中西交衝之日便容易跟著走。所以時至民初,梅光迪說中國只經過一代人,便從極端的保守成了極端的激進。“以至於如今在中國的教育、政治和思想論域扮演著主角的知識分子們,他們已經完全西化,對自己的精神家園缺乏起碼的理解和熱愛。因而在國內他們反而成了外國人。”羅家倫說近代中國人太輕信,本來相信的是天圓地方,但日心說一進來就很快接受了,本來相信的是盤古開天地,但進化論一進來馬上就相信人是猴子變來的。他說:日心說、進化論在西方從產生到被大家接受,要經過多少艱苦挫折,中間還有流血犧牲的事情。但中國人太容易接受。由於容易接受,所以也容易拋棄。毛澤東說,今之時流,多沒有本源,遂既無內省之明,又無外觀之識。然後以“大本大源”相度量,而“獨服曾文正”。他和羅家倫、梅光迪指述的是同一種世相,但比之羅家倫說的太輕信和梅光迪說的太極端,則其意中的大本大源,已更深刻地觸及了二百多年知識淹沒義理、文義淹沒意義、小題目淹沒大題目之後的內無所立,因此內無所守。輕信和極端正由此衍生而來。
對於陳寅恪先生來說,身在二十世紀的文化遷流之中,他所尤重的始終是中國文化的“本根”。其念茲在茲而不能不去懷的是“文化神州”、“禹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文化中的“別有超越時間空間之理性”,和“救國經世,尤必有精神之學問為根基”等等,關注的都是中國歷史所形成的中國人的精神本源。其意中的文化不僅是一種研究的物件,而且是應當進入其中和能夠進入其中的精神世界,因此以旨要而論,顯然切近的是宋學,不會是漢學。他曾借佛教經典“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為譬,闡說宋學生成的源遠流長,以為“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所以,以長遠而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譬諸冬季之樹林,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又可庇廕百十人矣”。他說的是因為有新儒學,所以才有宋學。這裡的“新儒學”與中國文化相對應,應當比一般的儒學涵義更廣。是以新儒學之歷經變遷傳衍的過程,其實是中國歷史在脈延中生成了中國文化主幹的過程。因此,陳寅恪先生在宋學衰頹之後的期望宋學復興和相信宋學復興,正是時逢古今中西交爭致文化本位搖動之日,期望和相信重建中國文化之主幹的可能。
然而以“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說新儒學的由來和形成,則他既識得思想本在變遷之中,就立意而言,他期望宋學的復興,同時又是深知宋學的復興不會是宋學的迴歸。他曾舉韓愈《原道》一文借禪宗直指人心,見心成佛之旨,重釋《禮記》中《大學》一篇,使抽象之心性和儒學的治國平天下道理融為一體,開宋代新儒學治經之先河。又說,“道教對於輸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無不盡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說以後,則堅持夷夏之辨,以排斥外來之教義。此種思想上之態度,自六朝時亦已如此”,後來“新儒家即繼承此種遺業而能成其大者”。以此詮釋“演變歷程”的“至繁至久”,顯見得儒學之演化為新儒學,是中國文化吸收匯融了外來文化的結果。而新儒學之仍是儒學,則是吸收匯融的過程中內有所守,以民族本位為自我意識的結果。所以他期望中的宋代文化的復興,是一種“新宋學之建立”。新宋學與宋學相為淵源,但二十世紀的中國,既已歷經百年古今中西交爭和交通,以及與之相隨而來的外來化為內在,則經此歷史變遷這個過程,中國文化的歷史內容中又已融入了古所未有的時代內容。這個過程重現了千年之前的“輸入”和“吸收”,也使傳承歷史的中國文化同時又在回應當下的時代。所以,他期望中的新宋學一定會越出“天水一朝”的規模而為中國文化別開生面。而新宋學與宋學的一脈相承,全在於這種新宋學能夠為歷經變遷的中國提供恆定於變遷之中的價值、義理、大問題,而這種價值、義理和大問題之所以恆定,都在於它們是由中國生成,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因此貫通而論,他心中的不古不今和中體西用,立意應俱在於此。
三
第三段話,陳先生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段話最初用之以寫照王國維先生的學人品格,後來陳寅恪先生又多次提及,以表達他心中的一種文化價值。外在地看,以此立言,有點像西方自由主義。但在陳先生那裡,則兩者都自內而生,出身本土,他稱之為“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用之以說歷史,以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自由,文章亦上乘”。因此,其本意中的獨立自由更多地是中國既有的,是與中國人的歷史文化連在一起的。
獨立、自由之成為一種文化品格,對應於“士之讀書治學,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的個體自立。俗諦本是佛教用語,與真諦相對,引申而及,又泛指世間眾人識見的止於淺表而不能俱足。所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要義,實際上是以自求真知的個體知識人同多數和世俗之間的自覺區別和分立。過去的兩千多年歲月裡也有世俗,也有多數,但兩千多年裡並未見有觸發學人的這種與世俗與多數相對而立的自覺意識。以今比昔,則過去文化的主導有一種以儒學為範圍的大體統一,同時是文化的主導者和文化的受眾之間界限分明,等序分明,主動與被動也分明。因此俗諦雖是多數,而不足以顛翻這種界限和等序,駕文化主導者那一面而上之。但時至二十世紀初年,這種界限、等序以及主動與被動的格局都已變得模糊。與他所說“時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的激盪”相對應的,一面是新式學堂已經培養出來和正在培養出來的成千上萬不同於傳統士人的新知識人,有如舒新城所說的“以工廠整批生產的方式”大量製造出來;另一方面是外來的知識、學理源源不絕地湧入,又以其源源不絕的後浪逐前浪而無從深化和固化,遂使知識衍化為思想,思想派生出議論。人不同,識也不同,而滔滔然自為論說則天下皆是。然後是成千上萬的新知識人,以知識、思想、議論為鼓盪,構成當時和後來稱為“潮流”的時趨。與之俱來的則是思想和學理的潮來潮去。我想,寅恪先生眼中的“俗諦”所對應的,大半正是這種學界的沒有靜氣。
潮流與俗諦相錯雜,帶來的是一種古來所未有的世相。潘光旦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分別寫過以潮流為題目的文章。他說常聽人講潮流,並且要順應潮流,尤其在思想界裡,好像真有一派浩浩蕩蕩的東西在那裡走動似的。又說,實際觀察山澗的激流,則既可以見到樹葉、草根、落花的隨水流而走;也可以見到水中的巨石、大樹之老根的不移不動;還會見到山澗中的魚,能順流而遊,也能逆流而遊。然後概而論之說:以此為比較,那麼人世間、社會上、思想界,如果真有潮流一樣的現象,則潮流中人也不過如此:一是不管潮流的方向目的,總是跟著走,如同飄落水上的殘花落葉;二是不管潮流來去而始終不改不變,就像浸在山澗中的巨石、老根;三是面對潮流能作自我選擇的少數有見識的人,他們與水流中的魚相彷彿,不會捲入漩渦遭滅頂之災。他區分潮流中的各成一類,說的其實都是知識人;並且以三種類比說明:潮流之為物,本來無可名狀,而時當順應潮流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則個體的知識人遂已不知不覺地存在於群體的潮流之中,而潮流則成了裹挾多數的東西。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潮流一詞的蓬蓬然而起,應當與天演進化之公理那一類觀念淵源相接(嚴復早年以西法說天演,謂之“世道必進,後勝於今”,而後遂有潮流之後勝於前的了無止境,迨其晚年雖已思想大變,而當初留下的影響則既深且遠),並由此派生而來的。與此相為因果而同出於一個源頭的,又是這種由順應而進入潮流的多數,大半並不關注方向目的,雖然他們自以為在各作表達,其實既是被動的又是盲目的。與兩千年曆史中士人的存在本以個體存在為常態相比較,此日順應之下的多數合為潮流和潮流匯為群鳴,便成了陳先生筆下不得不認真面對的俗諦。而與兩千年曆史中的俗諦相比,此日的俗諦之不能不認真面對,並與之分界,是因為身在潮流之中,便是身在四面牽引而不由自主之中。二十世紀初年志士倡反滿革命,但其間的力行者又常常兼奉無政府主義,而後是前一面的民族主義與後一面的世界主義雖宗旨全然相悖,卻能夠一體共存而無窒無礙。與這種名與實不能相合的矛盾同生於那個時代的,還有以學問負眾望的章太炎為外國人的信口開河所惑,曾一度真信中國人種西來說,而一時失其辨識的準頭;章太炎之外,又有喜歡引新知識校正舊道理的梁啟超先以公德、私德、新道德、舊道德之分立名目自為創說,之後又自己否定自己,以為道德無分新舊、公私,歸根結底只有一種良心的前後多變而自相翻覆。這種名與實不能相合、失其準頭和前後翻覆,都具體地寫照了四面牽引之下的不由自主裡,俗諦之容易淹沒個體之識力的事實。以此為反照,並由此作詮釋,則後人可以比較容易地理解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要義正是時處西來的知識衍化為思想,思想衍化為議論之日,以自立判識為本而不肯跟著走的自覺意識。
他所說的俗諦起於古今中西交爭之日,而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在俗諦與潮流相錯雜的背後,並與之一路同來的,還有文化的世俗化、大眾化、商業化。由此形成的文化遷流在空間上更廣延,時間上更長久,但潮來潮去之間,更難見到持久不變的恆常和定向。這個過程之不容易自覺生成中國文化的本位意識,今日已看得尤其瞭然分明。因此,以此釋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則顯然是獨立和自由只能從個體開始,又依個體存在。自一面而言,個體因獨立、自由而構成了與多數的人眾相區隔,並外觀地現顯出一種精神上的貴族氣;自另一面而言,則時當文化遷流無定的時候,這種獨立和自由在陳寅恪先生的意中不會是沒有具體涵義的抽象觀念,其中的要旨和內容都應當與中國文化的本位意識重疊交集。所以獨立和自由之歸之於個體,同時是文化的承擔歸之於個體。他論及唐代宗教,說一代文化有託命之人;以長詩追懷王國維,又有文化神州與文化個體相為依存的言之慨然。沿此同一種理路,後來吳宓稱陳寅恪一身系中國文化。抉其本來的涵義,說的都是中國文化本位之延續,只能是在文化人物的自覺承當中實現的。若通觀兩千年中國文化的歷史演進,並以其間的關節點皆因人物的前後承接而得以實現的一代與一代不同,又一代與一代一脈相沿而言,則這種獨立、自由、承擔,以及文化的託命之人和系文化於一身之人,對應的都是每一代文化各有其代表人物的事實,而陳寅恪先生身處古今中西交爭之際的於此耿耿於心而不能去懷,用意應當都在於此。但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立於潮流來去的學界之中,與之相伴隨的又常常會是一種孤獨。所以他既自述“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又自述“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而迫於時勢,噤不得發”,同時以詩抒懷,則有“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的深度感慨。其學人的倔強和愴涼都是非常明顯的。
這是我就自己的讀史所得對陳寅恪先生三段話的一點理解,不一定準確,也不一定全面,只能算是一種淺見和私見。謝謝大家。
本文為作者2019年10月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聯合主辦的“陳寅恪先生逝世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裘陳江記錄。2021年8月校定。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