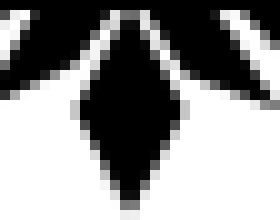話劇《寒梅》劇照 資料圖片
最新版本的《寒梅》(編劇羅懷臻,導演韓劍英)延續了羅懷臻戲劇構思的一貫風格,戲劇性更加強烈,藝術風格慷慨簡勁,讓人穿過歷史感受到柳枝新發的現代氣息。
懸念與衝突,始終在高位上執行,是淮劇《寒梅》最突出的特徵。為人妻也將為人母的寒梅,在那樣嚴酷慘烈的環境中,是什麼支撐著她堅持鬥爭?一方面,同志的慘烈犧牲和自己唯一僥倖得存,不單加深了寒梅對敵人的仇恨,也承載了她必須堅持鬥爭、為同志報仇的責任感。另一方面,她肚子裡有孩子,為人母而欲留之,為人妻而恥於再跟叛徒丈夫李炳輝有什麼關係。在此情形下,對信仰的堅守變得十分具體。
刑場劫後餘生,是現實劫難;得知丈夫叛變,上山遭鄉親們誤會,是精神塌方。寒梅吃了那麼多苦,憑什麼還在堅持?憑什麼還不惜冒著自己犧牲、肚中孩子流產的風險上山?因為對敵人的仇恨、對同志的責任和對孩子的愛。她毅然選擇冒死示警游擊隊,而恰恰是示警游擊隊的過程,才能保全隊伍,更好地進行對敵鬥爭,才能解脫她無處可遁的心結——這生不逢時的苦命孩子,還沒出生就有了一個叛徒父親,作為母親的寒梅能做什麼?想做什麼?她縱然是死,也是一定要給孩子做點什麼的。她不惜冒流產風險上山,也透露出了一個難以言明、痛徹心扉的決斷,即,若不能成功示警而對革命造成損失,她自覺揹負的罪責、孩子身後的汙點再也無法開釋和洗刷,她願意帶著肚中的孩子一起為命運的尊嚴和榮譽而抗爭。這種深入個體靈魂深處的考問和考驗,跟人物堅持革命鬥爭的情節結合,很好地體現出人物內心的複雜和堅持信仰的不易。
這些情節無論是文字還是表演和導演處理,都強烈集中地反映了寒梅的身心處境。特別是飾演寒梅的邢娜,幾乎貫穿全場的、高飽和度的演唱,迷茫、猶豫、憤怒、柔情、堅定,不同的情緒與心境,像烈酒,帶著淮劇的不同調式,酣暢淋漓地表達出來,從而深深地感染了觀眾。
這突出地表現在她和陸曉龍飾演的李炳輝之間的戲中。比如,第二場與丈夫李炳輝重逢時,她是悲情中帶著迷惘的,所有黨員都犧牲了,唯獨丈夫沒在其列,她多麼不想得出丈夫就是叛徒的結論,但那頂熟悉的斗笠告訴她,丈夫沒死,可他在哪裡?他是生是死?他會是志士、烈士還是叛徒?想而不敢想,便轉託為夢,舞臺佈景開合之間,相見舍離,終又成醒後赫然灼目的一頂斗笠,讓人驚心,讓人迷惘,讓人如面對深淵。待見到丈夫,她帶著僥倖也帶著冷靜,一步一步引李炳輝說出真相。原本李炳輝還居高臨下,把她視作嫁雞隨雞的鄉下婦女,請她體諒,勸她出走,她一個大耳光過去,李炳輝當即跪下,主客轉移,變成了她對叛徒的正義審判。後者對妻兒並非完全沒有情感,但當這些威脅到他的自私謀劃時,他便不惜向妻子舉槍、向二秀舉槍。到第五場兩人充滿懸念的、不同時空並進上山的過程中,又一個李炳輝的夢境,既與前夢呼應對比,也對應寒梅臨盆、孩子將要揹負歷史包袱,從而形成了兩人懸念疊加、情緒跌宕的二重唱。
導演的時空排程以及包括紅綢、斗笠、夢境等的使用,也鮮明確立了整個舞臺的寫意風格。紅綢表達的壯烈慷慨,是意象性的;斗笠擰結的前後情節,是懸念式的;兩個夢境前後呼應勾連起寒梅和李炳輝不同的心境,是人性與靈魂的直呈,而所有這些,既是導演的獨特創造,也是二度創作對這部戲兩個人、兩條線的張力結構深刻理解後的具體外化——在人性的考問面前,一個巍巍英姿,一個卑微匍匐。這是淮劇《寒梅》經創新而轉化的厚重深刻之處。
在舞美設計上,幾塊佈景拆分聚合,排程出了夢境與現實、室內與室外、關卡與層巒疊嶂的不同空間,也是洗練明快的。比較遺憾的地方,是對寒梅上山的動機解釋還不夠清晰,從而使得本可大做文章、深度開掘的空間,沒有全面開啟。因為她已懷孕,且有人可以代為上山,那麼,她的理由一定是要超越自己與孩子的生死。在劇中能承載如此分量的,只有對同志生死的責任以及她靈魂深處需要開解的心結。
為了信仰慷慨赴死,淮劇《寒梅》用這樣一個充滿戲劇張力的敘事表達和酣暢寫意的新穎樣式,演繹了一段歷史真實,也詮釋了愛與信仰的同構本質。信仰和初心,本來就是因為愛,因為愛著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
(作者:鄭榮健,系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