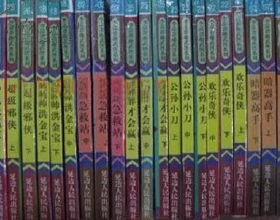讀過古龍的人,就會熟悉李尋歡、阿飛和荊無命。可惜先生英年早逝,一定還有很多關於他們的故事沒能講完。這個短篇,十多年前發在起點中文網。這是我用自己的方式,向古龍先生致敬。
(一)
暗夜,夜已深。
官道。沒有光亮,無星,無月。有兩人默默趕路,一人自東往西,一人自西往東。
他們走的並不快。別人走路會覺得累,而對他們,走路卻是難得的休息和放鬆。兩人就這樣不緊不慢地走。
相距十餘丈時,兩人幾乎同時停住腳步,站定,誰也沒動。他們幾乎同時嗅到了危險。
暗夜裡突然瀰漫著若有若無的殺氣。這殺氣彷彿鎮懾得秋蟲瑟瑟發抖全體噤聲,——官道變的墳墓般寂靜。
兩人表情都很鎮定,手都很穩定,甚至連指尖都無絲毫顫動。兩雙眼睛凝注前方。一雙呈奇異的死灰色,它漠視一切生命,包括自己的;另一雙亮若晨星,帶著一絲淡淡的憂傷。
兩雙眼睛對峙著,沒有語言,也沒有動作。
起霧了。
霧色又漸漸散去,天將破曉。
晨光裡可以看清,東來那人身著黃衣,服色已很破舊,下襬齊膝,腰帶上斜插一柄劍,短,薄,輕;西來那人穿灰衣,舊,漿洗得很乾淨,腰帶上斜插一根木棍,一頭削尖,是用普通的白楊木削就的。
黃衣人忽然開口道:“你?”語氣生澀——他不習慣用語言表達思想,而是用劍。
灰衣人道:“是我。”又一笑道:“你早知是我,對麼?”
黃衣人道:“你也早知是我,對麼?”
灰衣人道:“是。”
沉默。沉默。
灰衣人忽嘆道:“我們已有多年未見了。”
黃衣人沉默著,道:“是。”
灰衣人道:“你是我的敵人。”
黃衣人的瞳孔驟然收縮,右手慢慢扶上劍柄。
灰衣人眼都不眨,淡淡道:“但我們也是朋友,好像一直是。”
黃衣人冷漠的眼睛慢慢掠過一絲寂寞之色,而寂寞裡竟似透出兩分暖意。
他仍閉著嘴,手卻慢慢離開劍柄。
他似乎這才注意到灰衣人腰間的木棍,道:“你已不用劍?”
灰衣人低頭瞧瞧木棍,道:“但它同樣是武器。”
黃衣人道:“多年前我已說過,能殺人的就是利器!”
灰衣人笑了:“的確如此,能懂這道理的人並不多。”
黃衣人傲然道:“的確不多。”
灰衣人又笑了:“可惜這棍子已多年未殺過人。”
黃衣人瞭解。他們本就是同一類人,這世上已幾乎無人值得他出手!
“我已漸漸學會用它救人。”
黃衣人並不驚訝,道:“我見過葉開,也見過他的飛刀。他的飛刀不是殺人,是救人。”
灰衣人有幾分詫異:“哦?”
——葉開是小李飛刀的傳人,俠名滿播江湖,出手一刀,已不在昔年小李探花之下。
灰衣人緩緩道:“半年前,江南出現了一個可怕的無命劍手,瘋狂冷血,見人就殺。目下葉開已在江南。”
黃衣人面無表情,道:“我見過他。他出手的確很快,甚至比你我都快。”
灰衣人目光閃動,道:“你與他交過手?”
黃衣人道:“我還活著。”
灰衣人聳然動容:“你已殺了他?”
黃衣人閉上嘴——他本就是個沉默的人。
良久,他道:“近年來我學會了一件事,那就是隻殺想殺我的人。”他的眼神依舊冷酷堅定。
灰衣人看著,眼裡慢慢露出欣慰、歡喜之色。“我忽然想喝酒,你肯陪我一杯麼?”
黃衣人道:“你知我從不飲酒。”
灰衣人微笑道:“我們是朋友,這要求過分麼?”
黃衣人道:“也許。我甚至不知酒是何物,但我陪你。”
他又道:“你的口氣越來越象他了。”
灰衣人嘆道:“也許······”
(二)
酒樓。
酒樓生意很好,幾乎座無虛席。
臨窗的桌邊坐著一箇中年人,面容還算英俊,兩鬢略有白霜,但眼睛很亮,很年輕,眼神甚至比嬰兒更純淨。
他桌上擺著幾樣精緻的小菜和一壺酒。
奇怪的是,他明明只有一個人,卻放了四副杯筷。
臨桌擠著一群鏢師,大碗喝酒,正談論他們刀頭舐血的經歷,聲音大得惟恐別人聽不到。
忽然,語聲壓低了——
“大哥,想動那批紅貨的人都已退了。”
“他們跟蹤我們已有三天,志在必得,為何······”
“我也奇怪,本來昨晚他們就該出手的。”
“······而我們······絕不是對手。”
“老四,說什麼喪氣話!放著總鏢頭在這兒......”
“住口!”
那蒼老的總鏢頭低低喝道,“那幾人若聯手攻擊,放眼江湖,幾乎無人能對付。”
“我不信!”
“不信就得死!”
那聲音顯然不服氣,卻不敢再開口。
那總鏢頭緩緩自懷裡掏出一件物事,雙手捧著,恭謹地放到桌上,嘆道:“是它救了我們,也保住了鏢局的名聲。”
——這是一柄很薄很輕的刀,三寸七分,飛刀!
眾人屏住呼吸,看著他近乎膜拜神祗的眼睛。
有人試探問:“小李飛刀?”
“是,就是它。”
“都過來,跪下。”
不顧酒客們驚詫的神色,他老淚縱橫,頭觸樓板,咚咚作響:“李探花,我知您老人家就在附近,未敢相擾。大恩大德,戴橫沒齒難忘,來世做牛做馬,結草銜環,亦必相報。”
這毫不起眼的老者,竟是名動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龍威鏢局總鏢頭戴橫!
戴橫十六歲入行,從趟子手幹到總鏢頭,一生走過無數趟鏢,大小身經數百戰,從未失手。龍威鏢局的聲望如日中天,戴橫更是江湖公認的高手,豈是徒有虛名之輩?今日竟當眾失態,卻是為何?
眾酒客議論紛紛,卻儘量壓低聲音。若不小心說錯話,龍威鏢局誰得罪得起?
誰也沒有注意,臨窗而坐的那中年人輕輕嘆息。他臉上仍掛著平淡的笑容,眼裡卻流露出莫名的哀傷之色。
戴橫帶他的兄弟走了,下樓時似有意似無意深深瞧了那中年人一眼······
(三)
黃衣人和灰衣人一前一後,慢慢走上酒樓。
灰衣人在前,黃衣人在後。
灰衣人看到那中年人,目中透出暖意,微笑道:“你來了。”
中年人微笑道:“我來了。”
黃衣人看看桌上的刀,再看看那中年人,眼裡突然迸出灼熱的光芒,但這光芒隨即又黯淡下來。
中年人靜靜瞧著他,似乎一點也不意外,道:“多年不見,別來無恙?”
黃衣人的身體挺立如長槍,緊閉著嘴。
中年人道:“葉開本不該去江南,但畢竟還是去了。”
這話別人不懂,但黃衣人和灰衣人懂。
中年人道:“你既活著,那無名劍手想必已死了。”
黃衣人道:“他沒死。”
中年人靜靜聽著,因為他知道這話沒說完。
果然黃衣人道:“我沒殺他,但摧毀了他的信心,他這一生再也不能殺人了。”
中年人開始驚詫了:“你沒殺他?”
黃衣人蕭然道:“我覺得我也該學會一件事,寬恕。”
中年人望著他,彷彿不認識這個人,忽然笑笑:“坐,請坐。”
黃衣人果真走過去,在中年人對面慢慢坐下,身體仍如長槍般挺直,——他以前絕不肯坐的。
他瞄了眼空著的杯筷,沒說話。
中年人笑道:“你變了。”
灰衣人也笑了:“時間會改變一個人的,不管這人以前什麼樣……戴橫為何如此?”
中年人方才的哀傷之意更濃,緩緩道:“當一樣東西被奉為神聖供人頂禮膜拜,你不覺得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嗎?”
他提起酒壺為兩人斟酒,手依舊穩定,穩定得彷彿凝固在空氣中。
黃衣人扶著酒杯的手彷彿動了動,但酒仍齊沿而止,一滴也未濺出。他長吸一口氣,道:“佩服。”然後很快喝了這杯酒,道:“告辭。”轉身走了。
灰衣人望著他孤傲倔強的背影,中年人若有所思,但都沒有說話。
良久,灰衣人道:“還有人來?”
中年人道:“此人已在此地,既不願相見,我們便該走了。”
灰衣人道:“呂鳳先?”
中年人慢慢轉頭,瞧向右側角落,那裡悄無聲息坐著一個白衣人。
白衣人也正抬眼望向這邊。他年紀已不輕,面容有幾分憔悴,但依然冷漠高傲,瞧著中年人的眸子也似有一絲溫暖之意。他盯著中年人,舉舉手中杯,一飲而盡,起身蕭然離去。
(四)
葉開!
葉開上樓了。
陰魂不散的葉開!
他的笑容依舊燦爛,依舊開朗。
灰衣人和中年人淡淡瞧著他,沒有說話。
葉開除向兩人問好,也沒有多餘的言語。
灰衣人忽道:“我在樓下等你。你們之間,肯定有很多話要說。”
中年人淡淡道:“好。”
葉開的笑容更燦爛,跟往常一樣,也更加開朗。
但這笑容突然變得難以言說的詭異、邪惡。
他的手一動,三寸七分的飛刀已釘在桌上。
刀鋒泛著清冷的光,彷彿早就釘在那裡,連一絲顫動都沒有。
中年人道:“好刀。你殺了他?”
葉開傲然道:“不錯,我用的是小葉飛刀!殺該殺的人,這是你教我的。”
中年人道:“荊無命沒殺他,你卻殺了他?”
葉開的語氣非常堅定:“我用的是小葉飛刀!”
中年人的表情忽然變得非常沉重悲痛,緩緩道:“你不想一輩子活在小李飛刀的陰影裡,我理解。這種超邁前人的勇氣,沒錯。殺該殺的人,那是以前的想法。但現在我不這麼認為。生命是上天賦予人最珍貴的東西,沒有任何人可以用任何理由剝奪它。何況對錯沒有絕對的界限,誰對,誰錯,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回答。”
葉開不解:“您說過,邪不壓正,正義終將戰勝邪惡,所以您能殺了上官金虹。”
中年人道:“你錯了。上官金虹不是我殺的,是他自己殺了自己,只因他認為自己該死。”
葉開更不解:“為何?”
中年人沒直接回答這問題,道:“你知那無名劍手是誰?”
不待作答,他很快道:“他就是教我飛刀的人。”
葉開無語,他本就是心理素質極其穩定的人,否則怎能用無敵的飛刀?不知為何,他額頭突然沁出涔涔冷汗。
中年人道:“你今天來是殺我的,對麼?”
葉開不由道:“你怎知道?”
中年人微微一笑,不再說話。
葉開緊咬著牙,道:“我能殺你!”
中年人憐憫地看著他,還是不說話。
葉開突然喪失了所有的信心和勇氣,人已崩潰,然後重重跪下……
灰衣人站在酒樓對面,冷冷瞧著走出來的葉開。
葉開笑得依舊燦爛,依舊開朗。
灰衣人一字字道:“你一個人出來,就得死!”
葉開眼也不眨,道:“你殺得了我?”
灰衣人腰間的木棍忽然一動,其速度已不能用速度來形容,它將於瞬息間洞穿葉開的咽喉……
然而,它又不可思議地停頓了。
因為他瞧見了慢慢走出酒樓的中年人。
中年人的神情彷彿很疲憊,淡淡道:“讓他走,自己的路自己走,走吧。”
然後,這故事就結束了。
然後,這故事又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