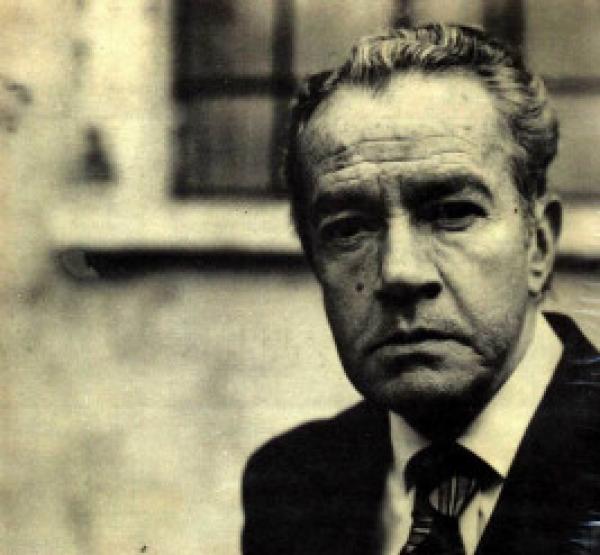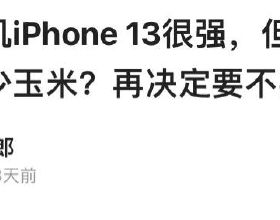北山杉

《燃燒的原野》,[墨西哥] 胡安·魯爾福著,張偉劼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204頁,48.00元
2020年初,遊歷墨西哥的我乘坐從瓜納華託到哈利斯科州的長途汽車,迎面而來的,是受水土侵蝕而成鋸齒狀的山脈和季節性乾涸的河谷,土地袒露,野草稀疏,一支扣著草帽的馬隊噠噠行進,揚起發白塵土。
一年後,魯爾福短篇集將我重又帶回那片灼熱的原野,這一次在文學世界裡去往道路更深處的內陸腹地,看一百年前的村莊如何灰飛煙滅,毀於大火。
走入魯爾福的世界不能不提到1910年爆發的墨西哥革命。它以推翻獨裁政府為起始,歷經十年派系混戰,建立共和國為結束。魯爾福於1917年出生,父母雙方皆來自哈利斯科富有的地主家庭,但家族產業在內戰摧毀殆盡。父親於1923年被槍殺,母親死於革命的餘波——1927年的基督戰爭時期。父母雙亡的魯爾福由奶奶和親戚撫養長大。
這場對魯爾福一生起了重大作用的墨西哥革命,影響還將延綿幾代人。它一方面代表了土地平等的正義訴求,如壁畫運動所展現的那樣,同時也以百萬流血傷亡造成民族創傷。當新政府施展一系列大計方針,從土地、教育到宗教,急於將墨西哥一步推入現代文明社會,墨西哥被擊敗的傳統的鄉土的那部分以強大的慣性裹足不前,與進步的願景再度撕裂。
魯爾福筆下的鄉村便是墨西哥的後一種分身。承受了內戰的巨大破壞後,農民的境遇並沒有因土地改革而變好。《我們分到了地》裡,“我們”名義上分到了整個平原的大片土地,卻是滴水不沾的不毛之地,硬得像牛皮,燙得像餅鐺。對此,負責分地的官員漠不關心。《科馬德雷斯坡》中,土地雖然平分給了農戶,實質卻被豪強的托里柯兄弟控制。敢怒不敢言的鄉親們默默拋棄了耕地,一個個遠走他鄉。
窮山惡水沒有法律,尊奉的還是暴力至上的叢林法則。托里柯殺人搶劫,為霸一方,卻被鄰村更加強大的惡霸打死。暴力一旦開啟,便播下了仇恨的種子。《那個人》便是這樣的冤冤相報。一個“男人”在山上不停趕路,一個“追趕人”在他身後緊緊相隨。追趕人等待男人力盡疲乏走入死路,好對他後腦勺放上一槍,因為那男人深夜殺了自己全家。而男人之所以那天摸黑進了追趕人的家,也是為向追趕人報殺(兄)弟之仇。哪怕男人此刻非常後悔,他已沒有了回頭的路。追與被追,如一條圓環賽道,身份隨時可能互換。故事的後一部分,發現了男人屍體的牧羊人被抓審問,主審的法律人員則是完全隱身的。正義不僅遲到,還會永遠缺席,甚至本來無辜的牧羊人也捲入漩渦。正如《科馬德雷斯坡》勤懇的敘述人最後手上也沾染鮮血。
暴力迴圈是魯爾福作品一個不斷復現的主題。《求他們別殺我!》中,最開始矛盾是土地不均,堂佩盧老爺家牧草青青,胡文西奧的牲畜瀕臨餓死。胡文西奧偷偷開啟護欄放牲畜去吃堂佩盧的牧草,引得堂佩盧勃然大怒,威脅要殺了那些牲口,反被胡文西奧殺死。原本的財產矛盾迅速升級為血仇。堂佩盧的老婆悲傷過度去世,兩個孩子成為孤兒,加重了悲劇。胡文西奧賄賂法官最終也失去了牲畜,此後他像染了瘟疫的人一輩子躲藏。暴力不僅不能解決矛盾,反而讓所有人的境遇變得更糟。胡文西奧在幾十年折磨中償還了自己的罪,但這並不是終結。堂佩盧的兒子長大成為上校,最終取走他性命。
“明知自己賴以生存的東西已經死掉了,還要成長,這的確很難。”(張偉劼譯,譯林2021版,下同)未露面的上校在竹牆後面說道,半是對胡文西奧,半是自白。他怨恨父親的缺位,以恨意滋養求生意志。這份意志必須依附一個更為堅固的實體,於是他將仇恨轉嫁到胡文西奧身上。哪怕此時胡文西奧已衰朽不堪,報仇也必須像使命一樣完成。故事的最後,胡文西奧的兒子將他的屍體放到驢背上馱回了家,那滿是槍眼的畫面繼續傳遞給孫兒,傳給下一代。
由此我們看到魯爾福作品中,與迴圈暴力伴生的另一主題——代際對立。外來西方文化與本土土著文化的結合從一開始就是強制和征服性的,“他不僅把她給馴服了,還從那道口子鑽進她的身體,鑽到很深的地方,讓她給他生了個兒子出來”。從殖民時期,到獨立戰爭,再到墨西哥革命,每一階段的混亂還未平息,便粗暴地被下一個時代的來臨覆蓋。承上啟下的平穩接替並不存在,新的時代弒父而生,一出生便無依無靠。國家命運換位到個人身上,要麼父親已死,成為暴力的藉口,如中篇《佩德羅·巴拉莫》中父親盧卡斯在婚禮中被槍殺,佩德羅·巴拉莫便誓言殺死婚禮所有人報仇。要麼父親形象是暴戾的,胡安·普雷西亞多之所以來到科馬拉千里尋父,便是因了母親臨終的囑託,“他該給我的東西就從來沒給過我……孩子,他早把我們給忘了”(屠孟超譯,譯林2021版)。佩德羅·巴拉莫拋妻棄子,本身即是一位失職的父親。
非但兒子記恨父親,父親也怨恨兒子。《北渡口》中,父親會製作炮仗,只要鎮上儀式慶典不絕就不愁捱餓。但對兒子他堅決不傳手藝,防得像賊。兒子販雞賣豬的生意不濟,向父親託付妻女,借款去美國闖蕩,父親轉手就將兒子的房子賣了抵債,使他從邊境回來人財兩空。映象的對話出現在《安納克萊託·莫羅內斯》,意欲向北逃難的養父向養子索要財產反被打死。《瑪蒂爾德·阿爾坎赫爾的遺產》裡,阿爾坎赫爾被馬撞死,老歐雷米奧便與還是襁褓中的小歐雷米奧結仇。他恨兒子的啼哭驚嚇了馬匹,他恨妻子摔倒時為保護兒子寧願犧牲自己。他神神叨叨說,“錯全在這孩子身上……他對我什麼用也沒有。她要是還活著,準能給我生更多的小孩兒”。
這些俄狄浦斯式對抗是雙向的。父親戒備兒子學會手藝奪走自己的生存權,或是嫉妒兒子分走了對妻子的絕對佔有。猶如敦煌變文裡的《未生怨》,兒子與父親成為敵手,對立關係在出世之前便已決定,他只是被動接受了這種命運,就像胡安·普雷西亞突然被告知自己要去尋找父親。當他像古典英雄踏上自己的征程,追尋註定是徒勞的——父親已於多年前去世。同樣阿爾坎赫爾的死使父與子在對其的競爭中都失敗了。沒有贏家,拮抗和挫敗即是故事本身。魯爾福對父子關係的處理融合了古希臘悲劇與弗洛伊德的現代分析,再融入本土故事。加西亞·馬爾克斯說魯爾福的作品不足三百頁,卻呈現出索福克勒斯般經久的生命力,便有這層道理。
藉由另一篇父子題材,深受君特·格拉斯喜愛的《你聽不到狗叫》,我們再來分析魯爾福的語言風格。該篇幾乎由二人對話組成,除了一些簡短場景動作提示,如薩繆爾·貝克特的舞臺劇。從對話我們得知,殺人越貨的浪蕩子伊格納西奧被父親憎恨詛咒。但當他傷重垂危,父親雖然罵罵咧咧,還是背起他沉重的身軀去託那亞求醫。兒子被父親扛在身上,被月光投出加長的黑影,兩人如連體的怪物,走在尋求救贖的旅程上。視覺風格強烈,同時象徵意味濃烈(另一篇《塔爾葩》也是抽象了的治病朝聖之旅)。故事開頭父親問兒子有沒有聽見聲音,兒子只零星迴答一兩句,看不見,難受。當他們到達村子,力竭的父親靠著柵欄把兒子鬆鬆垮垮地放下來,才因為兒子手指鬆開終於聽到了狗叫,與開篇相應。蘇珊·桑塔格曾援引魯爾福的話說他寫作中充滿寂靜。他沒有使用諸如“夜裡的村子靜得可怕”這類外在描述,有什麼能比當手指鬆開突然四面響起狗叫更能表達村落之前的寂靜呢?
之前提到要理解魯爾福必須將作品放入時代背景,而要賞析魯爾福,寫在紙上的內容和沒寫的同樣重要。第一是因為魯爾福創作短篇小說的高度自覺。他曾在訪談中提到《佩德羅·巴拉莫》之所以能精簡到現在的篇幅,是短篇小說訓練了他的凝練。短篇小說的體裁要求在較短篇幅內呈現一個有完整發展脈絡的故事,類似劇本的一幕。對銀幕時間精打細算的電影編劇知道,精簡劇本的一個技巧是把場景開頭和結尾幾行臺詞刪掉,如昆汀·塔倫蒂諾常做的那樣。觀眾並不需要知道完整的頭尾,當他們被扔進場景中段,自然會根據內容弄懂狀況。魯爾福不僅提前運用了現代編劇的技巧,對自己作品的精練更加嚴苛。《你聽不到狗叫》一開篇你便已置身故事的核心,父子倆已經在路上了,就像開頭可能存在的數段鋪墊——為什麼受傷,為什麼不能在本村治療——已被砍去那樣。當你讀完又會發現,這個故事只有核心。村子到了,聽到狗叫,就結束了。除了場景的剪裁,內容披露同樣儉省。《科馬德雷斯坡》中,“托里柯兄弟不管吃什麼東西都要加石鹽,但吃我的玉米的時候是不加鹽的”,表面說玉米的吃法,實則透露的是,村裡唯一與托里柯兄弟交好的“我”的勞動成果也會被他們霸佔。魯爾福的作品短,但你無法一目十行掃完,需要不斷主動補充被省略的細節,甚至關鍵資訊。“炮仗每響一聲,在我扔掉雷米希奧屍體的那個地方就會飛起一大群兀鷲。”當你從如此精簡的一句話裡展開一群禿鷲啃食托里柯的屍體,隨著遠處鄰村煙花的燃放而不時驚嚇起飛的完整畫面,又會得到莫大腦力互動的享受。
第二則是魯爾福有意識地在作品裡隱去作者的聲音。《佩德羅·巴拉莫》沒有一位全知全能的作者,情節來自十來個角色碎片對話。角色之口也佔據了短篇的主體。大體由對話組成的有《盧維納》等。完全對話組成的二篇。第二人稱一篇。第一人稱八篇。明顯外在敘述者的第三人稱僅兩篇,《清晨》和《那個夜晚,他掉隊了》,各自也有一半對話成分。這些故事呈現的鄉土,有愚昧,有殘暴,也有道德淪喪和荒唐可笑。魯爾福不對它們作價值判斷。佩雷達那樣充沛使用形容詞也為他所不喜。它們不會自文盲口中說出。對話與敘述的一致要求敘述也必然採取說話人平實的語彙。魯爾福的功力也確實能做到,僅透過自然環境和敘述人第一晚的見聞,便能實現陰森的氛圍營造,讓一個堪比科馬拉的偏遠鬼鎮盧維納躍然紙上。
去做一個高高在上的作者與魯爾福天性相違。他對自己的聲音太剋制了。如果不看生平,很難想象《求他們別殺我!》那個因為牧草爭端被殺死的堂佩盧老爺的原型,竟是魯爾福自己的父親。上校一句喃喃自白,已是他允許自己心聲的最大流露。小時候的魯爾福曾親眼見到基督戰爭中死去的人被吊在樹上。殘酷童年記憶落到故事,“他們給吊在馬場中央的一棵牧豆樹上,晃來晃去。從篝火堆上升起的煙模糊了他們失去神采的眼睛,燻黑了他們的臉,而他們對此好像並無知覺”。暴力本身即令人驚駭,平靜反而是最好的語氣。
魯爾福筆調平靜到了抽離的地步。精英領導的墨西哥革命號稱代表農民搶奪地主的土地,魯爾福並未因為自己是被革命一方的地主之子的出身站邊。同名故事《燃燒的原野》裡,起義軍與舊聯邦軍同樣殘暴。全書最接近地獄的圖景,玉米待收時節被點火焚燒,風吹火焰點燃整個平原。放火享受這“壯麗”景象的就是起義軍。革命結束起義軍成為新的政府,與教會之間爆發基督戰爭。說革命是代表人民意願的官方敘事很難將這不得人心的內部分裂容納入內。這種失諧反映到文學上,無論是作為政府職員的魯爾福,還是上過天主教孤兒院和兩年神學院的魯爾福,都沒有因個人處境選擇立場。《那個夜晚,他掉隊了》裡,要是讓基督兵漏網,政府兵準備隨便射殺一個平民充數。《安納克萊託·莫羅內斯》裡基督兵用卡賓槍頂著盧卡斯的背逼他承認沒犯過的罪。兩邊誰都可以成為更惡的一方。末尾兩個詼諧諷刺故事平分給了民間神棍和飯桶州長。
魯爾福在寫作中是沉默的,因為他把話語交給了角色,尤其是廣大農民。機關供職時魯爾福便常遊覽群山,擔任輪胎公司旅行推銷員和汽車雜誌編輯的職務之便給他更多自由周遊全國。這些經歷為他攝影的愛好提供了素材,一方面使他對山川地理尤其是哈利斯科州本鄉有了深入不毛的熟悉,比如《燃燒的原野》的戰場阿爾梅里亞河。旅行帶來更重要的經歷是,魯爾福可以去到鄉村,傾聽那些不會讀書寫字,沉默大多數的農民的聲音。他從他們身上,得知了第一手最真實的鄉土,擴充了比個體見聞更為豐富的經歷。魯爾福寡言少語,但他喜歡傾聽。他聽著老鄉們的故事,留意詞彙和語氣,包括給翻譯家帶來些微麻煩的方言,還帶著十六世紀卡斯蒂利亞語的印跡。這些對當時墨西哥城市居民也十分陌生的語言,被魯爾福藝術性地儲存下來,創造,轉寫,更是還原。
還原不等於保持原材料的粗糲。魯爾福對字句的加工是極謹慎的,比如書名原文的El Llano en llamas,原野的llano和火焰的llama押著頭韻。每次重版富爾福都會對個別字詞再調整,比如1980年版起,Llano轉為大寫,特指哈利斯科州南部的大平原。人物的名字系悉心挑選,比如安納克萊託·莫羅內斯由基督戰爭中兩位死對頭名字各取一半組成,加重諷刺。《那個人》裡男人和追趕人則因角色可能動態互換故意模糊姓名。小說語言做到平白如話,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用詞精確,無一詞突兀或脫離角色,除非他在模仿州長刻意滑稽。加西亞·馬爾克斯提到,若是把《佩德羅·巴拉莫》的時間線改換一種方式,便會凌亂不堪。《科馬德雷斯坡》也是類似,時間線在荒村的現在與村霸的過去之間跳躍,當你試圖變更則會發現每一段都已被固定在它應有的位置。甚至托里柯兄弟與我交好,和托里柯是我殺的,這樣強轉折所留的間隔也恰到分寸。魯爾福的短篇裡你不會感覺有任何東西是隨意放在那裡的。
魯爾福寫最鄉土的故事,但他的手法是現代的,他寫的是毫無疑義的現代小說。他的文學養料,不是十九世紀西班牙傳統文學,而是墨西哥本國曆史,斯堪的納維亞、俄羅斯還有美國的當代文學。一些先鋒性技巧如福克納《喧譁與騷動》的碎片化敘事、時間視角無標記地突然轉換被魯爾福採納並嫻熟運用。魯爾福因戰爭中斷學業,不喜的人攻擊他沒有受過完整大學教育,喜歡的人讚歎他是天賦型選手。雙方都不應忽視的是,魯爾福不僅上過人間這所大學,還從廣博的閱讀中完成了自我教育。作家朋友說,魯爾福幾乎閱讀了當時所有翻譯到西班牙語的文學。受世界文學啟蒙的魯爾福,原創性地將本土文化與現代技法融合,啟發了馬爾克斯等後輩,作為先導者以爆炸的拉丁美洲文學回饋了世界。短篇集《燃燒的原野》在西語文學界的影響力,大概僅次於博爾赫斯的《虛構集》。博爾赫斯本人是這樣評價魯爾福的:他的小說是西班牙語文學中最好的之一,甚至可以說任何語言裡。最優秀的文學超越語言。廣受大師激賞的魯爾福作品中譯再版,來到中國讀者面前,實為我等之幸,可堪重讀和品鑑。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