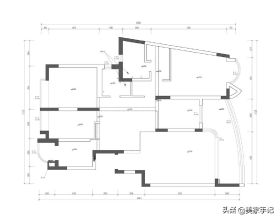作者:思 鬱
什麼才是卡佛式的小說?這個問題好像用一兩句話沒法概括,不如從他的一篇很普通的小說入手,這篇小說叫《你們為什麼不跳個舞》,收錄在《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小說非常簡短,情節也非常普通。一對小情侶走在街上,發現某戶人家很多東西擺在了路邊,進行大甩賣,但是主人好像又不在家。他們去挑了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男主人正好也買了酒回來,就邀請他們喝一杯。夜色降臨,酒意正酣,他們坐在陳舊的沙發上,播放著二手的唱片,嬉笑著,在路邊翩翩起舞。
這其實就是卡佛所寫的眾多短篇小說中很普通的一篇,但卻總是讓我念念不忘,因為情節太簡單了,以至於你總覺得它不像一篇小說,背景是模糊的,情節也是平淡如水,更別說有什麼起承轉合、故事衝突等等,你怎麼讀都覺得它不像一篇完整的小說,它更像一篇支離破碎、粗心大意、隨手寫下的小說素材。
但這樣一篇非常寡淡的短篇小說,總是會讓你不斷回想起來,琢磨其中的意味,比如男主人為什麼會大甩賣,他有什麼樣的故事?他總是喝得醉醺醺的,是因為酗酒才導致的婚姻破裂嗎?那一對小情侶出現在他的房子面前,他邀請他們喝酒,跳舞,坐在沙發上看著他們,心裡想到的是自己的愛人嗎?這些都是需要我們腦補出來的畫面。我覺得,小說最後的一句話真是神來之筆,這件事裡面其實有很多的東西,但就是說不出來,這句話幾乎可以概括卡佛所有小說的特點。
卡佛的小說總是被形容為極簡主義風格,這種風格的塑造與他的這種非常白描化的寫作手法有關,他不斷地削減自己的句子,到最後這種削減已經變成了削減故事、情節、衝突,只留下那些最表面的東西。卡佛的小說總是拿來與海明威比較,但是卡佛與其說繼承了海明威的寫作冰山理論,不如說是繼承發展了它。海明威的寫作理論是,我們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巨大的冰山在水面之下。但是卡佛的寫作剔除了水面之下的冰山,小說中只剩下冰山一角,冰面之下,並無他物存在。這就是那句話形容的,彷彿有很多東西,但其實什麼都沒有。他只用準確的語言描述了生活中的某個片段、某條經驗、某個場景,就如同拍照一樣,鎖定某一瞬間,並且儲存下來。
卡佛的小說,後來的評論家都喜歡用極簡主義來形容,但是卡佛對這個稱呼是非常反感的。在最新的《雷蒙德·卡佛訪談錄》中,凡是有記者追問到對極簡主義的評價時,卡佛都不厭其煩地解釋,他並不贊同這個稱呼。比如他在訪談中說:“我是在努力刪除小說中所有不必要的細節,努力把我的詞語削減到骨頭。但並不能就此稱我為極簡主義者。如果我是,我會真的把它們削減得只剩下骨頭。但我沒有那麼做,我留下了幾片肉。”
極簡主義成為卡佛的標籤是一種束縛,對卡佛來說,用極簡主義概括他的作品是不公平的,因為對一個作家來說,不可能只寫一種風格的作品,他的每一篇小說都應該是獨立的風格。比如他晚期的作品《大教堂》就比之前的小說溫暖和豐富了很多。
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呢?說白了,當評論家用極簡主義形容卡佛小說的時候,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小說風格,但是對卡佛來說,這不是小說風格,不是文學技巧,甚至不是文學,評論家輕飄飄提到的極簡主義,是他的生活,他就是寫了他大半生所經歷的現實。當然,小說從來不單單是複製現實這麼簡單,小說是發展現實。卡佛有條著名的寫作經驗,可能適合很多新手寫作者:一點點自傳性,加上大量的想象力。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事物,但並不能止步於此,要結合你的閱讀和想象,才能創造出有吸引力的場景和人物。卡佛小說都是從自己的生活出發,他的生活陷入悲慘的境遇,比如連一個寫作空間都沒有的時候,他只能寫簡短的東西或者詩歌;當他在晚年逐漸成名,他也有足夠的經濟實力,給自己一份安全保障的時候,他自然會豐富自己的作品,把原來皮包骨頭的小說風格填滿了更加豐富的血肉。
其實我們在閱讀《訪談錄》的時候就會注意到這種變化。首先這本書中收錄的大部分訪談集中在卡佛生活的最後10年,具體來說,第一篇是1977年,那一年卡佛的小說集《請你安靜些,好嗎?》入選了美國國家圖書獎,而且市場反響很好,卡佛開始進入主流文學圈;最後一篇是1988年,卡佛身患肺癌,正在接受化療。那一年的8月,卡佛去世,只有50歲。
在這些集中的訪談中,大多數重複提到了卡佛一生的經歷,因為只有瞭解他的生活,才能真正體會到他的文學。比如他18歲結婚,20歲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大半生做著最底層的工作,當過鋸木工、清潔工、售貨員、送貨員等等,這些工作都只夠為他的家庭付賬單。他熱愛寫作,但是寫作對他而言是非常奢侈的事情,當生存成為問題的時候,寫作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畢竟寫作是閒暇的派生物。但是卡佛依然堅持練習寫作,在杯盤狼藉的餐桌上,在汽車裡,在所有能夠寫作的地方。
在訪談中,他總是反覆提到他生命中的兩個貴人,一個是把他帶入寫作之路的美國作家約翰·加德納。他曾經參加過加德納的創意寫作班,加德納讓卡佛意識到什麼才是好的文學,真正的寫作是需要反覆錘鍊,不斷地改寫的。卡佛生命中的另外一個貴人是編輯戈登·利什,在《巴黎評論》的訪談中,卡佛將其稱為與麥克斯·珀金斯一樣的天才編輯,因為正是透過利什的幫助,他才開始發表作品。
大多數的寫作者經歷過這樣的階段,卡佛早年寫作開始投稿,如果有雜誌能夠接受他的作品,他已經感到很滿足了,從來沒奢望有稿酬。他總是反覆講到一個段子,在1962年的某天,他同時收到了兩本文學雜誌的通知,一本發表了他的一首詩歌,一本發表了他的一篇小說。文學青年卡佛奔走相告,睡覺的時候也不捨得放開手中的雜誌。這就是一個卑微的寫作者,但是當他的朋友利什成為《時尚先生》的編輯,並開始向他約稿的時候,他意識到機會來了。《時尚先生》不但發表名家作品,稿酬也相比普通的文學雜誌高出很多,卡佛的一篇小說稿酬可以拿到600美元,這對於默默無聞的寫作者來說是天價稿酬。
當然,作家與編輯的關係從來沒有這麼簡單過,十幾年後,當卡佛成了短篇小說大師,曾經的編輯和朋友利什不止一次說是他一手塑造了卡佛的極簡主義,因為在出版卡佛小說的時候,利什對他的作品進行了大量的刪減和改寫。很顯然,當時的卡佛並未質疑他的決定,因為出版作品是他最大的心願,以至於他一再容忍編輯對他的作品進行再創作。多年後,卡佛重新出版了那些沒有刪減的作品,我們才意識到,所謂極簡主義對卡佛的定義並不準確。
卡佛一直都生活在最底層,所以他也成了美國底層人民的代言人。在《訪談錄》的最後幾篇中,卡佛不得不面對很多人對他的指責,說他是一個不會書寫美國夢的好作家,因為他筆下的人物都是最底層的美國人,他們酗酒,家暴,失業,婚姻破裂,家庭不幸,沒有工作,四處流浪,做著沒有尊嚴的工作,這就是卡佛筆下最常寫到的人物。
卡佛辯解說,他雖然經常寫工薪階層的人,但他不是有意那樣做的,因為作家只能從自己熟悉的人物開始寫起。他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就是與這些人生活在一起,他只能寫他們,也是寫自己的生活。(思 鬱)
來源: 遼寧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