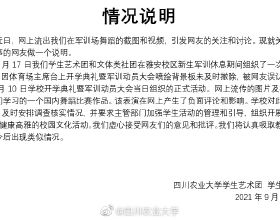長期以來,遵義會議一直是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這次會議舉行期間,中國共產黨已與共產國際中斷聯絡,會議不僅批判了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的軍事指揮錯誤,還取消了他們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增補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並明確他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會後不久,常委會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責的職務。對中央領導機構成員職務的這一系列調整,對於在共產國際指導和幫助下的中國共產黨來說,無疑是自成立14年以來破天荒的大事件。從會議最後作出的決議可以看出,遵義會議是在擁護共產國際大前提下進行的。因此,如何儘快地向共產國際報告會議情況,以爭取到他們的理解和支援,是新的黨中央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
從現已公佈的檔案資料表明,遵義會議後黨中央派去蘇聯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白區工作部部長陳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潘漢年。其中,最先派去的是潘漢年。1935年3月上旬,紅軍第二次攻佔遵義後,張聞天代表黨中央通知潘漢年,要求他立刻趕到白區,準備隨陳雲在上海附近長期潛伏,恢復白區工作,同時設法打聽上海有無共產國際的關係,並指示潘先行一步。同年6月中旬,紅軍過瀘定橋後,陳雲才離開隊伍,從四川天全縣靈關殿輾轉重慶乘輪船到上海。8月間,陳雲與潘漢年接上頭。經共產國際在滬代表安排,潘又先走,陳後離滬。兩人都在9月到達莫斯科。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1936年6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離開延安經新疆前往蘇聯,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1937年7月初,中央政治局委員王稼祥赴莫斯科治傷養病。
陳雲、鄧發、王稼祥都參加了遵義會議,潘漢年未參加會議,但他在紅軍中擔任重要職務。他們在蘇期間與共產國際領導人接觸時,談到遵義會議和長征情況,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迄今為止,正式發表的只有陳雲寫的《(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1935年10月15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因此,現在普遍認為共產國際瞭解遵義會議情況,最早是從陳雲的報告中得知的。
隨著研究工作的深入,不少資料表明,在陳雲等未到達莫斯科前,共產國際已初步掌握和了解了紅軍西征和遵義會議情況。例如:1935年5月1日,蘇聯《布林塞維克》雜誌發表了弗雷德寫的《在中國紅軍的前線》一文,最早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訊息;同年7月3日,蘇聯《真理報》又發表了哈馬丹的《中國紅軍的英勇進軍》。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介紹了紅軍向雲南進軍的情況。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大會主席團主席曼努依斯基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在他們向大會作的報告中,都一致高度評價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紅軍西征。這次大會上,毛澤東還第一次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
紅軍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前,原計劃是準備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當時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通訊聯絡尚未中斷,該計劃向共產國際報告後並經批准。1934年10月上旬,紅軍長征伊始,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到敵人破壞。因此,黨中央也中斷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絡,一直到長征勝利,紅軍抵達陝北後才得到恢復。共產國際“七大”和蘇共中央機關報刊一致肯定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紅軍西征,清楚地說明了共產國際對遵義會議調整中央領導人和正在進行的戰略轉移行動,不僅知道,還基本上認可了。那麼,這些重要情況究竟在什麼時間,透過什麼渠道流傳到共產國際的呢?
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從中央檔案館馬紅寫的《上海臨時中央局概況》一文,得到一個極其重要的資訊。他在文中寫道:“臨時中央局成立以後,透過各種關係恢復與蘇區和白區的聯絡。……在與蘇區的聯絡中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5月底,臨時中央局接到了紅二、六軍團任同志(可能是任弼時同志)的報告和中央關於五次反‘圍剿’總結的決議,任同志並要求上海派幹部到紅二、六軍團去。臨時中央局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提到了這個決議的情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合訂本,第363頁)。馬紅的文章,是根據有關檔案資料綜合整理成文的,文中所述這一重要情節,當然是可信的。文中提到的“中央關於反五次‘圍剿’總結的決議”,即指遵義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由於任弼時沒有參加遵義會議,他在什麼時間得到《決議》的呢?臨時中央局5月底接到任弼時的報告和《決議》後,又在什麼時間向共產國際報告並提到《決議》的情況?
為弄清楚這些問題,首先應瞭解《決議》成文的過程。根據黨史研究多年的成果,認為遵義會議後,張聞天遵照會議決定,在1935年2月7日至2月8日間完成了《決議》的起草工作,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雲南扎西附近召開會議,正式通過了《決議》,這在黨史學界已取得共識。《決議》全文共1.2萬餘字,以那個年代的通訊裝置完全不可能原原本本發往外地。那麼,臨時中央局給共產國際報告中所說的《決議》,又是怎麼回事呢?現有的材料表明,1935年2月10日,《決議》起草人、剛接替博古負總責職務的張聞天,代表黨中央在扎西向軍委縱隊的幹部傳達了《決議》精神,引起極大反響,幹部會一致擁護黨中央遵義會議做出的《決議》。為了儘快擴大傳達範圍,動員和鼓舞紅軍指戰員在戰略轉移中的鬥志,中共中央書記處於2月28日根據《決議》擬定印發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下簡稱《大綱》),專門作為向下傳達《決議》精神的提綱。同日,中央書記處還發出了《中共中央致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及中央軍區電》。我們把該電文和《大綱》內容作了仔細對照,幾乎完全相同,僅個別字稍有出入。根據以上情況,我們基本可以認為,任弼時接到的是黨中央2月28日發給他的電文,理應是《大綱》內容,而不是《決議》。任弼時接電後,立即把《大綱》內容向上海臨時中央局報告。那麼,上海臨時中央局在什麼時間接到任弼時的報告並向共產國際報告的呢?
根據馬紅文章記述,上海臨時中央局自1933年春成立起,它就是黨中央的派出機關,它的任務是代表黨中央領導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中的工作,保持和疏通黨中央與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之間的聯絡。雖然遭到敵人三次大破壞,仍於1935年3月中旬再次恢復了上海臨時中央局。這時黨中央正率領紅軍主力輾轉運動在雲、貴、川邊,根本無法取得聯絡,但與紅四方面軍,紅二、紅六軍團有通訊聯絡。5月底,臨時中央局從任弼時的報告中,得知了黨中央的行蹤和遵義會議《大綱》的內容,這對與黨中央失去聯絡半年多的臨時中央局來說,無疑是件頭等大事,定會盡快向共產國際報告。由於臨時中央局在7月21日又遭敵人破壞,因此,向共產國際報告只能在6月至7月21日期間。
在查閱上海臨時中央局有關檔案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一份中央局機關編印——1935年7月1日付印,7月5日出版的第79期《鬥爭》上,刊登了一篇署名迪克的《中央紅軍西征的意義》文章。全文無不貫穿著遵義會議精神,許多批評“左”傾軍事指揮錯誤的用語,完全與《大綱》提法相同(限於篇幅,在此就不一一引用)。但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迪克在文中論述紅軍為什麼西征時寫道:“……決不是敵人的堡壘主義持久戰,逼迫我們在蘇區範圍以內不能解決敵人,而是軍事領導上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以致我們失去在蘇區範圍以內解決敵人的一切有利條件(關於五次‘圍剿’的軍事路線問題,將來另有檔案或文章的解釋)。”這裡所說的“檔案”,不言而喻是指《決議》了。這段話十分清楚地表明,上海臨時中央局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絡半年多以後,一接到任弼時轉報的以《大綱》為內容的電文,來不及等《決議》下達,即寫文章宣傳紅軍長征及其重大意義;從該期《鬥爭》付印、出版的時間,可以認定文章是在6月份寫成的,《鬥爭》是黨中央的機關刊物,它及時刊登紅軍長征文章,理應不會耽誤時間,因此可以認定中央局在寫文章前或寫文章時,在6月即按任弼時的電文向共產國際作了報告。
綜上所述,遵義會議情況(即《決議》,也就是《大綱》概括的內容)是黨中央於1935年2月28日在貴州遵義附近,按《大綱》內容用電報通告給紅二、六軍團和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駐紅六軍團中央代表兼軍團長的任弼時的。任弼時接電後,又立即把《大綱》原原本本地報告給上海臨時中央局,臨時中央局5月底收到任弼時《大綱》後,在6月(最遲不超過7月21日)即向共產國際報告了《大綱》的內容。應該說,這是共產國際最早得到的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情況,也是至今唯一見到的文字記載。
作者:費侃如 陳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