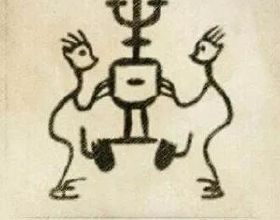天祚帝:千官側目後,落日枕燕雲
歷史上有很多機緣巧合之事,讀來也很是有趣,比如在1101年,就有兩位亡國之君同時上位,而他們卻都在後來的時光中,被同一個曾被他們瞧不起的蕞爾小國打得鼻青臉腫,最後都慘遭亡國之痛,他們一個是北宋的道君皇帝宋徽宗,另一個則是遼國的末代皇帝天祚帝。
國人對宋徽宗是相當熟悉的,一個“靖康之難”,成為大漢民族心中永遠的痛,但對這天祚帝就並不是太瞭解了,因為畢竟是遠離時人的生活,在宋人的眼中,金人打遼人,當屬狗咬狗,與我大宋有何干系?
不僅如此,當時的宋人對遼人佔我燕雲十六州一直是耿耿於懷,收復燕雲亦是歷代宋朝皇帝的一個夢想,有金人幫忙著打,那是求之不得之事,於是,這宋徽宗便派兵從背後狠狠地插了一刀,遼人雪上加霜,終至滅國。
但是,唇亡齒寒,沒過多久,這金兵南下,勢如破竹,將北宋首都汴梁圍困,宋徽宗被擄去北國,同那遼天祚帝關在一起,不知這哥倆兒此時相見,是否悔不當初聯手抗金,此事見於《大宋宣和遺事》記載。
宋、遼俱是大國,契丹人自唐末後,就一直在中原征戰的舞臺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而且還在後晉石敬瑭的手中,取得了包括現在北京在內的燕雲十六州,使得宋朝都城汴梁屏障皆無,直接暴露在北方遊牧民族面前。
自宋太宗發動收復之戰始,十數年的用兵換來的只是慘敗,楊家將中的老令公被俘,絕食而亡;太宗本人屁股中箭,偷驢車狂奔百餘里,大敗虧輸,自此,收復燕雲十六州,便成為北宋歷代皇帝一個想都不敢想的惡夢。
所以,宋朝對這遼人是又恨又怕,但自“澶淵之盟”後,宋王朝花錢買和平,每年向遼人進貢,卻也換來數十年的美好時光,得以全力對付西北那如狗皮膏藥般貼在身上的西夏。
及天祚帝和宋徽宗上位時,無論是宋王朝還是遼國,都在享受著前輩傳下的美好,而趙佶和天祚帝這兩位皇帝,一個在藝術海洋中恣意縱橫,揮毫潑墨,花石古玩,忙得個不亦樂乎;一個則在茫茫大草原上躍馬馳騁,承襲先輩田獵的愛好,駕鷹走狗,將所有的精力,都揮灑在遼闊草原的天空上。
遼國幅員遼闊,契丹人亦屬馬背上的民族,但及至有了北宋那白來的銀兩後,加上漢人的比例增大,漢化程度益高,遂有向農耕靠攏之趨勢,加上承平日久,這武功便日漸廢馳,如後世清之八旗般,一代不如一代了。
天祚帝名為耶律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在位期間寵信奸佞,不辨忠奸,導致大臣和各部落首領離心離德,他本人又極喜田獵,長期不務政事,在政策的實施上率性而為,說個倒行逆施亦不為過,這個同宋徽宗倒是有得一拼,只不過在性情上顯示為一文一武,殊途同歸。
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
養成外患兮磋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
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
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
這首詩是天祚帝的文妃蕭瑟瑟所作,她出身於渤海王族,國色天香,多才多藝,且生下長子被封為晉王,史載其“聰慧嫻雅,詳重寡言”,當看到夫君荒政遊獵,朝中奸人弄權,大臣離心,派系傾軋,屏藩失德,外患日熾的情況,憂憤不已,遂作詩勸諫。
不想這首詩反而引起了天祚帝極大的怨恨,後來竟借一個烏有的謀反事,將蕭瑟瑟母子一併處死,此事引起朝野震動,時人有記,“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體。”特別是對賢淑善良的蕭瑟瑟予以極大的同情,後人有詩悼雲:
瑟瑟傷時憫直臣,燕雲夕枕暗紅塵;
白頭宮監談遺事,芳草萋萋廢苑春。
天祚帝當時的唯一的敵手,只有南邊的宋王朝,然而,遼國疆域雖廣,但終究是一個以部落為根底的國家,天祚帝在位期間,各部落凝聚力漸失,看似龐大的國家,猶如一盤散沙,只是在一個名義上盟主之下,各自管控著自己的那一畝三分地。
但是,就是天祚帝執政期間,西邊的一個不起眼部落中出了一個名叫完顏阿骨打的漢子,他率領生女真部落,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對周邊小部落的統一,繼而又公開打出了反遼的旗號,並攻佔了遼國重鎮黃龍府。
一個曾經被自己在“頭魚宴”中安排獻舞的小人物,如今竟然發展到敢於同大遼叫板的地步,這讓天祚帝情何以堪,於是,他糾集起70萬遼軍東征,妄圖將這勃興的女真人一掌拍死,遂發生了遼、金之間生死攸關的護步答岡之戰。
此時的金人滿打滿算也不足2萬人,兩軍比例為1比35,這可能是歷史上兵力差距最大的對決了,結果當然又應了中國古代戰例中時常提及的一個詞,叫以少勝多。
對於這人數相差巨大的戰役,我是小有懷疑的,因為無論如何遼國是不太可能召集起這70萬之眾的,這肯定是後來修史之人,為凸顯輝煌的誇大之辭,抑或是當時天祚帝起兵時,為震懾對手的手段,就如同當年曹操下赤壁時,寫的那“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一般。
經此一戰,雙方的天平便發生了傾斜,大批遼國的文臣武將或逃或降,加上災荒饑饉,人畜死亡無算,短短十年內便已無同金人相抗衡的實力了。
到後來遼、金交戰時,不但出現大批將領投敵和部落倒戈的事件,而且還發生了內部反叛,相互攻伐,整個遼國呈現出極度混亂之時,這在當時羈留金朝的宋使洪皓所作的《松漠紀聞》中多有記載。
降金的契丹將領不僅在滅遼的征戰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後來滅宋的戰爭中勇猛無比,所向披靡,比如“靖康之難”後,趙構逃到揚州時,耶律馬五率軍突襲,嚇得趙構丟下正在歡娛的女人一路狂奔,從此落下“隱疾”而失去生育能力。
可別小看這一事件,這對南宋王朝有著巨大的影響,不僅關係到南宋皇位的走向,而且後來岳飛被害,其中有一條重要的原因,就是操了他不該操的心,因為,他上書請求趙構早點收養皇族之子,以解無嗣之憂。
平心而論,這天祚帝在最後與金人的交戰中,還是有著令人讚歎的不屈之精神,同宋徽宗看到金人來襲便跑得“飛叉叉”的不同,後來的天祚帝是一邊跑,一邊不停地重新組織軍力再戰,顯示了一個契丹漢子所特有的血性,這點同徽宗趙佶是無法比的,他是一直戰至一兵一卒,最後是戰敗被俘,一年後病死在金營中。
天災和人禍是摧毀大遼的兩大殺手,前者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而後者則是由歷代遼國皇帝長期放任的結果,到了天祚帝之時形成的總爆發,偏偏這時又遇到一個狗屎運極好的完顏阿骨打,所以,契丹人的亡國有著必然性,不幸的是讓天祚帝給遇到了。
北宋亡國,人們是怪罪於宋徽宗沉湎於自己的藝術世界中,當然,他作用奸佞、不理國政,所以後人有詩云:“胡營鐵馬入中原,漢宮衰草連朔邊,徽宗皇帝多慷慨,瘦金當年不值錢!”
反觀這天祚帝,被人指責為耽於田獵而亡國,但是,如果瞭解契丹人生活之習性,怕也要兩說了,至少不能將亡國的原因算在他的這一喜好上面。
同後世清王朝年度的“秋狩”一樣,這些馬背民族是很看重狩獵的,不過,他們一般是去一處名為木蘭圍場的固定之地,而當年的契丹人就廣闊多了,他們是“春水秋山,冬夏捺缽。”
“捺缽”是契丹語,其實是行營之意,後來引申為皇帝四季的狩獵活動,這是他們的祖宗法度,也是保持強健體魄和尚武精神的傳統,並不是天祚帝所特有,這其中也是有著每到一處,便召見各部落首領主各國使臣的慣例,所以,以此來指責天祚帝,肯定不是太貼切的。
遼人崇尚騎射之風,在對宋的戰爭中雖說是佔盡了風頭,可是他們卻怯於攻城略地,對此的能力極差,而一遇到比他們在騎射上更勝一籌的女真人時,便毫無優勢可言了。
天祚帝繼位之時比宋徽宗大不了多少,也不過二十多歲,此時的遼國同宋王朝一樣,各種積弊都凸顯了起來,特別是外有部落間的離心離德,內有文恬武嬉的縱情享樂,整個國家早已呈敗亡之勢。
加上天祚帝年輕任性,對內訌的隱患和金人的崛起沒有充分認識其危害性,所以,在他如前秦苻堅般,帶著一大幫各懷鬼胎的部落前去討伐完顏阿骨打時,被打敗也不是件讓人吃驚之事了。
接下來,這半漢半胡的遼國迎來的便是內部全面崩陷,如雪崩一樣,迅速地走向了沒落,雖然也有著一些同金人血拼到底的戰將,無奈,在金、宋的兩面夾擊下,歷兩百年的遼王朝壽終正寢。
不過,那背信棄義,在背後狠插了遼人一刀的宋徽宗最終也是自食其果,金人在滅遼後,馬頭一轉便向汴梁殺來,二帝被擄,妻女受辱,北宋亦慘遭亡國之痛。
我想,當金人將這二位關在一起之時,這撕毀合約的宋徽宗怕是羞愧滿滿,儘管亡國只是時間上的遲早,但如果不是他不懂唇亡齒寒這淺顯的道理,何至於受這樣大的苦難,不是天亡大宋,天亡大遼,而是他們這二人都是活在自己世界中的奇葩,換句話說,都不是當皇帝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