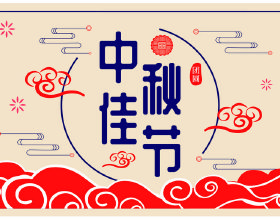五叔一覺醒來下不了炕,保健站的大夫看了看,搖搖頭,悄悄地囑咐五嬸準備後事。
五嬸顧不上抹眼淚,趕著做壽衣,可是,做了半截的壽衣,藍的黑的綢子緞子扯了一大堆,五叔卻哼著擋住不讓做。
昏迷的五叔扯著肩上的褂子,白眼翻著五嬸,悠著一絲的氣力說 ,做這樣的。
五叔肩上是件四個兜的制服,是多年前在城裡工作的二叔給的。說是給,其實是二叔看五叔喜歡,穿在身上,左瞅右瞅地不捨得脫下,一會兒又披在肩上,走得嗵嗵的,給二叔看,笑模樣樣地問二叔,哥,你瞅,穿上這四個兜,我像文化人不。
從此,那件四個兜的制服就沒有離開過五叔。趕集時披著,去地裡幹活時也披著。天熱了,五叔穿著五嬸做的粗布背褡,四個兜就搭在肩頭;下雪了,四個兜的制服在肩上披不住,風一吹,忽悠就掉了。
五叔把四個兜套在老黑棉襖上。四個兜的制服窄小得扣不上,五叔就敞著懷,走得蕩蕩的。
四個兜有時挑在玉米棵上,有時掛在北廈門口,來來往往的人見了,就說,老五在哩。
誰也不知道在多少個黃昏和清早,五叔披著四個兜的制服走在灑滿霞輝的巷裡或者蚰蜒般的田間小路上時,看著讓落日或者朝霞塗抹得上了釉般光彩奪目的四個兜,五叔的心是怎樣的激盪,一條走了多少年的土坷垃路,也讓他走得蕩蕩的,充滿了豪氣,走出了非凡的氣象,也走出了屬於五叔的翻翩風度。
人們都說,老五穿了四個兜,就是不一樣了。
五叔確實跟以前不一樣了。 說話不像以前吹鬍子瞪眼昨昨呼呼地吼叫了,就是吐痰也不像以前張口就來。五叔把痰吐在糞堆或是茅房,要是眼眉前沒有糞堆,五叔就硬憋著自己。
讓村人稀奇的是穿上四個兜制服的五叔真做起了文化人。五叔說,咱不能穿了文化人的四個兜,一點文化都沒有。
五叔趕集回來買了筆墨紙硯,五叔要學字寫字。五嬸不樂意,嫌花錢。一張紙的錢能買兩盒火柴,能稱半斤鹽。
五叔也不捨得花錢,狠心戒了煙,煙癮來了,就揉一把大麻葉子抽。五叔有了空閒就支開小方桌,一個大字一個大字的寫。
五叔上過掃盲班,能寫幾個字。可五叔不滿足,逮著人就要向字。沒事就要趴在桌子上寫倆字。站在地裡握著鍁把鋤把空閒了也要在地上畫幾下。
五嬸說你舞弄啥啊。
五叔說,你不懂,講話的人是話不離嘴,寫字的人是筆不離手。五叔不管五嬸咋笑話,抖抖肩上的四個兜,一把鐵鍁在地上畫得龍飛鳳舞,塵土飛揚。
寫來寫去,五叔還真學了好多字,後來,讓大家沒想到的是五叔的毛筆字寫到了村人的紅白喜事以及過年的對聯上了。
五叔一擺開架勢寫字,先要把四個兜的制服在肩上抖了又抖,低頭彎腰握筆,刷刷刷,大字是大字的樣,小字是小字的樣。
人們都說五叔的字橫豎看都跟那四個兜的制服一樣,文化得很。
五嬸卻不那麼看。
五嬸說五叔裝洋相瞎抖擻,穿個四個兜就以為是文化人,閒球得沒事寫啥字哩,貼了工夫還貼了錢。
五叔不跟五嬸計較,抖抖肩上的四個兜,笑得很文化。
以前那些事五嬸雖然覺得五叔荒唐,過去了,也不計較了, 現在要做壽衣,可不能再由著五叔了。
五叔迷瞪著眼,唸叨,把那一堆的綢子緞子都退了,我一輩子就這麼一個心思,就想穿一件新新的我自己的四個兜。
媳婦女子聽五叔說得心酸,抹著淚說,爸你別急,我們給你做一件新的。五叔點點頭,又昏迷了過去。
新四個兜制服還沒做好,五叔死了。
五叔成殮時,裡裡外外穿的都是綢子緞子做的壽衣。五嬸說,把那件舊的四個兜給他貼身穿吧,他心念哩。
作者:袁省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