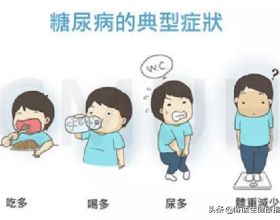只有初中文化的黃琳讀不懂文學,但能讀得懂《悲慘世界》裡的芳汀。她在那個年代裡沒有太多選擇,但本能地想要改變下一代命運。透過近乎倔強的奮鬥,這個單親媽媽一點點把兩個女兒的命運託舉到更廣的世界。
2021年7月22日這天,對黃琳來說是個特殊的日子。中午,她收到二女兒海海考上上海東華大學的訊息,而後,又得知大女兒跳槽加薪成功。“我的寶貝們太棒了!”誰都不知道欣喜滿足的黃琳,當時的心情到底有多少種層次。在夜色中手握方向盤的她,也曾迷茫在一個個十字路口,卻始終追逐著光。
黃琳今年45歲,出生於青海樂都縣的一個普通家庭,只有初中文化。她離過兩次婚,是兩個女孩的媽媽。十五年前,她開始了獨自撫養兩個女兒的日子。期間,她做過不少零工,日子有時緊有時松,在外人眼裡他們過得不算太富足。但黃琳一直有種樸素的樂觀:只要有健康的身體,有手有腳,就不會把自己餓死。
如今,她是一名在青海跑車的滴滴司機。而在此之前,黃琳在上海包裝生鮮蔬菜,每個月能拿六七千。在那個潮溼的低溫庫房裡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她犯了風溼性關節炎,右手連筷子和牙刷都拿不穩。不得已,黃琳辭掉了工作。
當時,大女兒剛工作沒多久,二女兒即將高考,家用主要還得靠黃琳掙。但就業市場對年過四十的女性並不友好,黃琳犯了難,自己還可以做什麼呢?後來,經朋友介紹,她決定貸款買車,回西寧開滴滴。
2020年12月,黃琳開始在西寧跑車。她有些著急,得趕緊掙生活費,不能影響女兒的學業。聽說機場線的深夜單掙得多,她也來看看。
機場線的活兒是一根難啃的肉骨頭,跑一趟掙得多,但接單難——從西寧市區到機場30多公里的距離,司機需要每天起早貪黑地在附近跑車才有可能被系統記住派活兒,有時繞著機場轉了好幾圈都不一定能接到單。許多人嫌辛苦,沒堅持下去。黃琳是這條線上為數不多堅持下來的滴滴女司機。
最開始,別人都在爆單,黃琳卻一個活兒也沒接到。她從來不是個愛哭的人,但黃琳清楚記得當時被急哭了。那不是太過疲憊的宣洩,而是被無形的壓力逼到角落的無奈。
她不認輸。
黃琳的一天從早上4點半開始。簡單收拾一陣就出門跑單,中途回家休息幾個小時後又重新出門。每天深夜接完市區的單之後,黃琳堅持來機場,一圈一圈地轉,等待系統派單。晚上2點多收車回家,匆匆吃了晚飯,洗漱一陣,沉沉睡去。開車考驗體力和注意力,黃琳曾在朋友圈裡寫:“一個人一臺車一直走,路上還堵車……困了我自己扇自己耳光!我絕不慣著自己。”
那段時間,幾乎每個清晨和深夜,都能看到黃琳白色的車駛過機場線的公路。終於,她開始搶到訂單,營收也漸漸有了起色。
這條機場線上的男司機基本都認得黃琳的車。跑了四五年的車,他們頭一回見到像黃琳這樣的人,跑了沒多久,一來機場就能接上單。7月結束,黃琳盤了盤當月流水,拉了一萬多塊錢。這是近幾個月以來跑滴滴賺得最多的一次。她很開心,女兒們的生活費有著落了。
如今,兩個女兒都不在自己的身邊——大女兒和二女兒分別在上海工作、上學。但黃琳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情況,而且她知道,母女三人在心靈上離得比誰都近。一個人開車的路上,黃琳時常想起女兒們。車內遮陽板上,她把一張母女三人的合照小心地放在那裡。
自女兒誕生起,黃琳就一直有一個信念:要把女兒們送到她們想去的地方,不要重走自己的老路。而今,看著群裡孩子們發來的生活照,她感覺她們正在走向更廣的世界。
想出去看看。這是黃琳還未成年時就蟄伏在心裡的願望。
1976年,黃琳出生在被山環抱的礦場裡。年少時,她最喜歡的時刻是放學後揹著書包爬上山去。山風吹著,眼前的大山沒什麼綠意,連在一起,向遠方湧去。她特別想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能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後來,父母離了婚,18歲的黃琳和姐姐離開了大山,到西寧找母親。在那個省會城市裡,街上多是裝著木門的小平房,她還看到了電影院和各色旅遊海報。這一切都令她新奇。
和她同齡的人此時多嫁了人。當地的傳統觀念中,女人嫁個好人家才是有好歸宿。但在黃琳眼裡,那些女人的生活都很糟糕,並不開心。黃琳覺得自己沒法和那些人交流,因為她們的話題迅速被困在婆媳和妯娌的家長裡短中,出不來。而黃琳感興趣的是海報裡的三亞和九寨溝,那些大山之外的世界。雖然她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沒法走出去。
後來,讀完初中的黃琳因為無錢唸書,被母親安排在飯館打工。在母親的介紹下,她稀裡糊塗地結了婚,有了兩個女兒。她仔細地教女兒唸書,希望有一天她們能去到更大的地方看看。
三十歲時,黃琳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跳出命運閉環的心愈發強烈,而這個可能的前提是自己出去掙更多的錢。恰巧,一位女朋友邀她去外地開飯店,但丈夫不同意,覺得女人不該在外面拋頭露面。黃琳和他爭吵,但沒有結果。黃琳形容自己“一下子醒了”:“我覺得我不能這樣生活下去,我的這一輩子還很長。”
她毅然出走,開始了自己的闖蕩。
四十歲時,距離黃琳第一次出走,過去了10年,她第一次在出租屋裡讀到《悲慘世界》,也是第一次讀到芳汀。書中,這位母親為了讓女兒活下去,出賣自己的頭髮、牙齒。自雨果寫下這本書一百五十多年後,黃琳在文字中與那位母親產生了共情:“這是一份責任,她願意付出自己最珍貴的東西。”
與第一任丈夫離婚後,為了讓女兒們有爸爸,她與第二任丈夫結婚。但不久,她發現男人對孩子並不好。為了不影響孩子學業,她又一次堅決地帶著女兒離開。
成為獨自撫養女兒的單親媽媽並不容易,但黃琳已經習慣了。時間撥回第一次離婚後,和女朋友合夥開的飯店黃了,三十二歲的黃琳回到西寧打工。她當過手機庫房管理員,做過財務,擺過地攤,在手機城裡賣過貨。剛開始,她一個人住,孩子託給父母照顧。那是最窘迫的時候,自己在外面吃飯都要盤算半天:是要一碗米粉,還是一串菜,或是一個餅?如果要菜的話,餅就吃不了。還是吃餅會飽一些,她把錢遞給了老闆。
那些日子,她住在西寧一間月租50元的出租屋裡。在那個幾平米的空間裡,黃琳開始看書。下班後吃過飯到睡前的時間,她讀那些勵志向和心理學的書。在書中,她重新理解自己的處境——生活中的磨難,會是一種財富。她感到充實,讀累了就睡,等待第二天的重啟。
後來,等她一個月能掙幾千塊時,黃琳陸續把兩個女兒也接到自己身邊。最開始,在那間西寧小小的出租屋裡,母女三人擠在一張一米五的小床上,每天晚上都會聊天。後來,黃琳帶著她們搬到一間更大的屋子裡,擺上了書架和綠蘿,朋友充話費送的洗衣機,一個小書桌,一臺便宜的二手電腦,還有借錢買來的一架將近三千塊的電子琴——她想讓還在上小學的二女兒學習彈琴,還替她報了課。這對於當時沒有積蓄的她們來說,有些奢侈。但是錢擠擠總會有的。
於是,母女三人在那間出租屋裡度過了許多難忘的時刻:女兒們會在三層書架上取下繪本和小說,或是跟隨母親在那臺二手電腦上看宮崎駿的電影。雖然生活並不特別富足,但母女三人過得十分充實。
如今,黃琳每隔半年或一年會重看一遍《悲慘世界》。每次重新看完這本書,黃琳都會深深同情芳汀,同時也會被書中人物所激勵。他們像是光,在黑暗中托起了希望。她喜歡書裡那些即使身處困境仍心懷善意的人們,想借此提醒自己做事要善良、寬容和堅強。她也這麼教導女兒們。
今年8月,黃琳在和人聊天時突然意識到,自己過去對芳汀的感情源自哪裡:“我覺得我就是芳汀,只是責任面前不允許我軟弱流淚。”
2021年9月,和母親黃琳一樣出生在青海的海海,收到了心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她即將前往上海東華大學上學。但假如小時候母親沒有把自己接回身邊撫養,可能這一切會走向另一條岔路。
最開始,離婚的母親把自己託付給爺爺奶奶撫養。但老人們對自己的期望和那片古老的土地一樣:女孩子不必好好讀書,尋得個好人家嫁了最好。少未經事的海海因此也不怎麼在意學業。直到黃琳把她接回身邊後,篤定地看著她:你唯一要做的事是好好讀書,考上大學。海海的眼裡重新燃起了光。
要如何形容母女間的關係?在黃琳的眼中,兩個女兒分別是太陽和月亮,而自己是地球,她們就像朋友,平等又親密。而在二女兒海海的回答裡,媽媽是朝陽,是人生中影響到自己的第一股力量。
對海海來說,她的母親是一個強大的人,也是漂泊生活中不變的座標。從小,她、姐姐和母親總是搬家,居無定所。和母親改嫁到北京後,她在北京上學,碰到母親在外地打工的時候,自己會在親戚和朋友家借住。“沒有什麼坎是過不去的。”海海記得母親一直在生活中重複這句話。
敏感如她,海海知道母親在外面受了許多苦,但她從未見過媽媽在她們面前流淚。她和姐姐能做的,是時常和她聊聊天,再送上一些小禮物。再次回憶過去,海海這麼形容:“像是和媽媽一起走在泥濘的路上,她披著披風,拿著權杖,跟我說:‘別跪下,往前走!’”
另一邊,黃琳一人肩負著養育兩個孩子的責任,輾轉不同的地方打工。她節衣縮食,絕不會讓孩子缺吃缺喝。在外人看來,這樣的日子過得很苦。曾有朋友擔心她想不開尋短見,但黃琳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管搬到哪裡,她一直保持著看書的習慣,她總記著書裡的那句話:生活中的磨難是生命的一部分。
她和芳汀一樣,面對生活的苦難只能迎難而上,她逐漸習慣了。並且知道自己有更重要的事還沒有完成——替女兒們構築起一片小小的避風港,讓她們在裡面自由生長。
海海記得,跟隨母親來到北京後,出租屋裡她陪自己練琴的場景——她正在練習克羅埃西亞狂想曲,細碎又重複的音節重複迴盪在客廳裡。在音樂的世界中,海海往往覺得很舒適,那是一種和現實世界不同的地方,令人愉快。母親坐在自己的房間織毛衣,時不時會欣喜地說:“好棒哦,寶貝!”
類似的稱讚在黃琳閱讀海海寫下的小說時也說過。
海海喜歡看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的書,從初中開始,她也開始嘗試自己寫小說。高中時,一位老師借給她膝上型電腦,讓她寫下那些故事。她把電腦帶回家,和母親黃琳說起這件事。黃琳十分高興,告訴她:“你什麼都不要做,就只要在那寫。”就這樣,那個暑假裡,海海浸入文字裡,一點點碼出了14萬字。
因為平時太忙,黃琳只讀過一些女兒寫的文章。她能樸素地感覺到女兒寫得很好,但那些內容超出了她的經驗,她無法像理解芳汀一樣去理解海海筆下的人物。但她仍然決定必須要讓孩子心無旁騖地繼續這件事,而且,海海即將高考,不能讓她操心生計問題。
2020年的疫情曾經打亂過黃琳的計劃,她一度不知道還能找到怎樣的工作維續。2021年,回西寧開滴滴的黃琳感到生活又接了地,但每月還賬時多是剛剛好還清,她得再掙多一些錢。
5月的某天下午,作為網約車司機,黃琳加入了滴滴“橙果計劃”,一個關注網約車司機子女教育發展的公益專案。填好表後,她發現自己的車主介面多了個“高考家庭”的標籤,她沒想太多,照常開車。驚喜發生在6月4日,女兒高考前三天。黃琳收到了橙果公益寄來的“高考加油包”。她看到包裹裡精緻的馬克杯、扇子和布袋,心裡湧出暖意,“還有別人在關心我們。”三年來,除了黃琳一家,還有近三萬多個司機家庭參與了“橙果計劃”,其中有不少人也曾感受過黃琳心中的暖意。
那天,黃琳特意拍了照,發了條朋友圈給女兒加油:“Happiness depends upon ourselves,幸福與否我們自己說了算。”3個月後,幸福的確降臨了,海海收到了心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後來,她們還收到了橙果計劃高考獎學金。孩子剛開學,生活支出比之前大許多,這筆錢緩了黃琳的燃眉之急。
最近,剛入學的海海透過考試,分進了最好的英語班。黃琳想起參加這個計劃的孩子還有機會獲得獎學金。她囑咐女兒,繼續好好學習,不要辜負期望。
假如將黃琳和海海各自在18歲這年的命運進行對照,再過不久,黃琳即將出嫁,生育一雙女兒;而海海即將去往心儀的大學。母女二人的命運在這裡發生了更大的分流。
黃琳曾想過,假如芳汀生活在今天,或許她也不至於在生活的苦難中死去,可以將女兒撫養成人——就像自己一樣,雖然生活並不平順,但還能夠在顛簸的生活中託著孩子們一點點離開那些陳舊的命運。
今年夏天,黃琳決定抽空帶海海去青海湖邊旅行一趟。那兩天,她們住在青海湖邊的民宿,騎犛牛,逛草原。那天清晨,她們決定一起去看日出。將近五點多,一輪金黃的太陽刺破冷冽的空氣,出現在藍色的湖面上,碎成粼粼的波光。
“媽媽,你看(朝陽)好美。”海海看向母親。
“這個太陽就像你們。你們的人生路還很長,即將開始新的生活了。真好。”黃琳開心地看向女兒。
她感受到一股欣欣向榮的力量,新生活即將開啟——自己的女兒們的確正在走向自己曾經嚮往過的那個更大的世界。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 END -
撰文 | 肖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