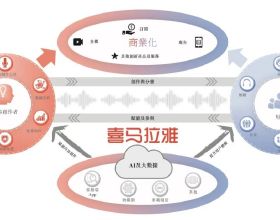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葛書潤 李濘伶 嘉賓 陳竹沁 胡卉 蘇敏 音訊編輯 張迪青 馬慶隆
Play
00:00
68:06
Volume
《漣漪效應》第九期
渴望上路,幾乎是人類永恆的、本能般的夢。
剛剛過去的國慶長假,據文化和旅遊部資料中心測算,全國國內旅遊出遊5.15億人次,按可比口徑恢復至疫前同期的70.1%。
旅行“最試驗得出一個人的品性”,因為它是“最勞頓,最麻煩……經過長期苦旅行而彼此不討厭的人,才可以結交做朋友。”旅行讓人跳出所處的人際網路,重新思考“己”與“群”的關係。
這期在長假錄製的節目,我們請來三位女性嘉賓:非虛構作家胡卉,公益人陳竹沁,以及“57歲阿姨自駕遊全國”的主人公蘇敏,聊聊自己有關旅行的經驗。
三位嘉賓裡,有人在獨自的旅行中看到了最圓的落日,有人在旅途中決定與愛人分開,有人將出門跋涉視作一場漫長的“透氣”,獨自上路,又在所到之處尋找新的聯結。
“出走”對於女性而言,常在思想史與文學史上和“自覺”“獨立”等詞相連,而現實中,當女性以某種形式暫時地離開生活軌道,也往往懷揣著獨屬於女性的動因、承受更多來自家庭的拉扯和顧慮。但正是這一次次選擇出走,一次次對慣性的叛逃,讓她們成為她們。
與此同時,旅遊的產業化和社交媒體的流行,正讓旅行與物質更深度的勾連,被建構為浸染著消費主義的中產幻景。目的地、機酒、餐廳,甚至入鏡的穿搭、妝容……當一切都可以被展演、排序和比較,我們如何重新定義一場好的旅行?
【嘉賓】
陳竹沁(竹子),多年記者,線下交流平臺Belonging Space創辦者之一,長期關注性別和精神健康話題。
胡卉,非虛構寫作者,出版女性真實故事集《木蘭結婚》。
蘇敏,“57歲阿姨自駕遊全國”主人公,2020年,她獨自一人從河南出發,自駕上萬公里到達海南。
【主播】
葛書潤,澎湃新聞特約撰稿人
李濘伶,澎湃新聞特約撰稿人
【以下為本次訪談的節選】
“一個人的旅行,能與世界發生直接的聯絡”
葛書潤:竹子老師有一個人去旅遊的經歷嗎,去了什麼地方呢?
陳竹沁:因為我之前也是做調查記者,工作中一個人出差的經歷特別多,所以真正計劃出遊的話還是會跟朋友一起。唯一一次獨自旅行很神奇,是我被我的閨蜜放了鴿子,當時本來要去日本玩兒,然後那時候日本剛剛發生海嘯和核洩漏,我閨蜜的老公就擔心不安全,她已經和我買好了機票,但最終還是退掉了,於是我就變成了一個人,去東京玩了一個禮拜。
我覺得可能跟東京的城市文化有關,一方面,這個城市的文化生活特別豐富,整個城市的設施對於獨自出行的人也特別友好,你不會感覺到任何的不便。但是同時,在東京那種特大的城市中一個人旅行,你又能夠感覺到一種清冷的孤獨,我很享受它。
葛書潤:胡卉老師有一個人旅行的經歷嗎?
胡卉:我有一年是自己去了新疆,那個時候剛剛碩士畢業,二十五六歲,剛參加工作,發了工資肯定要揮霍,就自己去了北京,一路又去了烏魯木齊、克拉瑪依、布林津、富蘊縣,在那邊呆了十多天。
我跑出去的時候好像運氣一般都不錯,南迦巴瓦峰常年積雪,一直雲霧繚繞著,不太輕易看得出它的面目。那天上午我竟然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看見了南迦巴瓦峰三次,有一次是臨近中午的時候,太陽金燦燦的,照著那個很尖銳的峰頂,非常美。
一個人去新疆那次,我還搭了很久的大巴去克拉瑪依的魔鬼城看落日。那時候天色已經晚了,落日在幾分鐘裡就會落下去,所以我下了車之後一個人一路跑、一路跑。魔鬼城是風蝕地貌,那些山丘被風吹得奇形怪狀的,你越是往裡面跑的話,其實越恐怖。那個時候我周圍好像還沒什麼人,我就自己跑到了一個最高的山丘上。
很奇怪,當時我在跑的時候,心裡好像還一直想著當時在上海遭遇的一點挫折,當時剛工作,還沒有完全的適應好。我的身子在新疆跑著,心卻好像還留在上海受傷。但是,我記得當時在魔鬼城裡一直跑的時候,心裡好像有一種決絕之氣,就想著自己在很多選擇上還是要自重、還是要堅持自己。
就在那個瞬間,好像很神奇,好像自己一個人在大自然之間好像做完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選擇。當我一個人跑上那個很高的山丘的時候,落日就出現在我的面前,非常渾圓,真的很美。我感覺到自己好像接住了上天的恩賜。
一個人的旅行,能夠跟世界發生很直接的聯絡,像是一場對話。感受力反而會更強,體驗會非常深刻。
葛書潤:感覺這對你的人生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場旅行。
胡卉:自己講不太清楚那次旅行中發生的深刻體驗,後來我讀到一個瑞士人寫的一部關於旅行的書,叫《世界之道》,裡面有一段話,我覺得對那種很神奇的體驗描述得蠻準確的,也寫得非常詩意。
他說,“最後為你搭起生命的架構的,不是家庭,不是職業,也不是別人對你的看法,而是自然界中為數不多的幾個瞬間。”那種瞬間“升起於時空的懸浮之中,比心裡的愛情還要恬靜,這樣的瞬間如此寶貴。生活把它們分配給我們的時候,總是精打細算,剛好裝滿我們弱小的心靈。”我當時好像被這一段話接住了,就是那麼一種體驗。
我還蠻喜歡一個人旅行的,因為自己的性格容易去照顧身邊的人,當我跟別人一塊兒出去的時候,我總是在噓寒問暖。
葛書潤:但是一個人的時候就不需要去照顧別人了,只要注重自己內心的感受就可以了。
李濘伶:蘇阿姨,你獨自在路上馳行的時候有什麼樣的感覺嗎?能夠描述一下嗎?
蘇敏:我比較喜歡車,也比較喜歡開車,我開著車在路上的時間,身心是特別自由放鬆的一個狀態,感覺特別愉悅,而且,滿眼的樹,路兩邊的風景,特別能感染到我,讓我感覺到特別寧靜,有一種呼吸到自由空氣的感覺。
李濘伶:在這一路上有結識到什麼朋友嗎?
蘇敏:有的,去年大部分時間都是我一個人在外面旅行,九月份出來,從鄭州一直到海南,這一路基本上是我一個人。路上也偶爾結識一下朋友,但都是結識幾天、同行幾天,也就分開了。
但今年三月份,有兩名我的粉絲主動邀請我,他們是我的同齡人,比我稍微就小了那麼一兩歲。他們就說“大姐,我們想跟著你環遊全中國,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計劃?”我說有,本來我今年也是要準備走這個環遊中國這個環線的,他們就說“那我們結伴兒吧,我們之前沒有自駕出來旅行過,你走了這麼長時間,啥都比較熟悉,所以我們想跟著你。”當時我說,那行,我們一起結個伴不是更好嗎?
我們幾個人雖然都沒有見過面,但一照面就把彼此認出來了。我感覺這很神奇。然後就是因為他們認識我吧,因為畢竟我的影片,他們都看過,因為從影片裡也看過我長什麼樣,但是我一眼把他們兩個認出來,他們也是感到很驚奇,說,“大姐,你怎麼能一下把我們認出來?”我說“我感覺就是你們”。
後來我們真的結伴而行了,一直到國慶節前才分開。
李濘伶:你覺得跟朋友一起旅行和你自己一個人旅行有什麼不同嗎?
蘇敏:我們路上遇到一些困難或者別的事情,大家可以一起出出主意,去想辦法解決。一群人在一起旅行有很多快樂,因為平常我們吃過飯的時間,會聊聊天說說話,去景點去逛逛也有人作伴了。
但是人多也有弊端,可能有的時候方向不統一、意見不統一,有人想去這個景點兒,但其他人又不想去,要是一個人的話分歧就不會產生了。一個人感覺更自由一點兒,想去哪兒去哪兒,自己說了算,我想停就停,想走就走,今天不餓,我說不吃就不吃飯了。但是人多了,大家就會說“哎呀,你不吃好像是不是你心情不好,為什麼不吃飯呢”?
李濘伶:之前澎湃人物這邊也採訪過你,你將這一場自駕遊描述為“一場自由的透氣”,現在回過頭來想,這場透氣對你的人生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呢?
蘇敏:它對我的人生真的影響很大,因為我的前半生沒有出來以前,我對生活是沒有抱任何希望的,我就感覺我的生活就是“從今天都可以看到最後一天”的感覺。但透過這次出來以後,不但結識了夥伴們,也改變了我很多的認知。我感覺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不應該束縛在家裡面,去過那種一眼能看到頭的生活,而應該找一些從來沒有過過的、自己比較嚮往的生活去過一下。
我出來旅行了以後,身體,思想各方面都改變比較大。大家都說我開朗、邏輯明確,其實我以前在家從沒有感覺到我講話、做事兒有邏輯,但是現在大家這樣說我,其實也是我出來這種旅行,接觸的人多了,鍛煉出來的一個結果。
我感覺我現在已經找到了我想要的那種生活,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想去看景,我就去看景,不想看景的話,我可以縮在一個地方,就在那兒,待上個十天半月,好好地休息一下,領略當地的風土人情。現在的心境,我感覺特別適合,我已經愛上了這種生活。
女性需要家庭之外的社交網路與公共空間
葛書潤:胡卉老師今年出版的一本書,叫《木蘭結婚》,裡面收錄了15個有關女性的故事,能給聽眾朋友們介紹一下這本書嗎?
胡卉:《木蘭結婚》這本書基本上就是我這幾年發表在澎湃新聞的非虛構欄目“鏡相”上的故事,也感謝澎湃。
這裡面一共是15個不同年齡階段的女性故事。她們當中有的才兩歲,有的已經60多歲了,有的人單身,有的正在婚戀當中,也有的離異。有的正在經歷一些困境,有的透過自己的努力已經走出了困境。我覺得她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她們在處理自我跟世界的關係的時候,都面對過很複雜的挑戰,然後在她們身上也可以看見一些人性的珍貴和閃光。
這本書,是我選擇從學校辭職,開始全職做採訪和寫作一個階段性的成果。國慶之後應該會在噹噹和京東上市,很期待聽到大家的反饋。
葛書潤:這本書每一篇的主角都是女性,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自覺,專門地把女性作為書寫物件呢?有沒有什麼事情啟發了你?
胡卉:應該是我那一年生了孩子,我因此發現男人跟女人最大的不同,應該在生育這件事情上。所以我就會去更自覺地關注性別。
葛書潤:那在你這本書的15個故事裡有一些就是對女性出走的一個描寫嗎?就是有這樣比較突出的出走女性的形象,這個“出走”不一定要是旅行,也可以是從家裡面出來,從以前的生活中出走,你可以介紹一兩個嗎?
胡卉:我寫了幾個這樣的女性,但是她們出走的方式有所不同。有一篇叫《逃離》,講一個年輕的女性好不容易在一線城市安下了家,卻發現丈夫有家暴的傾向。她就在猶豫要不要帶著年幼的孩子離異,因為這個家確實是她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要不要這麼快就去做一個把它切割的決定,對她來說也很為難。還有一篇是講一個單親媽媽辭掉了一個小地方醫院護士的工作,要去薪水更高的深圳打拼,還帶著自己的兒子跟母親。
我看到這個變化的時代裡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了,行動的自由也更大了,但與此同時,她們移動的時候揹負的東西也更重了。我的書寫物件們的每次移動,每次出走,其實她們都是把一些家庭的責任都拿到自己身上來了。
葛書潤:她們不是把家庭拋在後面了,反而是會揹著這個責任繼續出走。
胡卉:對,她出走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她不是從丈夫的家裡走出來,把孩子、把婚姻留在那個家裡,而是帶著孩子一起走。現在的城市女性都有一定的謀生的能力,她們在多年的婚姻生活裡習慣了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
葛書潤:這可能已經成為了她們的一種慣性。你的故事裡的這些女性,你觀察到她們的出走一般是出於什麼樣的動力呢,是對現有生活的不滿,還是說想去追求個人的價值?
胡卉:可能是就是所有人都會想的,對美好生活的希望吧。但她們都對自身有一份自信,才敢去變動,才敢挑戰新的東西。
葛書潤:你覺得女性在選擇從一種生活跳到另一種生活的時候,身上的擔子會比男性更重一些嗎?她們會遇到一些獨屬於這個性別的阻礙嗎?
胡卉:我好像不能夠下這個定論,因為男人也很難,我感覺一個個體加一個個體的社會好像很難去歸類,只能去看、去分析那個個體,她/他是怎麼樣的、怎麼想的。
葛書潤:每個個體都有自己的困境,有自己不同的想法。我覺得就是你剛才的話其實也給我一點啟發,就是不要把真實的經驗去套一些比較刻板的概念,還是得去誠實地走向這些真實地人,這可能一個更好的閱讀文學作品的方式。
李濘伶:竹子是一位前媒體人,現在在做一個線下的公益組織“Belonging space”。你對女性權益和精神健康這方面的偏向和你自身的親身經歷有關嗎?
陳竹沁:我們的空間是兩個女性聯合創辦的,可能是因為個人經歷慢慢把關注點會放在性別議題上,我的合作伙伴以前是做精神健康藝術特展相關的公益組織的,我們就想嘗試把在兩個議題之間尋找一個交叉。
無論是從身邊的經驗還是資料的統計上來看,女性抑鬱的發生率更高,而且這裡面有很多社會結構的因素,而不只是個體精神的原因。所以我們在做這樣一個線下空間的時候,一方面想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讓大家來討論這些話題,同時也透過豐富的文化活動讓大家能夠找到一種歸屬感,就像它的名字所體現的那樣。

Belonging space原來進門的展示區,放了一些公益宣傳冊子。受訪者供圖
剛剛胡卉提到,每個生長在男權環境的女性好像都有一個性別覺醒的過程,胡卉是因為生育,我比她稍微前置一點。 當時我剛結婚不久,然後就愛上了一個另外一個已婚的男士,這個很獨特的困境讓我更多地去思考什麼是愛,同時反思一些所謂的道德規範、社會規範,是不是更多地壓在了女性的身上。
我小時候媽媽也離婚了,但是她很多時候給了我一種感覺,就是女效能夠在自己覺得舒適的狀態下,找到一個安全的關係網路,它不一定是男性主導、依附在男性的親屬網路中,這個是很重要的。
李濘伶:你在探索自己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透過旅行的方式?
陳竹沁:我好像有很多關係變動的節點都是跟旅行有關,可能因為那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場域吧。
我先生在旅途中跟我表白,就發生我們在一起看日出的過程中。我決定離婚也是在一段我們共同的旅行中,那次是我們一起去土耳其,前一天玩皮划艇玩得比較晚,回到住宿的地方已經是十一二點了,但是我又很想第二天早上想去爬山,因為裡有土耳其跟希臘在一戰前因人口大交換留下的村落。那天我前夫他就覺得很累不想出去,但我又很堅持,我就一個人去爬山。那次我真正感受到了一個人克服恐懼的過程。

竹子在土耳其費特希耶的Kayakoy村落廢墟山頂。受訪者供圖
我確實會帶著性別視角去看待一些問題,就女性旅行這個話題而言,從古至今,女性和男性的區隔就在於,很多時候公共空間並不向女性敞開,或者它本身對女性不夠安全。
此外,旅行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中產階級文化,旅行的自主權很多時候體現在對於財富的支配上。當沒有手握家裡的財產大權,或者在一定範圍內可以支配家庭財產,女性想出門旅行,體會多樣文化、認識不同的人、打破確定,這種可能性對很多女性來說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覺得走出去,比如旅行,是打破常規的一種可能性。旅行可能正好是一個視窗,在這一段時空裡,可能也不會很長期,但你終於可以靜下來跟自己對話,去梳理很多的關係。
李濘伶:如果說旅行只能夠是一種短期改變自己生活的方式,你覺得處於現實困境當中的女性還可以做什麼事情,讓這種改善更加持久呢?
陳竹沁:我覺得可能更多的是重建自己身邊的社交網路。一個美國的女性心理學家(珍.貝克.密勒)在上世紀70年代寫了一本書叫《走向新的女性心理學》的書,她提出了關係文化理論,她說女性的特點是在和他人建立情感和歸屬關係的基礎上發展的,這可能會有別於男性以個人發展和競爭為中心。而女性因此會反過來被指責“依賴性強”,或者被指責將這個歸屬關係作為生活的中心。很多女性患抑鬱症也跟這種歸屬關係的喪失有關。
密勒認為,女性在社會上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歸屬形式是一種屈從的關係,這種關係更多是在尋找另一半的認可。但是,她們不應該對本身自己內心向往這種歸屬關係而進行譴責,更重要的是重構這種歸屬關係的本質。首先就是要自己決定跟誰聯合、聯結,要問自己,我到底是誰,我需要什麼,我真正想決定什麼,由此重建新的社會規範。像這樣的一種新的歸屬關係跟行動力量可以相互融合,促進女性攜手合作,集體行動,並從這樣的關係中獲取力量。
把旅行放置到這麼一個語境裡,我跟我的閨蜜去旅行,或者我跟一些陌生人,和新交的朋友一起去旅行,也可能是一種重建網路社交的方式。
旅行不必昂貴,日常“出走”亦是療愈
李濘伶:竹子對精神健康領域比較熟悉,旅行是不是能夠成為一種療愈方式?
陳竹沁:英國現在一些精神健康機構會開出一些所謂“社會處方”,不同於直接服用的精神健康藥物,它把人放回到一種人際交往的環境以及跟大自然的相處中。比如說花一定的時間去圖書館看書,或者參加一些文化活動,或者去大自然裡面徒步。這些本身有一種療愈的作用,可以創造一個跟你日常生活那些所煩心的事情相隔絕的氛圍,尋找到一種內心的寧靜。哪怕有的時候只是出個門,就是去身邊的一個公園,或者在庭院走一走,把它作為一種新的日常,而不是一個特殊行為,就會更持之有效地療愈自己。
葛書潤:我想問蘇阿姨,就是我聽說你在這個自駕遊之前,其實已經開始做直播錄影片了,然後你覺得就是錄影片這件事情本身,對你的走出門的這麼一個決定,起到了一些促進的作用嗎?
蘇敏:旅行之前沒有開始直播,只是開始創作一些小影片,其實也是為這個旅旅行做打算。剛才竹子老師也都說了,說是這個旅行是一箇中產階級什麼,其實就是說比較花錢的事情。對於我這個退休工資只有2000多塊錢的老人來說,支付我的旅途費用有點兒緊巴巴,所以我就想自己做一些事情,能夠攢一些旅途上的費用。
說實話,剛開始做了四五個月,沒有任何收入,最多就幾分幾毛錢。但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做這個影片也不一定就是為了收入去的,它也可以記錄你的生活。我們老年人有時記性不好,去年的事情我今年都可以忘記,但由於短影片的記錄,我隨時可以翻出來看一下,看看去年的今天我在哪兒,做了什麼。短影片其實也是對我的生活一個挺好的記錄。
今年(短影片和直播)對我旅途確實有幫助,隨著粉絲量的增加,我的櫥窗裡擺一些商品,也有人買了,這個收入也是對我旅途上的一點支援。
但我這種年紀的人,竟然學會了用手機去記錄生活,用攝像機去拍攝我眼中和別人不同的東西,我感覺這才是我最大的收穫。
葛書潤:你在旅途上遭遇的一些不開心的事情或者一些困難的時候,你會跟直播間的網友們交流嗎,還是把這些情緒隱藏在螢幕的背後?
蘇敏:我會跟他們交流,因為生活本來就有多面性,肯定有快樂也有不快樂,我在路上肯定也會遇到困難。我一般都會在直播間和他們交流,就說“看,我今天遇到什麼困難了,然後這個困難我怎麼處理解決”,遇到不如意的都有給大家分享的,這些才是真實的生活的寫照。所以我的直播間裡的粉絲說我是“最接地氣的主播”。
葛書潤:我覺得你一方面是很接地氣,然後另一方面,我感覺你的這一路的經歷也非常浪漫,像一個公路電影一樣,聽得我很感動。
蘇敏:我這一路真的就像一部公路電影,充滿了快樂,充滿了新奇,也充滿了波折,也有一些困難,也有一些困擾,總之來說,它是一個大千世界的寫照,是一個真實生活的記錄,真得很。我感覺如果拍出一部電影的話可能很精彩。
蘇敏:我想問一下(竹子、胡卉)兩位老師,你們怎麼看待我現在自駕遊在路上這個事兒,很多人會說,作為一個女性,就應該在家裡帶娃、相夫教子,不能有屬於自己的一個生活,我的直播間裡面還有些人問我,“你這樣拋家棄女感到舒服嗎?”
陳竹沁:我特別想讓我媽看蘇阿姨的影片,然後希望她也能夠為自己而活。我覺得這應該是我身邊很多女生共有的感觸吧,因為有的時候,很多的母女矛盾都存在於媽媽太在乎孩子了,在乎你怎麼還沒有結婚,怎麼還不讓我抱孫子之類的事情。我覺得我們上一代的媽媽,就是包括蘇阿姨也說,哪怕想要出去自由地生活,其實心中那個牽絆還在。但我就會對她說“說沒事兒,我自己都能搞定,你出去玩吧”。
葛書潤:就是反而希望母親把這個目光分散一點,不要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陳竹沁:對,反而壓力很大。我們都希望自己的母親能夠出去走走,但同時也希望,社會文化能夠給予她們精神上的支援,然後另一方面,就是“出走”的配套設施能更好,比如說城市的公共空間可以更安全,對於女性更性別友好。我們不該把“出去走走”這件事又變成另一種新的社會規範去push她們。我現在也會覺得我應該更多地陪我媽媽,帶她出去玩兒或者是在家裡面幫她做一些家務,從身邊做起,從理解自己的母親或者女性長輩做起。
責任編輯:黃芳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