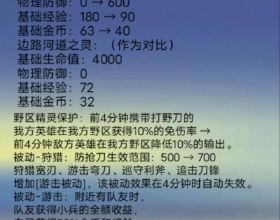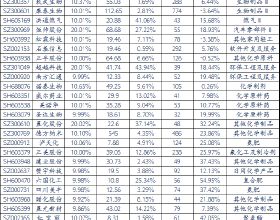話說曹文詔一路圍剿李自成,卻讓他逃脫了,當夜懊喪不已。他吩咐隨他進山追剿計程車卒,就地宿營,第二天調大軍來徹底搜山。
他治軍向來以嚴厲出名,軍令一下,那些小卒不敢稍有違抗,只得找背風的地方,權且休息一夜。
曹文詔雖然已經是總兵之職,卻一點沒有總兵的架子。他不講究氣派和吃喝,平時與士卒同甘共苦,譬如今夜吧,他計程車卒們經歷了一天的廝殺,到現在也吃不上飯;他呢,也並沒有比士卒們多吃一口飯,多喝一口水。有了這些,他計程車卒們心裡的怨氣就不是那麼強了。
士卒們跟著他,苦是苦了一點,也並不是沒有一點值得他們留戀的。別的將軍指揮的官軍,到處燒殺擄掠,種種流賊都不幹的勾當,他們卻一項不少地都幹了。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與其碰到官軍,還不如碰到流賊比較起來更好一點。而曹文詔的軍隊,在百姓的中間,名聲卻極好,他們從不擾亂當地百姓,所過之處,秋毫無犯。就憑這一點,人們就對他們充滿好感,至少是不是殺賊倒還是次要的。
曹文詔計程車卒們沒能擄掠來東西,有了這樣的榮譽,也十分自豪了。
當然,他們不騷擾百姓,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從不欠餉,官軍之中,他們是待遇最好的,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是陝甘邊軍中挑了又挑、選了又選的精兵強將,無論是朝廷還是地方,對他們期望極高,倚為重鎮,在糧餉方面也特別優待;另一方面,是曹文詔在上級的督撫眼中,素以倔強爽直著名,他為了給自己計程車卒爭取利益,從不畏懼任何權勢。
久而久之,人們也不敢欺瞞他,所有的該得的給養,提升軍官的機會只要是曹文詔和他的軍將卒應該得到的,一樣也不缺。曹文詔本人,又確實富有才能,無論是上司、同事還是敵人,都不敢輕視於他,這樣的結果,使曹氏的軍隊地位重要,兵精糧足,軍紀優良,聲名遠揚。
多年的行軍生涯,曹文詔見多了庸將腐兵,他們敗壞的軍紀,讓任何一個有道德心的人感到震驚,甚至無法理解和忍受。最令曹文詔頭痛的,是自己必須和那些貪婪殘暴、昏聵無能的將領或地方官員打交道,和他們合作。
有時候他就想,大明朝的江山如果遲早會丟掉的話,不是斷送在那些流賊土寇的手中,而是斷送在那些靠著這江山、吃著這江山的官老爺和兵大爺的手裡。他們像一群大大小小的蛀蟲,不知利害、不計後果地蛀蝕著這座大廈的每一根樑柱,還自作聰明地以為自己吃得越多,佔的便宜也就越大;有一些比他們更精明一點的人,對這後果也許有那麼一點預感,但是看著周圍一副副貪婪的嘴臉,他們又能做些什麼呢?
自己也不過是他們中的一員,即便自己和他們同流合汙,這個混亂骯髒的大池子也不會變得更髒。即使你潔身自好,那大廈也是要倒塌的,蝕蟲成千上萬,一條條的蛀蝕樑柱,根本沒有絲毫的影響。還不如索性趁著燈紅酒綠的時候瀟灑快活一番。
也算是不枉此生;等那大廈終於要倒塌的時候,自己再隨著那千萬條蛀蟲一起死掉。
曹文詔和別的文官武將不一樣,他仍然對自己所負擔的使命、自己的作用抱有很大的自信,雖然他偶爾也有悲觀失望的時候。
他覺著等到自己剿平了這些流賊土寇之後,仰仗著皇帝的年輕和英明,依靠像洪承疇洪大人那樣的地方大員赤心為國,這大明朝的天下,應該還能很有一番作為的吧。儘管這可能要花費相當大的努力。
曹文詔忽然想到今天和自己對陣的李自成,他禁不住一陣心寒。這李自成在目前的義軍將領中,根本算不了什麼,不知道比他人馬多的紫金梁、闖王、八大王、老回回等匪首,是不是也像他一樣作戰勇猛,能打能殺。如果那樣的話,自己將來要碰到的惡戰肯定也少不了。
幸虧自己的部卒要比對方人數多,而且訓練有素,不然就單憑李自成和他的幾員部將那勇猛拼殺的勁頭,自己也早就落敗了。
看來義軍裡還是有不少將才,自己過去剿一處滅一處,遂小覷了義軍隊伍,以為對方盡是烏合之眾,亡命之徒,自己一陣衝殺,對方定然分崩離析,沒想還有這樣不服輸的隊伍,自己以後須當多加小心才是。
曹文詔坐在一塊平坦的大石頭上,一邊胡思亂想,一邊盤算著明天應當如何指揮士卒細緻搜山,務必要將李自成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斬草除根免留後患。
他既然重傷未愈,肯是逃不出這一帶山區,自己也好趁搜山的機會,稍稍休整一下,自己自從入晉以來,一路殺伐,人困馬疲,也早該休息一段了。
這麼想著,曹文詔感到睏意襲來,漸漸支撐不住,也顧不上山風陰寒,顧不上冰冷的石頭,倒在那裡,進入了夢鄉。
但八月的大山,樹木繁茂,要想大海撈針般地抓住李自成,談何容易。曹文詔沒有能搜尋到李自成,又由於義軍勢力漸大,便上疏朝廷,請求集中軍卒,合剿流寇。
這樣兜了一段時間的圈子,曹文詔感到這樣下去太過被動,於是上疏朝廷,要調各地精兵強將,合剿流賊。
崇禎收到曹文詔的奏章後,便徵集了群臣的意見,便命昌平副總兵左良玉率兵2500人前往豫北助剿。
左良玉奉了詔書,率昌平兵離開駐地,前往河南剿殺義軍。
他剛剛三十出頭的年紀,在他這一級的武將之中,是相當年輕的。每當他受到別人稱頌他年輕有為的時候,他都不自覺地想起他的領路人——侯恂。
當時左良玉只不過是遼東軍中的一名小將,除了相貌英俊之外,即使有本領也無法施展。
侯恂一眼看出這個相貌出眾、英姿勃勃的小卒與眾不同,把他調到自己身邊,刻意地栽培提拔他。左良玉得到迅速的提升,不幾年便由一名默默無聞的普通一卒,升到了參將之職。
左良玉無論是帶兵打仗,還是為人處事,都有他自己的獨到之處。他身上有一種特殊的魅力,這種魅力使他對士卒產生一種強烈的影響。
他從來不怎麼用嚴格的軍紀約束部下,這使他的軍隊在衛戍京師的各軍之中名聲最差,他們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百姓的財物,拷掠那些在京城有背景的富紳,絲毫不把那些氣衝斗牛的富紳們聲色俱厲的恫嚇當作一回事。
但是他們卻對左良玉表示他們的忠誠與尊敬,無論是在表面上還是在內心裡。
散漫的軍紀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毀掉了這支軍隊的戰鬥力,使他們成為一群烏合之眾。左良玉的命令仍然得到最徹底的執行,他以高度靈活卻十分有力的方式,主宰著這群鬆散、傲慢計程車兵們,使他們知道,他們之所以能為所欲為,只是因為得到了他的默許。
只要他願意,他隨時可以收回他賦予他們的權力。
這些士兵們雖然很少接觸到自己的主帥,卻時時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左良玉並不威嚴,卻以他的聰明與手腕,贏得了士兵們的敬重。
這些士兵們在其它的軍隊中,或者能得到高升的機會,或者生活得可能更自在,但他們卻更喜歡在左良玉的手下當差,喜歡在他的軍隊中彌散的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氣氛。
在他們的感覺裡,左良玉的軍營能使他們過上一個士兵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生活。這種生活,既不是物質上的奢侈,又不是精神上的滿足,但似乎又都有那麼一點,許多到過左良玉的隊伍,並生活過一段的人們都會不自覺地喜歡上這種生活。
左良玉雖然不過三十來歲的年紀,從政的時間也不長,但他在官場上卻表現出少有的老練與早熟。他深通官場中的升降沉浮,即使對那些他極少接觸的陰謀與狡詐,他也能迅即地運用自己的才智與經驗,作出適當的反應,不卑不亢地化解掉。
據他的估計,這次自己出師征剿流賊,必定是朝中一些人看自己不順眼,趁著皇上要出兵援剿的機會,拿自己作了擋箭牌。不過這種小伎倆他左良玉是不會放在眼裡的,不多幾年的軍官生涯,他悟出了一個道理: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在官場上,所有的抗爭,在最終的意義上都是實力的競爭。
所以你儘可以忽視一個精明卻沒有實力的對手,卻不要輕視一個有實力卻不精明的對手,因為他具備傷害你的力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對手的聰明與否是不容易看出來的,除非你自己也是一個聰明的人。
而實力的大小,相對來說要容易得多,假如你從他本人身上看不出來,那麼從你周圍的人身上也能分辨出來,因為有不少人對勢力的強弱,有一種人生靈敏的嗅覺,而他們的一種本能的行動,就是趨炎附勢。
左良玉有相當的自信,無論自己此次剿賊是勝是敗,對自己的前途都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一旦你洞悉了事物背後的真相,那麼其它一切便都不再重要,它們對你達到目的並非毫無影響,但它們的作用卻要小得多了。
左良玉率兵前往河南,一路走了將近兩個月。在這段時間裡,紫金梁等人繼續在豫北縱橫馳騁,如入無人之境。
這時候,左良玉的昌平兵到了豫北。這些兵大爺在京營時尚且擄掠成性,此番到了河南,更是本性流露,無所不為。這些兵與其說是散漫放縱的軍隊,還不如說是有一點軍紀的土匪。他們一來,河南的百性可就遭了殃,豫北一帶,恍然間又成了以前的山陝。
左良玉所部都是朝廷的精銳部隊,又帶有土匪的習氣,糧食輜重暫時接濟不上,也能支援三五天,是以依照義軍向來的戰法,到了左良玉的部隊這裡,卻完全吃不開了。義軍的小股部隊與官軍接了幾陣,全被打敗,一時之間官軍氣勢大勝。
紫金梁王自用見義軍屢敗於左良玉的軍隊,大怒,率領本營約二萬兵馬,撤了懷慶之圍,前來與左良玉決戰。左良玉見義軍勢大,不敢硬碰,率軍撤走,紫金梁緊追不捨。
但是左良玉的部隊僅有2500人,機動靈活,奔走迅捷,紫金梁的隊伍男女老少2萬餘人,急切之間哪能趕上?卻被左良玉逃脫過程中幾次反撲,消耗掉了不少部隊。
紫金梁見前不能消滅掉左良玉軍,後不能攻下懷慶府,左右為難。召集各路義軍首領商議,眾人以為與其陷入兩難境地,不如暫且退回山西,待時機成熟再出太行山。紫金梁無奈,於是率領大隊義軍,越過太行山,返回潞安之長治,暫且休整一段時間。
左良玉見紫金梁解圍北去,便寫了一封奏疏,稱自己在河南連戰皆勝,殺敵數千。現在義軍大營聞風喪膽,盡數逃回山西,自己正帶得勝之兵,準備進剿紫金梁部。崇禎聞報,龍顏大悅,親自擬旨,將左良玉誇獎一番。
劉體純、高一功二人在壽陽隨李自成與曹文詔一場惡戰,幾乎全軍覆沒。兩個人帶了部分殘兵敗將,殺出了重圍,無處可去,便投奔高迎祥的大營而來。
高闖王聽了二人述說作戰經過,嘆惋不已。
自己自與李自成相識以來,英雄相惜,友情相會時日無多,總是為軍務所煩累,卻不料這一次李自成出征,一戰敗北,生死未卜。闖王思之再三,不禁愴然,虎目之中落下兩滴濁淚。
他抬頭對劉體純、高一功二人說道:“自成此次生死不明,你們兩個人可以再從我的營中撥出200名弟兄,到壽陽附近山中,尋找自成的下落。一旦有訊息,立刻報與我知道。”兩個人領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