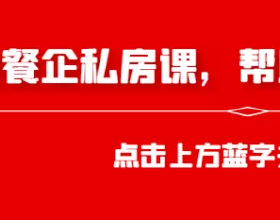故鄉與墳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有一句話:“一個人只要沒有個死去的親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這地方的人” 。
剛讀到這句話時,我便想到了我那個遠在西北的故鄉。
我是在懂了許多皮毛的世事後離開那裡的。
這些年來,我一直沒有回去過,一是為了心中的那一份還在燃燒的理想之火,二則也是希望能夠衣錦還鄉,體面地見到我那些闊別已久的親人、朋友。這種虛榮的想法也是我時常用來支援自己努力拼搏的信念。
然而,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在異鄉的這些日子裡,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北方的那片土地,即使那裡沒有清粼粼的水,只有渾濁的黃河的小支脈還在曲折地養育著幾代人;即使那裡沒有巍峨的山,只有風沙堆積起的黃土高原在千溝萬壑中支撐著幾代人的夢想;即使那裡沒有蔥鬱的樹,只有幾株白楊在迎風筆直地生長著幾代人的脊骨……然而正如馬爾克斯說的那樣,在那片土地上,不光有我活著的鄉親,還有我死去的父輩。
故鄉與墳
我的爺爺老了(在家鄉,老年人的去世不說是“死了”,而說成是“老了”),然後埋在那裡,田地裡便隆起了一個新的墳堆;我的父親患病去世後,埋在離爺爺墳冢不遠的地方,於是田地上又多了一個墳堆。而那時候,爺爺的墳堆上早已經長滿了雜草——也許,有時候生命其實並沒有停止生長,它只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罷了。
以前,每年的清明以及年三十,家裡人(也就是我們弟兄三人,以我們家鄉的習俗,女人是不允許上墳的,因此母親便留在家裡侍弄上墳用的祭品)便會去上墳。
我們總是給去世早的親人先燒紙、敬菸,然後再給後來去世的親人燒。
而且,邊燒還會說一些話,以此來表達心中的思念。有時,在爺爺的墳前燒紙時,哥哥會對著一旁的父親的墳說幾句,大致的意思不過是說這是給爺爺燒的紙,叫父親別搶,待會兒再給他燒等等。那時候,風往往會把燒著的紙灰吹得漫天都是,像一隻只黑色的蝴蝶飛舞,又像是什麼人在搶那些燒掉的“紙錢”似的,倘若真的是這樣,是誰呢?爺爺還是父親?抑或埋在那片土地裡的無數個鬼魂?
故鄉與墳
關於墳以及與墳有關的死,在年少的我看來,似乎始終是一個恐怖的存在。
但不管怎樣,那裡總是有一種神秘感在引誘著我不斷地去幻想鬼、閻王、無常、地獄……因著這一層緣由,每次上墳的時候,我都會集中精力去觀察周圍的一切。當然,偶爾也會有奇特的發現,比如在我們家地鄰近的地裡又多了一座新墳,比如在爺爺的墳冢上不知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個鼠洞,比如在父親的墳前長出了不知什麼名字的野花……如此的發現倒是有不少,但因為怕別人說我上墳不專心,於是也就把這些發現悄悄地藏在了心裡。
直到多年以後離開家鄉,我還時常會想起當時的那些發現。不過,回憶總使我無限悵惘地想到墳,想到我至今深埋於地下的親人,想到那些即將走向墳塋的衰病的鄉黨——當然,也時常想到自己,想到墳,想到與墳有關的死。
故鄉與墳
也許,再過許多年以後,我也會被埋在那裡,同我的祖輩們一起化作一個個隆起的墳堆。到那時候,有誰來為我燒紙呢?他們會不會也為我的爺爺、父親,他們的曾祖父、祖父燒上一吊紙錢呢?
古語有云,狐死首丘。
有生之年,我是無法與那片土地日夜相伴了——它給了我生命、童年以及一切,卻沒有給我以歸宿——因為我明白,即使有一天我真的死了(不必諱言,死乃是不可避免的事),也不會佔用那裡的一片土地。
故鄉與墳
我的骨灰也許會裝在一個不足盈尺的盒子裡,灑在那片土地中,讓風吹著、雨淋著,並最終成為土地的一部分;也許,它再也回不到那片土地裡,一如每個漂零他鄉的孤魂野鬼一樣在異鄉的水泥城郭裡做著日夜難眠的歸夢;也許,它永遠也無法與土地相依,而是在不知名的地方繼續漂零。
故鄉與墳
只是,我不知道,在灑有我的骨灰的那片土地上,將會長出什麼樣的植物?在盛放著我的骨灰的墳塋前,將會有誰來為我燒一吊紙錢?
在飄蕩著我的魂魄的時空裡,將會有誰在默默中記起我?
如此等等,死生之所,求而不得,只有順其自然。
只是,如果我的骨灰能在那片埋著父輩的土地裡找到住所,就應該將它撒在那片土地上,讓它同那片土地一道經風、沐雨,並讓那片土地更加肥沃,更加富饒。如此,既是對我這些年漂泊的最大回報,也是對我永逝的生命以一個無比欣慰的弔唁。
故鄉與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