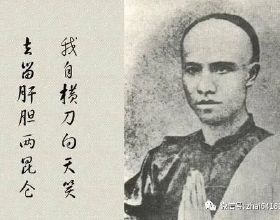賈平凹在他的小說《極花》的後記裡,談到貧窮與生育,寫了這麼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他說:“往往越是卑微的生命,如兔子、老鼠、蚊子,越是大量地繁殖……”,生育的本能,原始又荒蠻,偏偏那生命力又蓬勃的驚人,叫人敬畏的發怵。
本來就過得艱難,偏偏拖著螞蚱似的一串兒女們雪上加霜,活在現實裡是可憐可恨,寫進小說裡,便是絕佳的苦難敘事、絕妙的藝術縱深。
《豐乳肥臀》中,莫言將不同父親的8女一男,寫給悲苦一生的上官魯氏,母愛便鍍上厚重到悲愴的質感;張愛玲筆下,落敗的舊式大戶人家裡,守著乾巴巴“淑女”身份、泱泱擠在逼仄空間裡的六小姐、七小姐、八小姐們,脂粉盒掉進雞毛堆裡,命運就有了嘲諷般的悲涼。
在動盪變革的時代背景下,一對被生計煎熬著的夫妻,一群灰頭土臉的孩子,煙熏火燎中過得跌跌撞撞、急赤白臉,這樣的故事總歸是戲劇性地討巧的。貼近現實,又能在他人的苦難中尋得慰藉,生出隱秘且舒適的悲憫。未夕的《喬家的兒女》備受關注,也在情理之中了。
小說前兩句便是高潮——“喬一成十二歲的時候 ,添了個小弟弟。可是,沒了媽。”
一成、二強、三麗、四美、七七,一個不負責任的賭鬼老爹喬祖望,聞得到生活的苦,看得著未來的浪,這故事,催著人讀。
這位出場就因生第五胎而難產死去的媽媽,是十二歲少年喬一成模糊的愛與倉皇失措的痛。在別人的隻言片語裡,拼掇成一個溫和隱忍、善良無私的灰白形象。她三十五年的人生,最後定格於一張同樣模糊不清的遺照上,被閒言碎語切割,被時間細細遺忘。
多年以後,在二姨夫齊志強臨終前的回憶中,喬母的形象才如彌散的薄煙聚攏成一線:她叫“淑英”,也曾血肉豐滿地美麗過、戀愛過,而不僅僅是喬一成記憶裡肚子鼓起來、又癟下去,沒什麼光鮮衣裳穿的臃腫婦人。
喬母悲劇命運的源頭:家庭裡被迫“懂事”的老大
12歲的喬一成,在失去媽媽之後,頃刻間長大,用稚嫩的肩膀擔負起照顧弟妹的責任,因為他是大哥,長兄如父,向來如此。正如小小的他所想:“不幸,卻由命運交到你的掌心,不要都不行。”
在咱們傳統的約定俗成的家庭觀念裡,只要是老大,哪怕是早一兩分鐘出生的雙胞胎,也應該理所當然的“懂事”。
記得看過一個紀錄片,一對孿生姐弟,剖腹產時姐姐被父母選擇做老大。姐弟兩個每次爭吵,父母都會說:“你是老大,為什麼不能讓一下弟弟?”在一次看電視被弟弟搶了遙控器、向母親求助無果後,小姑娘徹底崩潰了,哭著等爸爸下班“主持公道”,結果委屈的姐姐又被爸爸教育了一通“不懂事”,最後向媽媽道了歉才被稱讚“好孩子”。看得如鯁在喉,倒吸涼氣!
為什麼成年人如此想當然地讓同樣是孩子的老大“懂事”?以家庭之名自私粗暴地挾持老大的情感,強加以責任,本質上是父母對教育的無能與懶政。
舊時代之下成長的喬母,自然更無以逃離身為老大的精神桎梏。
淑英與妹妹淑芳同齊志強青梅竹馬地長大,姐妹倆都對這個踏實端正的男人動了心。淑英白淨靦腆,與齊志強情投意合,就在兩個人訂婚之際,淑芳卻大病了一場,病中跪著乞求姐姐:“你把志強讓給我吧。喬祖望也是很歡喜你的,他家有個店子,條件不錯的。”
淑英為難,平常她什麼都可以無私地讓給妹妹,但深愛的未婚夫她怎麼能讓呢?淑芳一句你不讓我就去跳長江,到底擊中了她的軟肋,母親去世前,一再叮囑照顧妹妹,她不能讓妹妹丟了命。
妹妹自小被偏愛,自私的理直氣壯,她有恃無恐,對自己的幸福奮起直追,不管不顧。
擔著父母期望與家庭責任的姐姐卻不能,在辦喜事前不久,淑英瞞著不明就裡的齊志強,迅速跟了喬祖望。這一“讓”,人生置換、命運改寫。
喬祖望對家庭漠不關心,錢和人都耗在牌桌上,淑英從此在窮困的泥濘裡拖兒帶女、困頓掙扎。快臨產都捨不得坐公交車忍痛走到了醫院,一個人生下孩子,喬祖望還在牌桌上興致酣酣……
當少年喬一成暗自期望有二姨夫這樣負責任的父親時,當二姨家的兒子齊唯民純淨優秀的像一束刺痛他的光時,他再也不會想到,他原本可以幸福的人生,是被媽媽的善良葬送的。溫潤如玉的表哥,是被健康和滿的家庭徐徐焙出來的。他只有長出張牙舞爪的尖刺,才能保護他幼弱的弟妹。
媽媽身為老大自覺的“懂事”,為她悲劇的命運點燃引線,隨之炸的七零八落的,還有她子女們的人生。當喬一成為弟妹們自我讓度的人生與他的母親慢慢重疊時,原生家庭悲劇的延續性更令人嘆息,像燃不燼的火星子,誓把生活燙出個漆黑的無底洞。
喬母悲慘婚姻的宿命:軟弱的“奉獻型人格”
電影《教父》中有這麼句經典臺詞:“沒有邊界的心軟,只會讓對方得寸進尺;毫無原則的仁慈,只會讓對方為所欲為。”
在自我犧牲的自覺下嫁給喬祖望的淑英,從沒為自己活過一天。小說中一筆帶過的“男人不爭氣,不顧家,孩子多拖累重”,即可窺見她現實中的狼狽,直至死亡,12年婚姻帶給她的,是沒完沒了的生育、捉襟見肘的生活、累死累活的生存。
對於不負責任的丈夫,淑英的態度只有逆來順受的隱忍與軟弱。懷老五時,困窘的經濟狀況叫她猶豫,偷偷跑了兩回醫院,終因為忌憚丈夫沒敢做手術,縱使這樣,還叫丈夫拍桌子打板凳,把她臭罵了一通。
甚至給最愛的大兒子一成吃個溏心蛋的自由,淑英也沒有。擔心著被丈夫發現,偷摸讓一成躲在廚房雜物後面飛快地吃,燙得直嘆氣。臨盆在即,她也“識相”地獨自步走去一個偏遠且收費低的醫院,不去叨擾正打麻將的丈夫。
在本應該平等的夫妻關係裡,淑英的姿態低到了塵埃,越是對丈夫退讓、沒有要求,她越得不到最基本的尊重。一個人在產房生下老五後,喬祖望去看一眼的慾望都沒有:“有什麼好看的,哪家女人不生孩子?她也不是第一次生,怎麼這次就特別金貴了?”
觸目驚心的冷漠,默默為家庭燃燒奉獻自己的淑英,一步步走進自己用“無私”堆砌出的泥淖,最後的死亡,亦成了丈夫和旁人那裡一聲無足輕重的嘆息。“一輩子一件好衣服也沒穿過”,靈堂上拉了大紅的帳子,是丈夫給她最大的一點“犒賞”,為了安撫自己中年喪妻之痛,喬祖望連著打了兩個晚上的麻將……
《喬家的兒女》一書裡,不乏個性鮮明的女性,但過得好的,都是知道自己要什麼的。
喬一成的前妻葉小朗,同樣困難家庭出身,看清喬一成安於現狀的心後,果斷與平淡的婚姻切割,努力備考出了國;與喬一成曖昧過的女同事胡春曉,雖原生家庭上的共鳴與喬一成心有慼慼,但還是迅速嫁給了家境優越卻長相醜陋的“傑出”青年,以夫家的人脈資源實現了階層的躍遷,事業也平步青雲。
最具現實意義的,就是淑英的妹妹淑芳。她從姐姐那裡搶到溫和顧家的齊志強,便有了安定的生活,三個子女都各有出息。齊志強去世後,很快又再嫁,一生沒吃過苦受過累。往往“自私”的人,最懂得如何追求得到自己的幸福。
淑英的性格,其實很具有代表性,她的安於奉獻、任勞任怨,是很多“母親”形象的縮影。當我們習以為常妻子與母親的角色,就是“自我犧牲”時,謳歌也成了一種無形的道德綁架。
所以書中的旁觀者,感嘆喬一成兄弟姐妹的孤苦無依、唏噓喬祖望的壯年喪妻,甚至閒話編排懷疑淑英的貞潔,唯獨忽略了這個最無私的女人寫滿苦難的一生。
為了妹妹,淑英奉獻出自己深愛的未婚夫;為了家庭,淑英奉獻出自己的人生甚至生命。然而作為受益者的妹妹,在她喪事時就惦記要那頂靈堂裡的紅帳子;她做慣甩手掌櫃的丈夫,為她的醫藥費和丟下的一堆孩子窩火抱怨。
一個太過於“無私”的人,往往縱容了身邊“自私”的家人。長久的奉獻已逐漸熔為人格的一部分,他們將自我的需求與情感統統隱藏,反而所有付出都被認為天經地義。假如淑英有說“不”的態度,有追求自我的勇氣,有抗爭婚姻的無畏,她又怎會淪為一個失語的“生育機器”、並在這樣被定義的價值中死去?
常言說“我們的善良要有鋒芒”,同樣,我們的付出,也要有底線,這個底線,便是先愛自己的“自私”!以此為基礎衍生的一切“愛”,才是健康正常的情感關係。
寫在最後
《喬家的兒女》這本小說,主語在“兒女”上,它攫取時代縮影下一群人代表性的成長經歷,雖然是以艱難的成長與痛苦的拉扯為底色,但它想凸顯的是親情剪不斷的羈絆,雖“各人有各人的泥潭”,卻因為一個“家”字,打不散、拆不開,在困境時相依為命、彼此扶持。
儘管小說為了戲劇性增加了諸多不合情理的衝突,但切切有一種真實感,我們會發現,書中的人物與故事,與現實中的某些人、某些事重疊,這些都是散落在生活裡的人間真實,在看不見的角落,四處上演。
山水一程,兒女們各有歸處。合上書,我總想那幾筆帶過就死去的喬母,一個推進劇情的失語者,把她的溫柔、無私、簡樸、強韌都隱於歲月,籠統為一個“母親”的稱呼。這樣被忽視的她,隨處可見,為家庭付出所有,唯獨忘記去做自己,勞碌一生,彷彿本來就該如此。如果她活著,扛起這個家的,定然還是她。
書中二姨夫臨終前的回想令人動容,在他的內心深處,藏著一個叫淑英的女孩,她不是誰的媽媽、誰的妻子,她青澀好看、情感細膩,她擁有過真正美好的愛情。這隱秘的回憶,是給予淑英這個角色最悲憫的溫情。
王小波說“似水流年是一個人所有的一切,只有這個東西,才真正歸你所有。其餘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歡娛與不幸。”正因依靠著那片刻娛,多少如淑英一樣的母親,走完了她們被索取、被忽視的一生。很不想讚美這樣的人生偉大,但我們都願意承認,“她”很偉大。
-End-
看古今世事,讀書中天地,歡迎關注@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