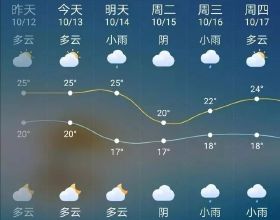古人喜好書寫遊記,在這些遊記當中,不乏荒誕離奇,乃至於怪力亂神的描寫。比如以下這段“清人北遊奇遇記”,便足以令今人感到嘖嘖稱奇。
湖南學子吳子春,落榜之後,在京為商,他酷愛地理,曾對友人說:“願效法徐霞客,遊歷名山大澤,不枉此生也!”
康熙三十六年,吳子春終於打定主意,他不惜重金買下“路引”,約上志同道合者九人,僱傭腳伕十人,攜帶刀劍弓弩,備齊乾糧淡水,以駱駝五匹、騾馬十匹,馱著輜重,於康熙三十六年三月正式啟程。
一行人等,先到琿春,休整幾天之後,正式向北進發,一路上風餐露宿, 披星戴月,受盡顛簸之苦,終於到達戈壁。
此地好個荒涼,但見飛沙浩渺,遮天蔽日;數步之外,不能見人。騾馬受驚,四散而逃,費盡千般辛苦,總算找回幾匹。趕緊清點輜重,所帶乾糧,尚夠充飢十日,無奈淡水已所剩無幾,照此下去,不出三五日,便紛紛都要渴死囉。
眾人一面頂著風沙前行,一面試圖找尋水源。烈日當頭,酷熱難耐;飛沙如刀,割傷臉面,令人無不叫苦。這般苦楚之下,有人打起退堂鼓,想要掉頭往回走。吳子春好言相勸,講出天降大任於斯人的道理,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成為人上人。倘若半途而廢,只怕這輩子都會深感遺憾。
他的話擲地有聲,句句打動人心,於是大家相互勉勵,你拽著我,我拉著你,重又頂著烈日飛沙踏上征程。
同行人中,有一人略懂找尋水脈的本領,就在大家已經乾渴的唇乾舌裂之時,這人終於找到一處水脈。掘地數丈,終於見到水源,大家拼命用手捧水來喝,頓感神清氣爽,無不大呼痛快。
吳子春笑稱此乃地宮清泉,無異於天宮瑤池中的金津玉露。眾人大笑,笑罷,重又哀嘆,水源稀少,只管人喝,不夠餵馬,若渴死了騾馬,那些輜重就要全憑人力馱著哩。
那個能識別水脈的人,只好另行尋找其他水源。找了一塊高地,手搭涼棚,朝四外遠眺,陡然手舞足蹈,他見到西南方向有個沙丘,認定沙丘之下,必有伏泉。眾人衝過去,合力挖掘,一個時辰之後,清水終於咕嘟咕嘟冒了出來。涓涓清水,清甜爽口,人與牲口,一併牛飲,一個個喝得肚子滾圓,才終於不再喝了。
喝飽之後,吳子春帶頭跪拜這一眼清泉,感謝上蒼憐憫,賜給他們“廣利刺泉”。
注:“廣利刺泉”源自唐朝詩人顧雲的《天威行》中——“耿恭拜出井底水,廣利刺開山上泉。”
參拜完畢之後,將水囊水瓶灌滿,一行人再次上路。又走十餘日,終於見到人煙,詢問之後,知道立足之地屬於準什噶爾的管轄範圍。在此地休養了幾天,補充了給養,再次準備向北行。
部落中人好言相勸:“出了準什噶爾的勢力範圍,屬於蠻荒地帶,常有蠻族出沒,那裡的人彪悍驍勇,對外人並不友好。”
吳子春謝過部落中人,毅然而然繼續上路。走了一月有餘,再次見到一個大型部落,這裡的人披頭散髮,面如油慄,幾乎所有的成年男女,臉上都刺有圖騰。吳子春試圖與他們溝通,發現他們根本聽不懂中原的語言,而吳子春一眾人等,也對他們使用的語言一竅不通。
就在雙方咿咿呀呀,比比劃劃之時,從人群中擠進一個身穿皮裘的土著男子,他居然能講一口流利的錫伯語,隊伍之中恰好有人懂得錫伯語,於是雙方展開交流。
土著男子聽說他們來自中原,興奮至極,立即翻譯給族長。族長隨即高呼一聲,部落中人紛紛手舞足蹈,以舞蹈的形式歡迎遠道而來的客人。
吳子春一夥被請到大帳之中,經過與那個會說錫伯語的男子一通交流,得知這裡就是準什噶爾部眾所說的蠻荒部落。這裡的人不會耕種,惡劣的天氣也不適宜耕種,因此這裡的人以狩獵和蓄養牛羊來維持生存。這裡沒有文字,也不懂貿易,對於中原人士尊奉的禮法,這裡的人更是一概不曉。
另外,會說錫伯語的男子還刻意對吳子春一眾說道,原本他們居住的區域也屬於大清國的管轄範圍,自從大清與羅剎國(古代對俄羅斯的稱呼)簽訂條約(尼布楚條約)之後,天山以北劃歸給了羅剎人,隨後他們就遭到了羅剎人的裹挾,部分族人順從了羅剎人,不順從的就與羅剎人展開廝殺,倖存下來的少數人輾轉來到了這個地方,自此過起了與世無爭的桃源生活。時間久了,人們開始懼怕外面的世界,既不願意接觸外界的人,也不願意外界的人踏足這裡。因此一旦有外人進入他們的領地,他們就會群起出動,將外人嚇跑。這一來,他們就成了外人眼裡的蠻族野人。
吳子春等人聽罷之後,深深為這些人的遭遇感到同情。在這裡住了幾天之後,吳子春等人又要上路了。蠻族中人送給他們牛脯和足夠的淡水,並給他們指了一條安全好走的路線。
走了三天之後,再一次人煙斷絕。朔風凜凜,放眼望去,一片荒涼,大風吹得人眼睛睜不開,根本不能借天上的日頭來識別道路,只能憑藉指南針以定方位。又走了五六天,乾糧和淡水所剩無幾,眾人再次發愁起來。吳子春登上高地,意圖找到水源,居然發現山巒之中,炊煙直上,似有人家居住。於是趕緊招呼大家朝著冒煙的方向趕奔過去。
離得近了,發現果然是一個村落。村落的規模不大,粗略一數,最多不過十五、六戶人家。有人發現了吳子春一夥陌生人,於是打起呼哨,立即從每家每戶之中衝出壯年,手持刀棒,準備禦敵。吳子春慌忙擺手,高呼自己這邊都是好人,絕無惡意。對方也不知道聽沒聽懂他的話,見他們沒有惡意,於是放下刀棒,一個黑麵黑衣的高個子大漢走過來與吳子春一夥交涉。
吳子春仔細看了這裡的人,發現他們的面容和衣著,似乎是蒙古人,但似乎又不是。那個黑麵大漢所說的也不是蒙古語,而是羅剎語。隊伍之中,那個會說錫伯語的人,也多少懂得一些羅剎語,交談之後,對方十分高興,趕緊將吳子春一夥請到一間很大的木屋之中,有人端來食物,請吳子春一夥充飢。
這裡的人十分好客,雖然雙方的語言不通,但透過手勢,以及那個稍懂羅剎語的人做翻譯,雙方也多多少少能溝通一下。
吳子春看到這裡的人雖然分開居住,但吃飯的時候,會聚在一起。他們用一個巨大的方爐烤制食物,烤出的食物外焦裡嫩,十分可口。問了名字,得知這種東西叫作麵包。
於是,吳子春用銀餅(銀子的一種)跟當地人交換麵包,當地人又送了他們一些肉脯,給予他們充足的淡水,目送他們遠去。
向北又走了五天,天氣愈發寒冷了起來,寒風撲面,痛如刀割,明明是白晝,卻瞬間變為黑夜,大家只能選擇背風的地方,搭起帳篷,在地上挖坑,堆上木炭,點燃之後,一面烹煮肉脯,一面借熱氣取暖。
黑夜退去之後,吳子春一夥不敢貿然上路。說來也巧,居然有個土人路過,吳子春趕緊將土人攔住,給他食物,請他說明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
土人所用的也是羅剎語,透過翻譯,得知這個地方名叫“夙木”,沒有四季之分,多數時候寒風怒吼,酷似寒冬,白晝的時間很短,有時候眨眼即黑,伴隨著寒風會落下巴掌大的雪片,在這裡很難生存下去,所以要麼快些趕路,走出這片嚴酷的地域,要麼往回走,遠離這裡。
吳子春決議再往前走,於是請土人為嚮導,走了十天,終於另有一番景緻。眼前一片荒山,山峰如琢玉,白茫茫一望無際。
充當嚮導的土人給他們指了方向後離去,一行人又走了十餘天,在一陌生地域修整,這裡的土人所使用的語言再也無法聽懂,土人如鼴鼠一般,挖地生存。其面目黝黑粗糙,以鴕鳥毛皮禦寒,茹毛飲血吃生肉、喝生水,與野人無異。這裡的白天更短,黑夜更長,吳子春一夥認為此地不宜久留,於是備齊淡水食物,繼續北上。
又走十餘日,遇到一條冰河。河對岸是一座冰山,寒風從冰山中穿過,發出嗚鳴之聲,如同冤鬼哭泣,眾人無不驚駭,不敢再往前走。眾人看到在冰山腳下,有一些體型巨大的動物,模樣像極了老鼠,卻比老鼠大出數倍,渾身皮毛呈銀色,用爪牙鑿開冰面,到水中抓魚。
吳子春撿起那些怪異鼠類丟下的魚,發現這裡的魚居然長著短短的角,兩腮各有十多條鬚子,脊背上長有如劍戟一樣的魚鰭,異常堅硬,十分鋒利。燉來嘗試味道,其味苦澀,並不好吃。
夜裡觀望星辰,天上星寥寥數顆,北斗星已過南數度,用指南針辨別方位,發現指南針居然不能轉動。
這並非好兆頭,眾人商議之後,認為不宜再往前行,前面冰雪皚皚,不知兇險,執意前行,恐怕難以生還。吳子春接受建議,改轍向南,走了一年多,方才到達琿春。去時二十人,回來僅十個,不幸罹難之人,埋骨荒涼之地,再無法迴歸中原。
吳子春回到京師之後,將自己一路上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編撰成冊,刊印發行,取名《北遊雜記》。可惜這本書未能全數留存下來,後世學子“泖濱野客”將殘存的部分記載於筆記之中,這便有了筆者這篇拙作。至於吳子春所述是否真實,他到過的地方究竟又是何地,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