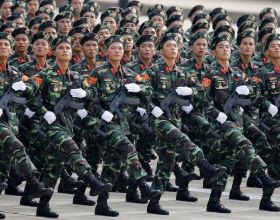馬建紅(法學博士)
在傳統社會中,女性的地位很低,她們的一生幾乎都要依附從屬於男性,所謂的“三從”(“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就是這種從屬地位的恰當概括。尤其在婚姻方面,女子什麼時候嫁、要嫁給誰都由父母說了算,完全沒有自由。婚後又要服從公婆的管教,相夫教子,稍有差池,就可能得到一紙休書。而且男女一旦成婚,妻子遂成為丈夫的私產,不僅其命運被丈夫拿捏著,甚至在夫家生活無以為繼時,還有可能被賣掉變現,以此來換回夫家的生活必需品。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左聯作家之一的柔石,曾寫過一篇題為《為奴隸的母親》的小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無名無姓,只因為兒子叫春寶,所以被人們喚作“春寶娘”。她丈夫家裡極窮,丈夫脾氣也差,還得了無法醫治的黃疸病,在春寶娘生下一個女兒後還將女兒溺斃。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春寶娘被其丈夫“典賣”給了一個財主,典期三年,目的是為財主生一個兒子。春寶娘在財主家裡幹著下人的活兒,給財主生下兒子秋寶。三年出典期滿,春寶娘只能與秋寶骨肉分離,繼續回到自己一貧如洗的家。在那個年代,有多少女性的命運如春寶娘一樣不堪?這恐怕無法統計。
《為奴隸的母親》只是一篇小說,其中不乏虛構成分的話,而那些保存於檔案中的史料,為我們記錄了生活中部分女性的真實生活——典妻、賣妻的現象不僅切實存在,且數量還相當可觀。收錄於《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一書中的《清代縣衙的賣妻案件審判:以272件巴縣、南部與寶坻縣案子為例證》,是斯坦福大學的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教授寫的一篇論文。該研究運用的有關賣妻的案件樣本,是四川巴縣1750年代到1900年代的208個案件,四川南部縣1800年代至1890年代的47個案件,以及直隸寶坻縣1810年代至1900年代的16個案子。這些案件是由地方官府直接受理的“細事”。此外,蘇成捷教授在研究中還運用了刑科題本中的材料。刑科題本是由各省督撫上呈到中央請求複核的題本,是由地方官府定擬後,由府級與省級覆審的各級審判的記錄,而刑科題本中所涉的主要是命案,賣妻案件則是需要中央覆審的殺人罪所附帶的次要罪行。也可以說,在這類案件中,賣妻是殺人案的由頭。
從有關“賣妻”的案件材料可以看出,在清代因賣妻而引發的民事或刑事糾紛不少。可以想見,民間那些沒有因糾紛訴諸官府的賣妻事件肯定會更多。賣妻是“丈夫販賣妻子,讓她成為另一男人的妻或妾”。在清代,雖然法律上將賣妻視為“犯奸”罪之一種,並規定對相關的各方施以嚴厲的刑罰,因為在人們正統的道德觀念中,認為賣妻是一種犯奸行為,即是本夫縱容了妻子與後夫犯奸。在清律中有禁止“買休賣休”的規定:“若用財買休賣休(因而)和(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婦人離異歸宗,財禮入官。……妾,減一等。媒合人各減犯人……罪一等。”
在與婚姻相關的法律條文中,也規定禁止典僱自己的妻妾給他人為妻妾,禁止“將其妻妾妄作姊妹嫁人”。但在現實生活中,賣妻則是在窮人間普遍存在的一種生存策略。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源於男女性別的比例不均,一方面由於鄉野間溺殺女嬰的情況較多,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貧困地區有無數的女兒與年輕女性,被賣到較富裕的家庭裡當傭人或妾,使得貧困地區的性別不均更加惡化,由此導致了這種私下的女人交易行為。
19世紀時,美國傳教士Adele Fielde就講述了一位在廣東遭丈夫連同孩子賣掉的女性教徒的想法:“(我的丈夫)對我說:‘你跟著我一直過苦日子,小孩這麼瘦,你也這麼瘦弱,嫁給另一個能養活你的男人對你比較好,我會找這樣的一個人把你嫁給他(連同我們的孩子)’。我同意這個提議,因為我知道不這樣小孩會餓死,當他離開我的時候,我一點都沒有哭泣,因為我想怎麼樣都不會比跟著他更悲慘。”對於買主來說,這筆買賣也很划算,因為大部分買主都很貧窮,而買他人之妻,雖然有風險,但通常比娶一個寡婦花費要低,比娶一個未婚的女人則花費更是低廉。至於那些富有的買主,支付較高的價格買他人之妻為妾,則一般以能生兒育女為優先條件。
這樣一種明顯為法律所禁止的非法行為,人們本應儘量避免引起官府的注意,卻又為何被訴上公堂?這類訴訟發生的原因,或是源自賣夫或其家庭的勒索,或是由於妻子及其孃家人的反對,或是其他人的勒索或金錢糾紛。要想規避這些風險,在訂立契約時,就要寫明買主知道女方的來歷和婚姻狀況,賣方賣妻出於自願,並由妻子的孃家人擔任證人或保證人,以減少糾紛的發生。
當一個社會以貧窮作為賣妻的藉口,將一個活生生的人作為財產時,就會讓人不寒而慄。好在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的女性早已在經濟上、人格上擺脫了對男性的依附,過上了獨立而有尊嚴的生活,這樣的日子,真好!漫畫/陳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