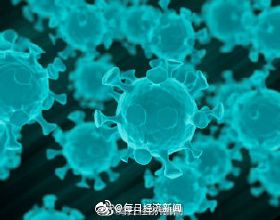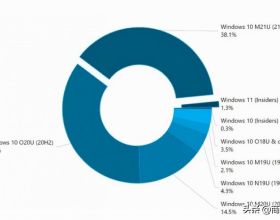在唐朝立國時,他們的家族決定放棄故地、遷往長安時就已經決定了。而那時,他們還有別的選擇嗎?似乎沒有。?很多人都說:因為有了科舉制啊。其實不是。隋唐時期依然是正兒八經計程車族社會,寒門能透過科舉制出人頭地的寥寥無幾,即便是“漏網之魚”也會被人看不起。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張九齡,早年間考中進士,在唐玄宗時官至宰相,文壇政界兩開花,很成功吧?可有次唐玄宗和他聊天,他就把天聊死了。
唐玄宗和藹可親地問:“你什麼家庭啊?”張九齡有點慌:“臣……臣的祖父是錄事參軍,父親是縣丞,也算殷實人家。”唐玄宗說:“嗨,不就是寒門嘛,你直說呀。”
然後又聊起親戚、兄弟、朋友圈……張九齡被問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出宮後是渾身冷汗、臉色煞白。為什麼?雖然張九齡出生於中產階級,但在皇帝和門閥士族眼中,他只是寒門。士族從骨子裡就看不起他,他也自慚形穢。
就算中了進士,你也進不了人家的圈子。維繫士族門閥、上流社會和階層的紐帶就是社交關係,社交關係決定了他們的前途。
隋、唐的科舉制度問題很多。隋文帝當皇帝后,發現“九品中正制”都被玩壞了。幾百年來,朝廷官員基本是根據門第、關係來推薦的,魚龍混雜。
於是,他對大臣們說:“你們推薦的人到底有沒有本事,咱也不知道,那就透過考試來篩選吧。”這便是科舉制的雛形。這和明、清的科舉有很大的不同。此時的科舉是先進行推薦,然後再透過考試來過濾,所以還是在小圈子裡玩。唐朝時,科舉的物件擴大到學校、地方,但也有一個漏洞:不糊名。
我們考試會在卷子上填寫考號、名字、班級等,唐朝是在卷子上寫名字、住址、祖上官職……這樣的話,閱卷老師一看就明白了:自己人當然錄取,不認識的自然落榜。黃巢同學屢試不中一點兒都不冤,你一介私鹽販子,人家才不跟你一起玩兒呢。
為了進入考官的視野,唐朝人會在考試前去長安活動,把自己的詩集和家譜送給考官,以求關照。要不然,“干謁詩”是怎麼來的呢?
在這種體制下,科舉只是門閥士族的調節器、篩選機,只能起到內部淨化的作用,與廣大人民群眾是無緣的。
舉個例子吧。“關隴八柱國”有一個叫於謹的人,和李世民、楊廣的爺爺都是親密戰友。到了晚唐,他有一個後代叫於琮。於琮有能力、有志向,卻一直得不到重用,每天都過得很鬱悶。正好,唐宣宗要選女婿,秘書監鄭顥就說:“我知道你很棒,但是你得先進核心圈子啊。不如你先當個駙馬如何?”於琮一口答應了下來。
於是,鄭顥讓他去參加科舉,然後和考官打招呼:“他以後是駙馬,多多關照啊,拜託了。”後來於琮中進士、娶公主,最後官至大唐宰相。
科舉制消滅門閥士族了嗎?沒有的事。他們在科舉的幫助下,生活得更美好了。
朝廷用科舉來選官,也迫使門閥士族更注重學業,畢竟詩文寫不好,家世再牛也沒用。彼時,優質教育資源基本集中在長安和洛陽。離長安、洛陽越近的地方,越能享受到名師、教材、學風的紅利。如果出生在福建、遼東、廣西之類的地方,讀書就很吃虧了。而長安又是首都,更勝洛陽一籌。
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家族紛紛離開故地,來到長安定居,一方面積極向權力中心靠攏,另一方面謀劃子弟的學業前程。太學、國子監、四門學等名校都在長安,就算名額有限,能交個朋友也好啊。
而此地最有名的是“五姓七家。”趙郡李氏,乍一看還以為是河北人,其實他們從唐朝中期就舉家搬到關中了,和河北趙郡沒有半點兒關係。滎陽鄭氏、清河與博陵崔氏、范陽盧氏的族人,但凡能做到高官的,也基本定居河洛地區,留在家族故地的都是沒出息的。
長安和洛陽匯聚了大半士族。“安史之亂”後,關東逐漸進入藩鎮割據的模式。為了保護生命財產和學業前程,愈加促使門閥士族向河洛地區遷徙。到了晚唐,關東藩鎮已是平民和軍人的天下。
門閥士族集中在長安有什麼好處呢?他們早已放棄了地方的根基,把身家性命和朝廷命運捆綁在一起,讓門閥士族和朝廷成為利益共同體。
地方則是平民和軍人的樂園,所以在晚唐藩鎮割據的歲月,只有藩鎮兵變、平民造反,絕對沒有門閥士族推舉一個司馬懿出來,分一杯羹。時代不同了,保護朝廷、保護長安,就是保護士族自己。
士族的朝廷、平民的藩鎮,再加上統領禁軍的太監,組成了晚唐的鐵三角,讓大唐在“安史之亂”後繼續生存了150年。
在這150年中,門閥士族反而迎來了第二春。趙郡李氏出了17個宰相,滎陽鄭氏號稱“鄭半朝”,清河崔氏有10位宰相……而在盛唐前期,朝堂沒有過他們的位置。
既然早已放棄了地方根基,門閥士族維持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社交關係。這是保護傘,也是最後的遮羞布。在一個圈子裡,大家互相提攜、互相幫助,就算有困難也不要緊,打個招呼就能中進士,長安依然是他們的天下。只要社交關係在,他們就不會掉落階層。
可如果他們的朋友圈不存在了呢?
唐朝的長安歷經多次屠殺。“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著急跑路,只帶了和自己親近的王爺、公主,留在長安的宗室,大多被叛軍屠戮。皇家尚且如此,何況臣子。無數大臣、豪族都沒有逃脫叛軍的屠刀,門閥士族在這場戰爭中元氣大傷。不過還好,剩下的倖存者依然可以把斷裂的朋友圈重新連線,開啟晚唐輝煌的大門。
然而真正的絕殺,來自黃巢之亂。看看《資治通鑑》的記載:“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大唐宗室只要留在長安的,一個不留,滿朝公卿和門閥士族也被殺得人丁大減。迎娶廣德公主的於琮,就死在此時。
這些事都被詩人韋莊寫在了《秦婦吟》中:
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
舞伎歌姬盡暗捐,嬰兒稚女皆生棄。
……
華軒繡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
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
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
當維繫社交關係的人都大半被殺之後,朋友圈也就散了。更重要的是,在一片大亂中,門閥士族的譜牒也丟了。沒有譜牒,活下來的人都成了個體。這個人到底是叔叔還是二大爺,大嬸是哪家的,親戚都有誰,完全搞不清楚。社交網路,斷得一乾二淨。
從此以後,門閥士族的倖存者再也不能恢復社交網路,重新搭建起自己在長安的平臺,只能維持生存。
905年,朱溫在白馬驛殺死朝臣三十餘人,並且投入黃河,倖存下來的門閥士族骨幹也退出了歷史舞臺。
君以此興,必以此亡,門閥士族依靠社交關係興旺了900年,最終又在時代的變遷中,因為社交網路斷裂而消散。從表面上看,他們是敗給了黃巢的屠刀,實際上,他們是敗給了時代的程序。
門閥士族在晚唐的社交關係是寄生於朝廷的軀體之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當社會秩序崩塌、平民崛起,他們再也不能像祖先一樣,在亂世中重振家業。這就是歷史的程序。
在唐朝立國時,他們的家族決定放棄故在唐朝立國時,他們的家族決定放棄故地、遷往長安時就已經決定了。而那時,他們還有別的選擇嗎?似乎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