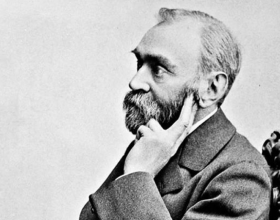(圖源:圖蟲網)
劉剛/文
明州(寧波)之於宋朝,究竟有多重要?南宋定都杭州,明州就在杭州門口,對於杭州的影響,那就不必說了。北宋都城,即使遠在黃河邊上的汴州,也把明州當作了開放社會的海上風向標,海外貿易和海洋文化,透過京甬大運河影響著杭州、蘇州、汴州。
可不,沿著京甬運河走,從明州到汴州,走來了一個要改變中國的人物,列寧稱他是“十一世紀的中國改革家”,而普列漢諾夫乾脆把列寧稱作“俄國的王安石”。為什麼社會主義的列寧新政和資本主義的羅斯福新政,都提到了十一世紀中國的王安石?
這就說明,王安石不但是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還是世界歷史上的改革家,誰讓他在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上出現,並且還在中國做了一次政治改革的實驗呢?當時的中國,在歷史的轉折上,走在了世界的前面,最早開始了從中世紀向近世社會的轉變。
世界歷史上的近世社會,一開始,就出現在了中國的運河兩岸。
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透過大運河,形成了統一的大市場,還以出海口,連線了一萬八千公里的海岸線,三萬多公里的島岸線,以及通往東洋和西洋的航道。試問,在歐洲人的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前,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擁有過如此巨大的海陸兩棲市場?羅馬帝國不曾有過,阿拉伯帝國不曾有過,就連中國本土曾經的漢唐盛世也不曾有過。
面對歷史轉折,宋在文化上準備好了,它消化了來自西域的希臘化世界因素,同時,又與來自西洋的阿拉伯文化互動。在經濟上也準備好了,技術進步、海外貿易和貨幣經濟,那些導致近代國家產生的社會條件基本上也都具備了。文化上儒道釋,經濟上絲瓷茶,都在向外輸出,還有那推動世界歷史程序的“四大發明”,也開始影響世界了。
他看不慣《清明上河圖》裡的模樣
宋也有不足,其不足在於在國家的統一性方面多有缺憾,還有儒教國家觀念與王朝國家形態難以適應新的歷史轉變。其時,世界歷史的主導權,無論陸權還是海權,都轉向了東亞。
東亞內陸,興起了農牧混合型別的草原帝國,在中國歷史上,表現為遼、金、元三朝,再加上一個西夏政權,它們同北宋、南宋互動著,構成了新的南北朝。
東亞沿海底蘊裡,本就孕育了個海洋帝國的胚胎,要透過海外貿易和海權思維將它催生出來,有宋一代,海外貿易足夠了,可海權思維準備好了嗎?還沒有。
就拿王安石來說吧,他對海外貿易的關注,在詩裡有所表現。可他的海權思維,在他的變法主張裡有過表現嗎?沒有,一點也沒有。至少,我們還沒有看到。
王安石未曾航海,卻喜歡觀海,還像曹操那樣,寫了一首觀海的詩,叫做《狼山觀海》,“狼山”在哪裡?在長江出海口,其時,一峰聳立,孤懸江面,未與地接,海拔約百餘米,登之卻以“崑崙”自居,而有詩曰“萬里崑崙誰鑿破?無邊波浪拍天來”。
還有比這更有氣勢的嗎?那氣勢裡,充滿了美少年的氣息,洋溢著大宋青春志,像孟子說的那樣,有一股子“浩然之氣”蓬勃而出。“沛然無御”,連“崑崙”都可以“鑿破”,還有什麼不能“破”?連蒼天都可以滔滔不停地拍打,還有什麼是不可變的“法”?
五百年出一個。他從《山海經》裡出來,海闊天空,獨立一人。一出手,便掀天揭地,有如刑天,他不再是“遨遊半是江湖裡”的少年,“始覺今朝眼界開”,他成為了從崑崙來的“閬苑仙人”,往大海去的“靈槎使者”,要“致君齊堯舜”,為中國立言。如此境界,其詩性風發,神思飛躍,就非錢鍾書《宋詩選》中一句“把鋒芒犀利的語言時常斬截乾脆得不留餘地,沒有回味的表達了新穎的意思”所能道出。
除了寫觀海的詩,他還寫過跟海外貿易有關的詩,那一首《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陰見及之作》,就寫了港口和外貿。從詩題來看,他求官不成——“予求守江陰未得”,還留詩一首——“酬昌叔憶陰見及之作”,這樣的詩,也就他這樣的“非常之人”能寫,“詩言志”,多言“懷才不遇”,哪有言“求官不成”的?有之,也就他王安石。
他為什麼要“求守江陰”?因為他的詩友朱明之,字昌叔,也是他的妹夫,曾在江陰任職,在一首《寄王荊公憶江陰》的詩中,這樣對他說道:“魚是接海隨時足,稻米連湖逐歲豐。太伯人民堪教育,春申溝港可疏通。”詩一共八句,這是其中四句。
對於江南,他本就有著很深的鄉愁,只一句“春風又綠江南岸”——那極簡的一個“綠”字,便將千言萬語道不盡的江南說了個分明,江南之於他,並非地域,而是血脈,不但遍及全身,而且入魂。那時,他從塞外使遼而歸,能不天南地北,感觸尤甚?詩中,江南湖海之地,魚米之鄉,豐饒歲月,那些都早已刻在他的骨子裡了,真正觸及他靈魂的,是寫運河的那兩句,不經意間,寫出他政治的痛點。
他在常州做知州時,就像他在明州鄞縣做知縣那樣,一上來就抓水利,不過,這一回他抓的不是農田水利建設,而是開運河,結果呢?一跤跌倒在運河上。一番勞民傷財之後,他不得不停了下來,因為,他得不到上級支援,只能憑一己之心一職之力,自食其果,有人嘲笑他,說他在地方上,老想著搞改革。
而那時的江陰,就在附近,一條運河從無錫過來,已經開通了,那便是錫澄運河。朱昌叔在江陰任職時,有可能參與了建設,看那四句詩,後兩句,寫的就是錫澄運河。詩中的“太伯”,即吳泰伯,於殷商之際,從周原來無錫,開了一條運河——泰伯瀆,作為運河的源頭;詩中的“春申”,即楚人春申君。戰國時,於江陰長江口岸,鑿溝開港,因其本名黃歇,故曰“黃田港”,宋時,錫澄運河便經由黃田港而入長江。
唐時,長江出海口,港口的重心在江北揚州。宋時,重心轉移,從江北轉向江南,運河入海從揚州改為明州,長江入海則從揚州改在江陰了,王安石在運河入海口的明州鄞縣做過知縣,接下來,他理所當然就想在長江入海口的江陰軍做個知軍了。他對江陰的看法,都反映在詩裡,我們先來看“黃田港”,假設王安石鄞縣三年任職期滿,從明州返回汴京,由南而北,他會怎麼走?一定會沿著運河走吧。
經由杭甬運河、蘇杭運河,他進入錫澄運河,而“黃田港”,就在錫澄運河抵達長江的口岸,是大運河的一個逗號,其對岸,便是揚州——南北運河樞紐。他站在江南岸的這個逗號上,放眼一望,詩曰“黃田港北水如天”,如此勝景,對岸的揚州,已經看不到了,現在的江陰也看不到,那是宋時獨有的勝景。
他在狼山望海,於天人之際,蒼茫獨立,所見者,惟我而已。
而江陰觀港,則不僅看到了“水如天”,還看到了船,“萬里風檣看賈船”,看到了“賈船”帶來的奢侈與繁榮——“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能看到這些不算什麼,還有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也能看到,比如他能看到那些“賈船”是中國經濟的一個變數,這個變數正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所以,他後來在與司馬光辯論時,才那麼有底氣的說道:“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司馬光著眼於國內,看到的就是一個常量,他若睜眼看世界,看到了國際貿易,而不是一頭埋入《資治通鑑》裡,也許他也能抓到一些歷史轉折的頭緒。
但王安石看到了又如何呢?他只能看在眼裡放在心裡,任歲月蹉跎,時光流逝,想當年,他與朱昌叔一道登高望遠,立於高亭,指點江山,談笑風生,那一番書生意氣啊,真是“高亭笑語如昨日”!可今日,風華成昔,已是“末路塵沙非少年”。
他剛從遼國出使歸來,“強乞一官終未得”,數不清他辭過多少回京官,辭得都怕人說他以此沽名釣譽了,可偏偏就在這麼一個不起眼的江陰軍,他要“強乞一官”,然而朝廷自有安排,哪能都遂他願?他也就跟昌叔這麼一說,“只君同病肯相憐”。他為何寧願留在江南觀海,而辭去汴京上河呢?因為他有獨眼。
以他獨眼來看,他在兩地所見不同,從汴京幾進幾齣,於汴河兩岸所見,皆如《清明上河圖》那樣繁榮的景觀。在那景觀裡,資本主義的尾巴高懸如酒旗。那是在小農經濟和小商品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小資市場,是每日每時產生著“資本主義”的溫床,是文化消費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者們歲月靜好的天堂。
可他看不慣,看著看著就皺起了眉頭,因為,他從中看不到增長,只能看到增長的極限,看到在小農經濟主體上生長起來的小商品經濟的那副小模小樣。那小樣,怎麼看,都看不出是個能“富國”的樣,留下一副風流汴梁的富裕皮相,何況還有百萬大軍的臥榻,安放在汴梁城下,那花染人韻,又豈能“強兵”?
他不想讓運河變成《清明上河圖》那樣,他要以運河為紐帶,形成統一的商品市場,要以運河為基地,形成統一的國民經濟,以運河建都般構造舉國體制。
他預感到了現代國家的苗頭
宋立國,既得運河貫通中國之地利,又適逢世界歷史轉折的天時,那時,現代國家的苗頭,隱隱然初現於神州,而第一個預感到它要來的人,便是王安石。
現代國家的本質,既非神化的宗教信仰,亦非聖化的政治倫理,而是作為經濟集中反映的政治權利,請注意,是權利不是權力,然而,在《萬國公法》譯入之前,中國僅有權力,如政權與軍權,它們都是權力,而“權利”,似乎從來就與中國無緣。
可我們從王安石那裡看到了“理財”二字,它已先於“權利”出現。此二者,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價值理性那一面,便是“權利”,而工具理性另一面,則是“理財”。王安石沒有翻開“權利”那一面,從而避免了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糾纏,但他在“理財”那一面,卻做足了文章,做了一篇“以天下之財,興天下之利”的大文章——《上仁宗言事書》。
這是王安石變法的綱領性檔案,文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國家觀念。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國家,是用儒家思想締造的,號稱“禮制國家”,標榜“仁政”理想,兩千年來一以貫之,期間,雖有“陽儒陰法”,禮法並用,且造就“漢唐盛世”,但直到王安石問世之前,那樣一副國家面孔並無大變,要等到王安石出來才有一變。
王安石怎麼個變法?他要把國家重心轉移到“理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解決國家“發展”問題,將“禮制國家”發展為“財政國家”,用“財政”的“法式”坐實“仁政”理想。但其“法式”,既不同於商鞅變法打造耕戰合一的國體,也不同於韓非法術勢三位一體搞君主專制,更不同於漢唐盛世搞“陽儒陰法”那些小玩意,他的思想來自孟子。
我們讀《上仁宗言事書》,通篇下來,發現孟子是個關鍵人物。
王安石認為,他的變法思想,來源於孟子,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是打著“法先王”的旗幟來變法的,而高舉“法先王”的第一旗手,就是孟子。我們知道,孔子是“吾從周”的,所以,經常夢見周公,孟子走得更遠,直接就到了堯舜那裡,走向“法先王”,王安石跟著孟子走,也走向“法先王”——堯舜之道。
堯舜之道,在孟子那裡,表現為“仁政”理想,它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社會主義,主張土地國有,天下為公,如公有化的井田制,另一方面則是市場經濟,主張社會分工,商品交換,強調國家以十一稅為基礎,發展民生主義,有人說那是空想。
對於小農經濟,它可能是個空想,要是在一個統一的國家,用統一的市場,發展統一的國民經濟——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這兩者用一種方式結合起來呢?王安石就這麼想,他要用“理財”的方式,去實現孟子的“仁政”理想,這有點像後來英國的思想家亞當·斯密以《國富論》的方式坐實其《道德情操論》主張。
十八世紀出現的“亞當·斯密問題”,十一世紀的王安石也遇到了。如果說“理財”是王安石的《國富論》,那麼來自孟子的“仁政”理想,便是他的《道德情操論》了。
但凡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既要富國強兵,同時還要為富國強兵提供正義性與正當性,亦即為《國富論》確立一個道德基礎。
亞當·斯密這樣做了,理所當然,因為他是國家現代化教父,要為國家走向指明道路,因此,他應當回答人們對他的提問:道德情操是否與自私自利相矛盾?
如果說,不同的私利追求透過市場作用能達成國富目標的說法還好理解,那麼認為個體逐利行為能滿足道德情操的要求,又該怎樣解讀呢?亞當·斯密指出,自然界給予所有動物既定目標,人類具有嚮往這些目標的天性,自然界指導我們運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來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沒有被交給我們那遲緩而不可靠的理性來決定,所有動物的本能行動,都將實現我們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結果——偉大的自然界所設定的善良目標。
按照亞當·斯密的指導,我們用天性去讀,而非以理性讀,這兩本書就讀通了,從對立中讀出了統一,從衝突中讀出了互動,從鬥爭哲學裡讀出了道德天啟。
王安石也這樣做了,而且比亞當·斯密早了700來年,從世界歷史來看,當時,世界三大帝國,只有宋帝國,率先來到了國家轉型的邊緣,徘徊在近世國家門前,而阿拉伯帝國、拜占庭等,雖與宋並駕齊驅,但它們未能成為世界歷史程序的領航船。
它們畢竟沒有一條大運河能連山通海,將全國從南到北統一起來,也沒有運河兩岸那些令蘇萊曼和馬可波羅驚歎不已的城市,那些城市,不僅人口眾多,規模宏大,而且高度發達,極其繁華,可供揚帆逐利的商人們流連忘返,而追求利益最大化。
運河之上,不僅有東京汴梁,還有蘇、杭,有揚州、越州與明州,其中任何一個城市都足夠富裕,足夠風流,放到國際上去,都可以名利雙收,而王安石卻對它們皺緊了眉頭,因為他知道,那些城市早已是頭頂著天花板跳舞,跳到了極限也沒能跳出新的增長點,在小農經濟和小商品經濟的基礎上,難有新的增長,於是,國家必須出場。
(未完待續。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