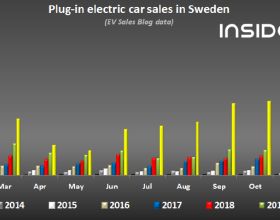阿水
時間是個不忍細想的無底洞,可沒有一個認真的創作者能夠繞開它。到了一定的時刻,它就會像攔路虎躍至跟前。是隻威風凜凜的斑斕猛虎,令人無法忽視。
羅思容和孤毛頭樂團的新專輯《今日本是馬》,同名歌即是題眼,說時間:
“今本日(今日)是馬,行跑著
天光日(明日)是虎,慾望著
昨本日(昨日)是一串風鈴
叮噹說個不停”
是她和友人登山,在雙扇蕨密佈的山林剪碎光影行走,緊接著在垂直陡降的路段攀拉繩索,凝神腳下,經歷三十分鐘恍如隔世的體驗後,返家寫下的小詩。
登過山的人能理解這種體驗。因為腳下險峻,須把全副心力集中在腳底和土地接觸的一個個瞬間。時間過得既快又慢,不見人類痕跡的山野環境模糊掉年月日的界限。日常的時間感被打破,滑進更廣闊的維度。吉他和低音提琴在無垠的廣闊中,勾勒出一片可以被感知的銀亮空間。羅思容稍稍為吟誦添上旋律,歌就活了。
第一段曠遠,第二段的節奏彈撥頭皮,身體開始律動。對於時間千鈞一髮的體驗,奔跑的今天,即將吞噬你的明天,不肯閉嘴的昨天,她讓短小潤澤的撥絃和天真的小提琴對話。女聲吟唱彷彿無知覺,閉上眼,只順著音樂哼出音符自由的形態。臨到深淵,驟然開闊,這是羅思容的拿手好戲。

羅思容是詩人,音樂人,女性,熱愛土地和人的人。這些是別人給她的介紹性標籤。她中年以後才開始做音樂,途徑是找到幾位對的音樂夥伴,把詩譜上曲唱成歌。中文的詩,多用客家話演唱;曲風多變,藍調、Bossa Nova、爵士搖擺、實驗民謠、鄉村搖滾,不拘一格。樂隊和她在一起該很高興,因為一切都可嘗試。客家音樂的半音撐起即興空間,接駁遙遠土地的各種音樂。
羅思容奇特的一個地方在於,她的每張專輯都會聽,《落腳》(2018)、《多一個》(2015)、《攬花去》(2011)、《每日》(2007)。但她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她的年齡、外表和生活經歷,卻好像始終沒有分明的印象。這大概可以說明,羅思容是個真正的詩人。
詩人是容器。不管她在鄉下耕種養雞鴨,還是住進公寓樓,或在哪裡做駐鄉藝術家,容器都能隨時騰空,裝進新的內容。她性感,來自一顆冒騰著熱氣的心,“我不過四五十歲而已/有人說我像朵花/我不過四五十歲而已/我愛笑愛哭感情又豐富/我想要做什麼就放手去做”(《我不過四五十歲而已》)。她書寫和土地萬物相處的細緻感受,“一落腳,土地燒暖/一回頭,山水微笑/落腳南莊,放眼四方”(《落腳南莊》),有神的氣魄。她認為愛情是“青春流逝的梨花,命運交融的梨子”(《我們的愛情》)。“哀樂中年”的滋味,因為相濡以沫的情意而得以細嘗,那是“手牽手/共下行/應該都無/應該都有”(《白薯,月光山》)的豐厚饋贈。親情化作“有兩條鬍鬚仔的塘蝨(鯰魚)”“烏烏的目金金”的陰司使者(《塘蝨》)。她含淚向他們詢問,父母在那邊可好?這聲音可撼動天地。
土地、女性、歷史、社會這些她從前常涉的議題,淡去在《今日本是馬》更普世的生命體驗身後。溫暖的更溫暖,神秘的愈神秘。《斜斜的心》淡筆勾勒夏天、橘貓、仲夏夜的月光、玫瑰色的天空。她不寫斜斜的雨絲,只寫斜斜的心、斜斜地跳動。雨絲確實存在,包裹住一個思念遠方的女人,古典情意生存在輕輕搖擺的音樂裡。手風琴緊接著跳出來,炎熱陸地的熱情音樂撩撥著春心。她唱“跳~~舞”像手工打製的銅器,轉個角度撞到太陽而大放光輝。愛情就是銅質的聖器,罕見又珍貴。她的嬌俏歌聲一時轉為“噠啦啦噠哈哈哈”的渾厚奔放。羅思容是酒館裡唱弗拉明戈的西班牙女人,一生的故事放下,融進歌舞和煙霧中。
有時候是別人的故事。嫁歌《你出嫁該日》,空蕩的鼓一下一下打在提琴絲線上。送嫁的隊伍行遠後,音樂變了一張臉。悲傷從山的那邊折返,成了雀躍的小調。小打、管笛和胡琴鬆鬆落落,預示重要的篇章翻過。離別的一刻已經過去,接下來期盼重逢。
神秘的歌有《巫婆塔》和《測量》。在沒有月光的所在,是誰披著暗灰的羅帕垂淚,卻仍懷有質樸的嚮往,想要草、花和跳舞。她像換了一個靈魂似的唱《測量》,不再憂傷,幾乎狠狠。塔布拉鼓如同巨大的皮囊,發出深沉回聲,在水下吐著泡泡。線條和光影交錯,小人的身形忽而變大。“花園裡的玫瑰/還在測量 刺的位所/並且垂涎著血”。誰能破解密語?羅思容最迷人的地方,是她唱到全情投入後近巫的狀態。語言被拋棄,喉嚨深處擠壓出“咔咔咔咔咔”。聽到頭皮發緊,還想頑抗,不被拽進神秘的處所。
最喜歡的一首歌是《被雨啄溼的母雞》,在頭一場春雨,誕下第一顆雞蛋。她那種唱法像在祭祀,血腥的古老儀式早被廢除,只剩下真誠地慶祝春天到來。一句三嘆,把一根皮筋拉到無限長,在一張薄紙上寫滿密密麻麻的字元。器樂們自由不羈,盡情表達萬物復甦時嫩綠的喜悅。聽多少遍,都會被“咕咕咕咕咕”逗得很開心。學母雞叫的歌者,把最好聽的聲音和最充沛的元氣都傾入雞叫。這種快樂玩過小黃鴨/尖叫雞的朋友會懂。一捏一叫,樂不可支,天地萬物頓時化為無形。春天勢不可擋,只有生命值得歌頌。
有兩個版本的《紙人》是隱喻。地上搖來搖去的紙人沒有魂,但紙人兇險。《千與千尋》裡渡海追殺的紙人被法術操縱,把白龍割傷,鮮血淋漓。它們像螻蟻蝗蟲,起時大軍壓境,去時飄搖零落。吟唱和銅管召喚世間的真人:願你們以身為器皿,心作神殿,讓天賜的力量充滿頭腦,永遠不要變成紙人。
責任編輯:陳詩懷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