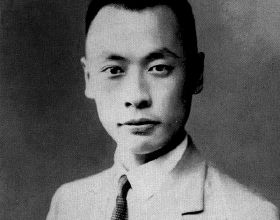最近“元宇宙”的話題十分流行,其英文Metaverse的意思是“超越宇宙”,代表著與現實世界平行的虛擬世界,這似乎是一種更為廣大的宇宙觀。人類對宇宙的認識,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樸素的直觀感受到傳說故事,再到自然科學上的研究,從古至今的宇宙觀,也體現著文明的變化。
明代徐光啟湯若望測繪《赤道南北兩總星圖》
古語云:“上下四方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由此觀之,“宇”與“宙”並舉,同時涵蓋了空間和時間的概念,實際上更符合現代人對於宇宙、乃至“元宇宙”的認識。那麼,中國古人是如何認識“宇宙”的呢?
混沌初開 宇宙誕生
盤古開天闢地是中國最經典的關於宇宙誕生的傳說。但實際上,盤古的故事出現時間很晚,當司馬遷在《史記》中明確記載黃帝為文明始祖的時候,典籍中還不見盤古的蹤影,此時公認的歷史源頭已有五帝,而三皇的故事則要在此後才進入歷史敘述。三國時期的徐整在《三五歷記》中終於把三皇和更早的盤古故事納入典籍,其中有關盤古開天闢地的文字,是此後盤古故事與宇宙起源傳說的“模板”,其經典性是毋庸置疑的: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
這段文字雖然不長,卻提供了兩個極為關鍵的資訊:首先,宇宙之處是一片混沌,像個雞蛋一樣,天地的界限不明顯,而盤古也是誕生於混沌之。宇宙在誕生之前是“無”的狀態,是有一個突然“誕生”的時刻,這在古人眼中就是盤古的誕生,而在今天的科學中,這或許就是宇宙大爆炸的時刻。
還有一個關鍵資訊,說明天地是根據陰陽變化而逐漸形成,陽氣慢慢到了天上,陰氣逐步沉入地下,這就形成了最初的天地。這是一種樸素的自然觀念,也是道家思想的體現,認為陽氣是輕而清的,陰氣是重而濁的,這才有了天地之別,上下之別,以及距離與方位的不同。
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靈,大多都有超凡的法力與無窮的生命力,但盤古是罕見的為了天地萬物而自我犧牲的神。盤古的身軀化為世間萬物,這種形象並不多見。在宋真宗時期,有一部大型道教類書《雲笈七籤》,其中關於宇宙起源的記載與之類似,卻更加詳細,也更加文學化與哲理化:
“混沌之先,太無空焉;混沌之始,太和寄焉。寂兮寥兮,無適無莫……元氣先清,升上為天,元氣後濁,降下為地,太無虛空之道已生焉。道既無生,自然之本,不可名宣,乃知自然者,道之父母,氣之根本也。夫自然本一,大道本一,元氣本一。一者,真正至元,純陽一氣,與太無合體,與大道同心,與自然同性,則可以無始無終,無形無象,清濁一體,混沌之未質,故莫可紀其窮極……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裡,肌肉為田土,發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
在這裡,《老子》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思想與盤古故事結合起來,不僅盤古是“真正至元,純陽一氣”的產物,盤古死後,也是化為日月星辰,山川湖海,其生命與宇宙萬物融為一體,這是古人樸素的宇宙觀與自然觀:不把個體與自然割裂開,而且不論是神靈還是普通人,都是宇宙元氣的產物,最終也會進入宇宙,迴歸自然。
從“天圓地方”到宇宙圖景
關於宇宙形象的認知,古代最經典的說法是“天圓地方”,一般認為這是《淮南子·天文訓》中的記載:“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這是一種基於現實生活認知而產生的樸素觀念。
這種樸素的宇宙觀與道家、佛教思想結合後,就產生了更多關於宇宙圖景更加細緻的想象,在文學作品中,它多有呈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遊記》中關於天地方位的“設計”:四大部洲、須彌山與海洋共同組成了龐大的宇宙。
《西遊記》對鴻蒙初開、盤古故事之後的記錄,在全書開篇就有出現:
“感盤古開闢,三皇治世,五帝定倫,世界之間,遂分為四大部洲:曰東勝神洲,曰西牛賀洲,曰南贍部洲,曰北俱蘆洲。這部書單表東勝神洲。海外有一國土,名曰傲來國。國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山,喚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脈,三島之來龍,自開清濁而立,鴻蒙判後而成。”
四大部洲最初來自古代佛教典籍《阿含經》,在《西遊記》中,它成為故事宇宙觀的重要載體。而書中關於天宮、西天的內容,則是道教與佛教思想的集中體現,這種混雜著不同神話體系的文學作品,其實對讀者的吸引力更強,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都能從中找到思想的認同感,或者說,這符合多數人對宇宙萬物的樸素認知,都能從中獲取精神的共鳴。
從文學創作上看,這是一個巧妙的做法,但從讀者接受的層面上看,這實際上還是古人宇宙觀的體現:承認宇宙圖景的複雜性與多元性,而不是站在某個絕對的立場上來認識宇宙,接納不同的宇宙觀。這或許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容性的體現,即便是儒釋道的宇宙觀混雜在一起,在文學作品中也不“違和”。
元代劉貫道《夢蝶圖》
超越宇宙 逍遙棲居
除了對宇宙起源與宇宙形象的認知,古人也十分關心自己如何與宇宙之中合理生存,如何與天地萬物保持合理的關係。這其中道家思想最具超越性,尤其是莊子的思想,更加引人遐思,令人神往。
莊子在《逍遙遊》中有這段經典的文字: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裡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裡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這段文字不僅是進入莊子哲學的“第一站”,也是幾千年來無數人嚮往的美好境界。在水中為鯤,進入空中則為鵬,鯤鵬展翅,後世的李白也驚歎“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鯤鵬的生命是自然而靈動的,它被太多人寄託了少年意氣,又被無數人看成精神自由的載體。
像鯤鵬這種可以在天地之間隨意遷徙、變化的形象,已經超越了時空界限。這其中有一個頗為深刻的哲學思考:宇宙中“大小之辯”的問題。在莊子看來,事物的大小都是相對而言的,這是一種“相對主義”。而逍遙的狀態,就在於突破了這種形式上的侷限。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時間也並非無窮無盡,但人追求自我超越的衝動卻是始終存在的。而鯤鵬這個美好的意象,讓我們看到了超越時間、自我之後的逍遙狀態,令人無比神往。
要想達到這一境界並非易事。莊子在《齊物論》中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種“逍遙於天地之間”的狀態是個體與自然的統一,是我們在宇宙萬物中最佳的生存狀態:既有個體主體性,又有自由精神,這並不是消弭個性,而是各種自由狀態的並存。
古往今來,太多人嚮往逍遙的狀態,但大多數人只能憧憬其美好,卻在現實中與世沉浮,很難獲得超脫的人生狀態。莊子反對外物對人的約束,拋棄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或許才能獲得更多的自由與幸福。
莊子《大宗師》中說:“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哲學家牟宗三曾說:“道家的智慧是‘忘’的智慧……相忘是一種很高的智慧”。擁有“忘”的智慧,可以讓我們放下很多執念與煩惱,也能達到更高的精神境界。要想真正做到“相忘”,還需放下心中過強的執念,尤其是對物慾的執念,要不然就會陷入慾望的深淵,難以掙脫現實的桎梏。
莊子筆下的鯤鵬,似乎是一個沒有煩惱與執念的自由狀態,它超脫於現實之上,融入大自然的變化,身體形態也能輕鬆轉換。鯤鵬與逍遙的狀態,是古人想象力的呈現,也是對現實之上超越精神的體現。
這其中的“遊”,就是一個自由而暢快的狀態。德國學者漢斯-格奧爾格·梅勒認為這關乎“我們來自何方”這一終極問題:“‘遊’的運動狀態漫無目的,它沒有發端,沒有終點,卻體現著一種敏銳的適應能力”。這種漫遊的精神狀態,其實古往今來一直存在,越是精神自由的生命,越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古人面對無邊無際的宇宙,會產生無窮的想象,卻在現實中不得不感嘆生命的侷限,以及生產力的有限,古人的遷徙能力受制於身體與自然條件的約束,只能想象出各種有極限能力的生靈。水中之魚,空中之鳥,都激發著古人的想象力,長此以往,便產生了各種神話傳說。不論是盤古的故事,還是鯤鵬的誕生,都是如此。正是這種在宇宙中“遊”的狀態,讓人們獲得了心靈上的自由,即便宇宙是遼闊的,個體也能在心靈自由中實現真正的逍遙與超越。
如今,現代科學技術實現了對更遙遠的星空的探索,可以在渺遠的宇宙中探索更多的奧妙,古人對宇宙的樸素認識,於今看來也頗具想象力,而道家思想中關於人在天地萬物之間如何逍遙棲居的思考,也值得今人細細品味。
原標題:古代人可以夢見“元宇宙”嗎?
文/黃西蒙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