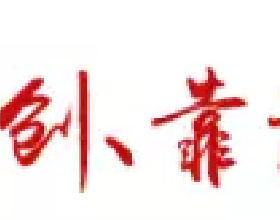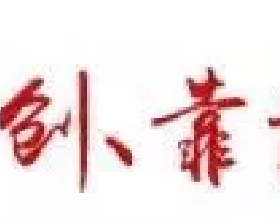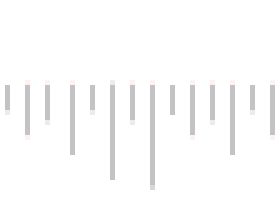唐朝時,福州府長樂縣有一沈姓富戶,家中良田萬頃,房屋連舍,還經營著酒館、當鋪等各色生意。沈財主家中一妻三妾,九個孩子。依仗著家中財勢,孩子們個個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時常在街頭以捉拿窮苦人家的孩子或乞丐為樂。
為看家護院,沈財主還養了一條大狗,半米來高,黝黑髮亮的皮毛,結實的肌肉,滿眼兇狠。和沈家人一樣,這狗也是眼高於頂,但凡有穿著破爛的人從門前經過,要麼狂吠,要麼衝出來嚇唬,甚至有時還會咬上一口,縣民們對沈家的狗唯恐避之不及。
財神爺似乎只垂青於沈家。住在沈家宅院南端的萬裕良家裡卻是相當貧困,一家五口全靠他打點零工,妻子為人縫補為生,一年到頭掙的錢還管不夠吃喝,更不要說置一件好衣服了。
這天,萬裕良的兒子萬家寶從沈家門前經過。聽到門外有腳步聲,大狗狂吠一聲,從院子裡衝了出來。見對方穿著一件灰白的褂衫,上面還綴著不少的補丁,便一下子撲了上去,張開大嘴朝著萬家寶腿上狠咬下去。
五歲的萬家寶哪裡見過這等陣勢?嚇得哇得一聲大哭起來,想跑又跑不動。周圍的人聽見哭聲,都從家裡出來張望,見大狗正在咬孩子,紛紛拿起棍子、扁擔,作勢要朝惡狗打去。
大狗見勢不妙,放開萬家寶轉身逃進了屋裡。
此時的萬家寶已經哭得緩不過氣來了,腿上被咬掉一大塊肉,鮮血長流。萬妻趕到,抱起孩子就往藥鋪跑。
可憐的萬家寶因為受驚過度,當天晚上便發起了高燒。萬裕良回到家中,見兒子無辜受傷,抄起扁擔衝到沈家找人算賬。可任他怎麼拍門,沈家毫無反應,一副置之不理的態度。萬裕良在門口罵了幾句後,悻悻而歸。
萬家寶一連三天,高燒不退,再加上傷口發炎感染,第四日凌晨,夭折了。
萬家人哭得呼天搶地,萬家老爺子和老伴更是痛不欲生,幾次想隨著孩子一起去。萬裕良抹了抹眼淚,忿忿地說:“我要去報官,讓沈家償命!”
第二天一早,萬裕良帶著訴狀去到了長樂縣衙,狀告沈家惡狗傷人致死,要求沈家處死惡狗。
長樂知縣錢適從來長樂四年了,平日裡沒少受沈家的賄賂。聞知有人要告沈家,還沒升堂,就派了一個衙役去沈家報信。
沈財主根本沒當回事,淡淡地說了一句:“誰讓他從我門前經過?穿成那樣,誰知道是不是盜賊呢?讓錢知縣看著辦好了,完事後一起喝酒。”
錢知縣得了回信,瞭然其中的意思,胸有成竹地開堂。還沒等萬裕良陳述完事由,錢知縣一臉不耐煩地打斷他:“好了,我已經知道了。狗傷人,並非主人指使,你找沈家有何用?我看你純屬是想訛詐吧?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訛詐,還有天理嗎?來人,將堂下之下杖責二十大板!”
萬裕良一臉震驚,自己明明是受害者,如今反被誣陷為訛詐!還憑白無故地受責打!
二十大板後,萬裕良瘸著腿走出縣衙,回過身,朝著縣衙門口呸了一聲,才慢慢地走回家去。
看著丈夫身上的血,萬妻很是心痛:“算了,我們告不過人家的,認命吧。”這個忠厚的中年漢子聽著妻子的安慰,卻更是內疚,雙手抱著頭,深深地低了下去,不住地嘆息著。
自那以後,萬家人再出門,寧願繞上一個大彎,也不再從沈家門前經過。
沈家的狗仍舊惡性不改,不時有傷人的訊息傳出,也有傷者去縣衙報官的,可都沒討到好,反倒是錢知縣的腰包一天比一天鼓了起來。
半年後的一天,有貨郎沿街叫賣,萬老孃想著媳婦的針線快用完了,便叫住貨郎,想再添置一些。貨郎在萬家門口停下,萬老孃走出家門,在貨擔前埋頭挑選。
沈家大狗正好在家門口閒逛,遠遠地看見有人,飛也似地跑了過來。等看清楚對方一身破爛衣服時,縱身一撲,霎時將萬老孃撲倒在地,張口大嘴向肩膀咬去。
萬老孃驚呼,貨郎拿起扁擔朝狗身上打去,萬家老爺子和萬妻也拿著棍子、扁擔從屋裡衝了出來。三人合力驅趕,才將惡狗嚇走。狗牙太過鋒利,雖及時卻還是在萬老孃肩頭上留下了兩排半寸來深的牙印。
兒子被狗咬死,母親被狗咬傷,萬裕良哪裡還坐得住?又想找沈家人拼命。萬老爺子和萬妻死死地拽住他,萬妻哭著勸道:“算了,上次的教訓忘了嗎?兒子沒了,母親又這樣了,你再出事,我可怎麼活啊!”
惱狠至極的萬裕良還算有一絲理智,他嘆了一口氣,丟下了手中的扁擔,蹲在院子裡,悶頭抽著煙。
夜裡,萬裕良徹夜難眠,他翻來覆去地想著,該如何討回一個公道呢?告狀,縣衙是指望不上的;講道理,沈家是指望不上的。那還能怎麼做?天矇矇亮時,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這天,萬裕良典當了家裡的一件破棉襖,換了兩文錢,去到迎來酒樓,想要買些滷牛肉。夥計見他寒酸,隨手取下一塊肉,從中切了十來片,遞給他,還指了指對面的大樹,意思是讓他摘片樹葉來包肉。
萬裕良也不糾結,見酒樓後院有一株植物,長著又大又綠的葉子,遂進去摘下一片,將肉放在其中,然後左折右疊,一層一層地包好,還擔心破漏,又使勁地揉了揉葉子壓實。那葉子來回的折騰,經脈都斷了,有些地方還滲出了汁液。萬裕良避開滲汁的地方,將肉放進背後的簍子裡。
這天,他選擇從沈家門前的路回家。
快到沈家門口的時候,他加重了腳步。果然,院裡的大狗開始狂吠了起來,把門撞得砰砰直響。萬裕良也不走了,從簍子裡取出肉,等著大狗衝出來。
狗衝出來那一刻,萬裕良將肉擲向它,然後快步跑開,找了個拐角躲了起來。
那狗聞著肉味,也不再追趕萬裕良,口腳並用,將葉子開啟,餓狼般將肉一口吞了下去。還不解饞,又用舌頭將葉子上殘留的肉渣舔了又舔,連肉汁也不放過。
等狗吃完了,萬裕良笑了,他繞了一個遠路回家去了。
第二天一早,街上吵雜一片,萬裕良推門而出,只見街上站滿了人,個個喜笑顏開。
萬裕良上前詢問,有人悄悄告訴他,沈家的狗死了!沈家的人已經罵了快一個時辰了!萬裕良心中暗喜,臉上卻是不動聲色,轉身回到了屋裡。
沈家的狗半夜死了,等到僕人們早上發現時,已經全身僵硬了,嘴邊還有一灘白沫。
沈財主勃然大怒,將僕人們全部喊來審問。僕人們都說這狗昨日吃的還是同往常一樣,也不知為什麼會死。
後來管家在門外撿了片踩得稀爛、上面還留有油漬的葉子,猜測是有人給狗餵了帶毒的肉。沈財主聽聞,更是怒不可遏,發誓要找到投毒的人。
他將府裡所有僕人安排出去,去到各家肉店詢問,昨日有誰買過肉,還是用葉子包裝的。直到中午,有人回來告訴他,昨天萬裕良曾在迎來酒樓買過肉,夥計欺他窮,讓他用葉子包好帶回去。
沈財主帶著葉子,拖著狗的屍體,去到縣衙,狀告萬裕良投毒害狗。
錢知縣將萬裕良叫到縣衙,升堂問案。
面對怒氣沖天的沈財主,萬裕良一臉鎮靜,他說:“我的肉是在迎來酒樓買的,如果有毒,那是這肉有毒嗎?”
聽到這話,沈財主一下子愣住了,錢知縣也不好應答。縣裡幾乎所有人都知道,迎來酒樓是沈財主的產業,如果承認肉有毒,豈不是說自己一直在賣帶毒的肉嗎?
錢知縣哼了一聲,說道:“肉肯定沒毒,定是那葉子有毒。你葉子從何而來?”
萬裕良假裝驚詫地“啊”了一聲後,說道:“那葉子也是酒樓裡摘的,酒樓裡怎麼會有有毒的植物?”
這一問,沈財主和錢知縣更是不好回答了,如果承認葉子有毒,那酒樓裡種有毒的植物,莫非是想讓客人中毒?
沈財主氣惱地看著萬裕良,卻是無計可施。他想了想,狗死是小事,影響酒樓的生意卻是大事,如今承認肉和葉子無毒才是上策。
他暗地裡朝錢知縣搖了搖頭,錢知縣會意,朗聲對萬裕良說道:“嗯,本官已經明白,下毒之人不是你,肉無毒,葉子也無毒。退堂!”
回家的路上,街坊四鄰們都朝他豎起大拇指。妻子也來打聽他到底做了什麼。
萬裕良笑了笑:“也沒什麼,我以前從酒樓經過時,看見裡面有一盆滴水觀音,我摘的那片葉子正是滴水觀音的葉子。我用它包肉,然後使勁揉搓,使葉面損壞,汁液滲出,浸到了肉上。葉完好時無毒,但汁液卻有毒,狗吃了有毒的肉,能不死嗎?”
就這樣,萬裕良用一片葉子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條人人痛恨的惡狗。
惡狗傷人並非稀奇的事,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對狗如何處理,對養狗的人如何處理,和對狗主人如何處理,這卻彰顯了社會的文明程度。
在唐朝,對惡狗傷人已經列入了律法。
《唐律疏議》中曾寫道:諸畜產及噬犬有觝蹋齧人,而標識羈絆不如法,若狂犬不殺者,笞四十;以故殺傷人者,以過失論。若故放令殺傷人者,減鬥殺傷一等。
意思是畜產用角抵人者,割去兩角;踩踏人者,割去雙足;咬人者,截去兩耳。如果狂犬主人不依法執行,人和狗都將受四十杖刑。如果再犯,則以過失殺人罪論處。如果明知道狗有此等惡性,還故意縱放者,按鬥毆殺傷罪減一等執行;如被惡犬咬傷,有20日觀察期,觀察期內傷者死亡,按鬥毆殺傷罪論處。20天后死亡,則以傷人罪論處;故意放縱惡犬咬傷孩子的,流放一年。
相較於很多國家有專門的《惡犬法》,對狗主人追究刑事責任;在我國,對惡犬傷人,更多的是民事責任,顯然震懾力遠遠不夠。